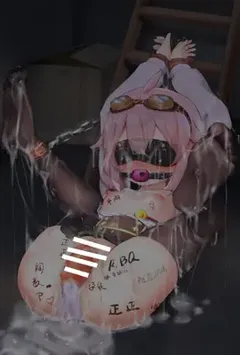医院病房内,惨白的日光灯下,一切都显得毫无生气。
玄机子躺在病床上,脸色如纸般苍白,嘴角还残留着未擦净的血迹。张志成和他的弟子们围在床边,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
“师父,您怎么会输得这么惨?”大弟子陈明声音发颤,“您可是龙虎山正一派的传人,师祖曾说过您是千年难遇的奇才。天下能伤您的人,屈指可数啊!”
玄机子艰难地睁开眼,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那不是普通的厉鬼……”
他剧烈咳嗽几声,嘴角渗出新的血丝。
“那是极为强大的鬼王……”他停顿了很久,像在回想什么,“它站在黑雾之中,四周的温度瞬间跌入冰窖。我太轻敌了……”
他喘息着,眼中闪过一丝忧虑:“那个叫昊天的少年,才二十出头的年纪,满头白发……那是生命力流失的明证。他为了复仇,付出的代价恐怕远比我想象的要惨重。”
声音更加虚弱:“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也正因如此,他才是最可怕的。”
张志成听得心惊胆战,声音中透着绝望:“道长,连您都无法降伏那鬼物,放眼当世,恐怕已无人能治!难道……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祸害人间吗?”
“不。”玄机子缓缓摇头,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光芒,“有一人,定能治得了它。”
“什么?”张志成猛地抬头,“当世竟还有比道长您更高明的人?此人是谁?在何处?求您务必为我引荐!”
玄机子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能人辈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比我道行高深之人,何止千百。”
他顿了顿:“这位高人是泰国的降头师,法号阿赞?尼拉,近日恰好在台湾修行。”
“降头师?”张志成愣了愣,脸上浮现疑惑之色,“泰国的巫术……可靠吗?”
“正因如此,才更显其高深。”玄机子正色道,“真正的高人,往往隐于市井,不为世人所知。若非我三年前在曼谷亲身领教过阿赞?尼拉的神通,也不会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奇人。我估计他的法力……至少高我十倍。”
他从枕下摸出一张纸条,那动作很吃力,像在移动千斤重物。
“这是他的联络方式。你去找他,不必多言,他看你一眼,便知该如何是好。”
张志成接过纸条,如获至宝。他恭敬地说:“多谢道长指点!”
玄机子停顿了很久,像在思考该不该说出下面的话。最后,他还是说了:
“这场正邪之战,恐怕才刚刚拉开序幕。无论结局如何,都将是一场血雨腥风……”
张志成心头一凛,握紧了手中的纸条——那纸条很薄,薄得像一根稻草,可此刻却是他唯一的希望。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病房内,玄机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一位护士拿着一张符走进来,说在他要送洗裤子的口袋里找到这张符,拿来还给他。
玄机子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是大胡子塞给他的。他把符拿在手上,轻轻一抖。
一段影像缓缓浮现在空中,画面模糊,像隔着一层雾。病房里的温度骤然下降,玄机子感到一股寒意从骨子里渗出来。
影像中,是一个阴暗的密室。
清虚子站在炼丹炉前,炉火通红。他的脸上带着狂热的表情,嘴里念着什么咒语。旁边,几个活人被绑在木桩上,嘴巴被堵住,眼中充满恐惧。
影像继续播放,但画面开始跳动,象是被什么东西干扰了。
清虚子将活人推入炉火中,惨叫声撕裂了整个密室。
那声音很远,又很近,象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
“不……这不可能……”玄机子喃喃自语。
影像突然断掉了一瞬,然后再次浮现。
这次,清虚子跪在地上,双手抱头,脸上的表情扭曲得不像人类。
他的身体开始痉挛,七窍流血,最后——
整个人爆裂开来,血肉四溅。
影像在这里戛然而止,像一个残缺的梦。
玄机子浑身颤抖,额头冷汗涔涔。他张开嘴,想说些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这些年来,他一直奉清虚子为师祖,尊崇师门正统。可现在……现在……
那些信仰,那些坚持,象是突然被人撕开了一个口子。
“我……我一直以来……”
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呼吸越来越困难。
影像中那些残缺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重播,清虚子的惨叫,那些活人的眼神,炉火中的血肉——
一口鲜血喷出,溅在雪白的床单上,像盛开的红花。
玄机子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张志成站在黑色宾士车旁,手里拿着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泰文名字——阿赞?尼拉,以及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
“老大,这真的靠谱吗?”坐在副驾驶座的阿豹皱着眉头,“连玄机子那种得道高人都败了,找个泰国人有用?”
张志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后,一个带着浓重泰式口音的中文传来:“喂?”
“你是阿赞?尼拉吗?”张志成开门见山,“我是玄机子介绍的。我需要你的帮助。”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玄机子啊……之前有过一面之缘。”
“我方便找你当面谈吗?”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张志成几乎以为对方挂断了,直到阿赞?尼拉终于开口:“我现在在港口旁边的一个工地。”
张志成愣了愣:“工地?”
“对,工地。”阿赞?尼拉报出了地址,便挂断了电话。
张志成盯着手机,心中升起一丝疑惑。一个降头师,在工地?
半小时后,张志成带着四名手下来到了港边的建筑工地。
这是一处正在兴建的办公大楼,钢筋水泥的骨架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工地门口的保全拦住了他们。
“这里是工地,间人禁止进入。”保全板着脸说。
张志成皱起眉头,正要说话,阿豹已经上前一步,抓住保全的衣领:“让开。”
就在这时,工地深处传来一个声音:“尼拉,你这堆水泥早上如果搬不完,我就扣你今天的工资!听到没有?”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瘦削的男人正从卡车上卸下一袋袋水泥。
他的皮肤黝黑,身上沾满了灰尘,头上戴着一顶破旧帽子。
旁边一个监工正对着他大吼。
张志成看着那个瘦削的男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这个在烈日下搬水泥、被监工呼来喝去的工人,就是玄机子口中能对付鬼王的降头师?
张志成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
他想起玄机子苍白的脸,想起那句“法力至少高我十倍”。
可眼前这个男人……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工人,甚至还有些落魄。
会不会是玄机子怕丢脸,随便塞个人给他?
“阿豹。”张志成冷冷地说。
阿豹会意,上前推开保全,朝着阿赞?尼拉走去。其他几名手下也跟了上去。保全想要阻拦,但被另一名手下一把拖到旁边,压制在地上。
张志成走到阿赞?尼拉面前,上下打量着这个男人。阿赞?尼拉放下水泥袋,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然后缓缓地抬起头。
他的眼神平静如水,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深邃。
“你就是阿赞?尼拉?”张志成冷声问道。
阿赞?尼拉微微一笑:“你说呢?”
张志成皱起眉头:“我问你,你是不是降头师?”
“也许吧。”阿赞?尼拉耸了耸肩,继续搬起另一袋水泥。
“也许?”张志成的声音中带着怒意,“我没时间跟你玩文字游戏。你到底能不能对付那个鬼王?”
“可能吧。”阿赞?尼拉回答得云淡风轻。
张志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个泰国人分明是在敷衍他!他混了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眼前这个男人,不是骗子,就是疯子。
阿豹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上前一步,抓住阿赞?尼拉的衣领,一拳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
阿赞?尼拉被打得蹲在地上,捂着脸颊。阿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冷笑道:“老实回答我老大的问题,听到没有?”
阿赞?尼拉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刚站到一半,阿豹又是一脚踹在他的腹部。阿赞?尼拉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双手护住头部和腹部。
“说话!”阿豹抬起脚,又狠狠地踹了几脚。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阿赞?尼拉虽然被踹得在地上滚了几圈,却又慢慢地撑着地面,试图站起来。
他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
甚至连一丝伤痕都没有。
阿豹愣了愣。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看阿赞?尼拉。刚才那几拳,他可是实打实地打上去的,怎么可能一点伤都没有?
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筋,狠狠地朝阿赞?尼拉的背上砸了几下。
清脆的撞击声响起。那声音象是打在石头上,而不是人的身体。
阿赞?尼拉又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脸上依然挂着那副平静的表情。
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阿豹彻底恼羞成怒了。他举起钢筋,准备再次朝阿赞?尼拉砸去。就在这时,他的屁股突然被狠狠地踹了一脚。
阿豹惨叫一声,整个人扑倒在地。他回过头,发现踹他的人竟然是张志成。
“老……老大?”阿豹一脸不解。
张志成冷冷地瞪着他:“怎么可以对阿赞无礼?”
阿豹瞪大了眼睛,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张志成上前一步,作势要踹阿豹几脚。然而,就在他的脚快要落在阿豹身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脚竟然踩不下去。
而是他的整个身体都开始变得轻飘飘的。
张志成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他想要挣扎,但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就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起,缓缓地向后飘了两公尺。
那种感觉很奇怪。不是被推,不是被拉,而是像……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托着,轻轻地放到了别处。
张志成的双脚重新落在地上。他浑身冷汗淋漓,心脏狂跳不止。
“不要打他了。”阿赞?尼拉平静地说,“他只是个可怜人。”
张志成呆立在原地,脑海中回放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阿豹那些拳脚和钢筋落在阿赞?
尼拉身上,竟然没有造成任何伤痕。
而刚才那股让他离开地面的力量……
那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
他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在工地搬水泥的瘦削男人,并不是什么骗子或普通工人。他是真正的降头师,而且实力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张志成深吸一口气,压下内心的震惊,快步上前,恭敬地说:“请阿赞帮忙。”
阿赞?尼拉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身,注视着张志成。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人心。
良久,阿赞?尼拉叹了一口气:“你杀过很多人。”
张志成的身体一僵。这不是疑问,而是陈述。他低下头,一言不发。
“你身上不只煞气。”阿赞?尼拉缓缓说道,“还有一股将临之劫。”
张志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阿赞?尼拉又说:“本不该帮你。”他顿了顿,“但你身上的煞气非比寻常,我生平所仅见。我一生从未遇过敌手,是该会会这个对手了。”
“我答应你。”阿赞?尼拉说。
旁边的监工见到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连忙退到远处。
张志成心中暗自庆幸,觉得自己果然找对了人。他扫了那监工一眼,目光一冷,沉声道:
“阿赞,这不长眼的家伙竟敢如此对您,我这就替您出气,也算是赔罪。”
话音一落,他一挥手。阿豹立刻会意,掏出刀子,迈步向监工走去。
阿赞?尼拉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无形的墙,让阿豹瞬间停在原地。
“他何罪之有?”阿赞?尼拉转过身,深邃的眼神凝视着张志成,“他只是帮我修行罢了。”
张志成一愣:“帮您……修行?”
阿赞?尼拉走到监工面前。那监工早已吓得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阿赞只是淡淡拍了拍他的肩膀:“起来吧。”
监工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阿赞?尼拉转回身,看着满脸困惑的张志成:“我的法力已至化境,术法再修,也难有寸进。唯一的突破,不在术,而在心。”
他顿了顿:“《金刚经》有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肉身承受极限之痛与疲累,而心仍能不动如水,那便是破『我执』的契机。”
张志成似懂非懂,却不敢多问。
“在泰国,人人敬我为阿赞,处处奉迎,句句恭敬。”阿赞?
尼拉苦笑,“可那样的环境,反倒是修行最大的障碍。越被捧得高,越容易执着于『我是高人』这个念头。”
他望向工地那堆未完成的水泥——那些灰色的袋子堆在那里,像一座座小山,每一袋都是苦难的重量:
“所以我来到这里,当一个无名的工人。监工骂我,我便观照怒气的生灭;身体疲累,我便体会肉身的虚幻。当我能在烈日下搬水泥而心不起怨,被辱骂时仍心如止水——那时,我方能真正破『我执』。”
张志成听得头皮发麻。这辈子他杀人无数,从没想过世上竟有人把受苦当作修行。
“是……是,阿赞真乃大智慧。”他口中附和,心里却暗暗嘀咕:明明是日子过太好,间得没事找罪受。
阿赞?尼拉轻叹一声,摇了摇头——自己终究还是在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