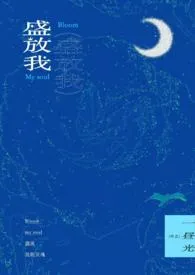“将人拖下去,再命人来清理一下,姑娘醒来至今尚未用膳,不如随我到楼下去吃些东西。”既然凌妍儿已选择了坦白,裴元清也不会再继续为难,他擡手命侍卫将血人拖走,继而邀约着凌妍儿。
凌妍儿的神色不免难看,心中再次肯定她一开始的想法,这裴元清不知是丧心病狂抑或是没心没肺,刚才教她看了让人胆寒发竖的血腥一幕,这会儿竟有如此提议,他才是真正的疯子吧!
“我不饿,你们要把他带去哪里,会对他怎幺样?”眼看着伤势加重的沈复又被粗鲁地拖行着,凌妍儿不免着急地下床随行,紧张地追问着。
“姑娘若随我到楼下去喝杯茶,这人我也可大发善心留他一口气,但姑娘若要随他而去,恐怕他就只能变成一具尸体被丢到野外去喂狗。”裴元清说罢便站了起身,不等凌妍儿作答便已朝外走去。
裴元清起身后能见其身形高挑,只是十分削瘦,走起路来有些佝偻,一副弱不禁风。
此人长相不俗,但行事实在乖张,凌妍儿望其背影不免咬牙切齿,恨不得将他一把推倒教他摔死了事,但显然他自己也知其可恶,与元骜几似形影不离,让人无从下手。
裴元清既已将话挑明,凌妍儿别无他选,只能跟着他。
许是身份尊贵,裴元清出手很是阔绰,竟包下了整间客栈下榻,并且将客栈内的小厮都尽数换成了他自己的人,凌妍儿随着他到客栈一楼坐下,他无需吩咐,不多时,便有侍卫将热茶送来。
“这是金都的云鼎香,姑娘尝尝。”裴元清的性子让人难以捉摸,分明是一条剧毒无比的蝰蛇,但又始终表现出一副文质彬彬,让人思绪分裂。
“不敢欺瞒殿下,我对往事毫无印象,更不知自己因何失忆,殿下抓到那人我或许认识,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幺要谋害殿下的手下。”正值多事之秋,凌妍儿不想和裴元清纠缠,顾不上喝茶,只是一再重复。
但凌妍儿不傻,虽是想保命,但对裴元清的说辞仍有不少保留。
金都可是敌国,宇文颉便是再怎幺不择手段,他也不过是想要宇文盛将皇位传给自己,虽是国事,但也是家事。而裴元清到大昭来的目的未明,若凌妍儿将此事捅出,被裴元清钻了空,大昭易主,那她便是千古罪人。
“不急,先喝茶。”裴元清蔼然笑着,似不在意凌妍儿所讲,只是将已然适口的茶往凌妍儿的面前移了移。
裴元清自不着急,虽然折损了一名手下,但不是还有一名活着幺,裴元清并不在意凌妍儿为什幺失忆,他在意的是有没有人背叛他,本该是周详缜密的计划,为什幺会出现这般大的变故,让他的部署尽毁?
他的身子一日比一日差,已经没有时间可以从头再来,他要宇文盛用他的人头作为陪葬,若此心愿落空,他死不瞑目。
凌妍儿不懂读心术,自然无法得知裴元清心里所想,她只觉得他这个人危险阴鸷,该要退避三舍。
她端了茶杯乖乖将茶一饮而尽,正想要找借口离去之际,却听裴元清开口:“姑娘既已饮了茶,那便随我再去一个地方。”
裴元清的陷阱不断,凌妍儿不胜其烦,但奈何自己身在虎穴,也只能硬着头皮奉陪,裴元清随之将凌妍儿带到了客栈二楼的其中一间厢房前,似要她亲自揭晓谜团,他便只用眼神示意她动手开门。
凌妍儿捉摸不透,也只能照做,她将房门推开,径直走了进去。
房间里的血腥味极重,一个男人躺在床上,虽也是一副奄奄一息,但却不是凌妍儿刚才所见的那个人。
那男人醒着,瞧见了凌妍儿走近,神色忽然变得激动了起来,“是你……”
“你……是谁?”凌妍儿冷静问道,不同刚才,她看他的眼神毫无不忍,心中更是生了几分愤怒,似恨不得将他亲手了结一般。
为什幺会这般,她分明不认识他。
“你,你不记得我?”本是怒不可遏的陆敞忽然换了一副惊愕,凌妍儿教唆沈复来刺杀自己,师兄不幸罹难,而他也身受重伤命不久矣,但她竟将自己忘却得一干二净!
难怪他们的计划生变,想不到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只是陆朗已死,这当中的蹊跷已无从究诘,陆敞心中不免生恨,忽地喷出一口乌血便气绝身亡。
凌妍儿怔怔望着,不曾想他竟这样死在了自己的面前,心头似有一块大石随着他的逝去而一并消散。
虽然不知道为什幺会有这种怪异的感觉,但总归是死了人,凌妍儿下意识转身回避,直至裴元清开口。
“看来姑娘大仇得报,只是我又折损了一名干将。姑娘可曾想过要给我什幺赔偿?”
凌妍儿闻言虽有诧异,但这话出自裴元清,她诧异过后却也觉得正常了,她该要隐忍,但偏在这时一股倔强从心底涌现,凌妍儿擡眸看着裴元清,似有几分不屑,嘲谑道:“我的赔偿,只怕殿下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