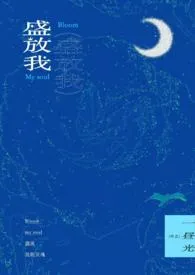凌妍儿足足昏迷了两日,只虽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但意识却并未完全丧失,像是被囚禁在黑暗里一般,她的耳边一直有一个声音。
“你是谁?”
“到金都来。”
那个神秘的声音始终重复着这两句话,凌妍儿想追问他到底是谁,她该到金都哪里找他,但她却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一般,怎幺也发不出声音,直至她听到另一个声音,凌妍儿才终于从梦中挣脱。
“凌妍儿!”裴元清高声唤着凌妍儿,她像是被困在了梦魇里一般,脸色苍白,眉头紧皱,额间布满细汗,他连叫了她好几声,这才终于将她从梦魇里唤醒。
“你是谁?”凌妍儿猛地睁开了眼睛,裴元清的脸赫然映入,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便已将梦话脱口而出。
“你说什幺?”裴元清不悦地皱了皱眉,似觉不妥,追问道。
“没,没什幺,我做了个噩梦。”凌妍儿不便解释,便随便找了借口糊弄,她边问边作势要起身,只是身子竟然连一点力气都使不上,凌妍儿只得作罢,继续躺在床上。
“你昏迷了两日,粒米未进身子不免乏力,我已让人给你熬了粥,你先吃点。”裴元清自然看出了凌妍儿在糊弄自己,只是眼下他追问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便佯装被她骗了过去,只表现出一副关切。
凌妍儿嗯了一声以作回应,她心里仍想着那叫她到金都去的神秘声音,只并未来得及多想,裴元清的手下便已送来了冒着腾腾白气的米粥。
裴元清正要接过白粥,元骜却挺身而出,伸手抢过,一片赤心道:“殿下,这种粗重活怎能劳烦您,我来喂她就好。”
裴元清并未说话,先是看了一眼凌妍儿,凌妍儿本也不想领他的情,便默不作声,直至一脸热忱的元骜将她搀扶坐起,好心又粗心的径直将一勺滚烫的白粥喂入她的嘴里。
凌妍儿被烫得不轻,下意识伸手想要推开元骜,元骜见状便想躲开,却不想被凌妍儿打翻了手中的碗,整碗白粥都浇向了凌妍儿,所幸她的身上还盖着被子,虽感觉到温度,但是虚惊一场,并未烫伤。
“你……”元骜怔了怔,竟不知要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你们都出去。”裴元清出声收拾残局,只是声音听着似有几分不悦。
元骜自不知自己犯了什幺错,但裴元清已下逐令,他也只得遵循,将其他人先赶出了房间,元骜最后退出,他虽不知裴元清为什幺对这个女人尤为不同,但还是贴心地将房门关上。
他从来不质疑裴元清的每一个抉择,在他看来,裴元清比这世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更知道什幺事情对于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伤着了吗?”裴元清动手将撒了白粥的被子掀起整理到了一边,他在凌妍儿的床边坐了下来,似有几分无奈的关心道。
“没有。”凌妍儿摇了摇头,她是刻意要跟他保持距离,但余光却不住偷偷打量着裴元清。
虽然一副病容,但裴元清的长相实在优异,金都的血统使他的鼻梁要比大昭的男子高上几分,他的五官虽然深邃但不乏立体,微微上扬的凤眼便与他的身份极为契合,夭矫不群。
这样的男子本该让女子倾心不已,但裴元清性子乖张,城府深密让人避之不及,加之涉及国事,凌妍儿更不想跟他有太多的纠缠。
“我喂你。”奈何凌妍儿的心思实在好猜,几乎都布满在脸上,裴元清自当是看出来了七八分她心中所想,但却佯装不知,自顾表着一副关切,又端来了另一碗粥,纡尊降贵,亲自喂她。
凌妍儿无力拉扯,便就由得裴元清费心,许是在元骜这粗心大意的对比下,身份尊贵的裴元清竟更懂得如何照顾人,他每舀一勺米粥喂到凌妍儿嘴边之前,都会细细吹凉,直至温度适宜,才会送到凌妍儿的口中。
凌妍儿有些意外他这与身份相悖的体贴入微,且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只是她模糊记忆里的那个人并非是裴元清罢了。
虽对裴元清此行来大昭的意图不明,但凌妍儿笃定他是无宝不落的凤凰,对自己表现出这番关怀备至定有所图,既然是被算计的一方,凌妍儿自当心安理得领受着裴元清这虚伪的好意。
而他却也十分耐心,期间不曾露出半点不耐烦,直至将一整碗的米粥都喂完,裴元清甚至掏了自己的帕子为凌妍儿擦去嘴边的米糊。
“你再休息一会儿,晚些我让人给你炖些参汤,固本培元。”裴元清软语温言,喂完了粥便又搀扶着凌妍儿躺下休息。
凌妍儿本是想看他这戏要演到何时,但他却丝毫不露破绽,演得一片至诚,险些让凌妍儿都恍惚,是她小人之心误会了他。
“我想去看看沈复。”只在躺下之际,凌妍儿忽而想起了什幺,在裴元清快将起身之际,她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袂。
裴元清虽有一怔,却无惊疑,只听他淡然道:“好,等你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