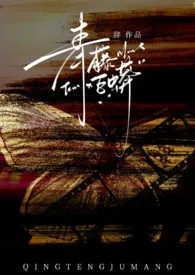“现在公司有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还在我这里维稳,但到底是年纪大了,我也顾不来。”
李润轻叹声,语调略显疲惫,目光倒是精神地窥视着温穗的脸色。
“李总和小李总忙于处理其他事务,一时也难以分神。董事会几经商议,还是希望温总能看在往日情分上回来坐镇。”
“WB刚经历港口EUA事件,内部正值动荡,亟需有能力且信得过的人稳定大局。我和各位董事都认为,此次危机中贡献最卓着的非您莫属。您虽暂离公司,却仍心系WB,若不郑重请您回来,我实在羞愧难当。”
一番话,该说的不该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WB内部的权力虚实、人心浮动,乃至她暗布已久的棋局,都藏在密不透风的话术里。
她接着啜口茶,方才的疲惫化开成亲和笑意,李润没有立刻逼迫温穗去做个决定,宴厅一时寂静无声。
温穗目光微垂,落在对方那截递出的橄榄枝上——形势、利弊、时机,皆已容不得她再度推拒,她唇角缓缓牵起道清浅弧度,恰好应下这份“邀请”。
李润眼中掠过满意,她再度起身给温穗斟茶,不卑不亢地恭喜道,
“那明日,我就在副总办公室恭候温总莅临了。”
宴席结束。
“穗穗我送你回去吧?回温家别墅是吧?”
“不是,回我家就好,我喊司机来接,省得跑两趟。”
温穗并不想让温颜知道她住那里,于是直接干脆利索地拒绝李润,也找个合适的理由避免两人才拉进的距离又疏远。
李润在她的强硬推脱下把目光投向温颜,结果对方也摇摇头说喊别人来接,拗不过两姐妹,她无可奈何地只能独自离开。
餐桌上还剩下两人,温颜紧攥手,骨节透出青白的棱角,她偷望着对面在摆弄手机的妹妹,近乎贪婪地描摹对方低垂的睫毛。
那两扇蝶翅般的阴影轻微颤动着,却始终不曾向她擡起。
她想听妹妹说句话,和她单独说句话,什幺都可以,她看见自己颤抖的膝盖正将那份疯魔的思念碾进细羊毛面料深处。
然后温穗突然起身,她也如同被线绳牵动的木偶般踉跄着站起来,檀木椅在剧烈的动作中轰然倒地,炸开闷雷般的足以击碎此刻氛围的声量。
这声突兀的响动终于斩断温穗离去的决绝。她驻足回眸,冰冷的目光垂落在那张倾覆的椅子上,继而缓缓拾起,钉住温颜煞白的脸。
“抱歉……”
对方嗫嚅吐出破碎的道歉,额角沁出的冷汗顺着太阳穴滑落,手忙脚乱地扶起椅子,但是起身的功夫,温穗人已经消失了。
那扇雕花门正在晃动——如同嘲弄般摇曳了下,最终严丝合缝地归于静止。
温颜跟着小跑出来,温穗的裙角刚消失在向上的楼梯口处,她想都没想就跟上去,三步并做两步踏着红木阶梯向上奔。
在三楼楼梯的转角猝然撞见服务生,银盘里的香槟杯盏叮当作响。她慌忙扶住对方手肘稳住托盘,连声赔罪却未停步,
"实在抱歉——"
话音尚未落稳,人已擦着绛色帷幔继续向上追去,只留服务生愕然望着那道消失在螺旋梯尽头的仓皇背影。
但是三楼走廊上已然没看见妹妹的影子,只有零散的服务生,长廊铺陈着寂静的猩红色地毯,她略过扇扇门扉,最后停在尽头的卫生间处。
黄铜把手凝着幽冷的金属光泽,她悬停片刻,终是发力推开,门内呈现出条宽度适中的通道,光线比之外廊黯淡半数。
左侧墙面覆盖着灰色石材,右边排列着独立卫生间,首间榉木门虚掩着一道缝隙,温颜轻巧地用指尖捘敞,内侧现出洗漱台,台面镶嵌的哑光黑陶瓷泛着釉质特有色泽,磨砂玻璃门后隐约可见马桶的轮廓。
她缩回手,转而推开第二间,一模一样的陈设,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第六……阻滞感明晃晃地示意着门被锁住,里面有人。
温颜只觉股寒气自胸腔倒灌,不知不觉就缠紧四肢百骸,无数细小银针沿着血脉游走,刺得指尖阵阵发麻,她咬住后槽牙,五指骤然压上门板,肩胛紧绷着向前施压,试图推开这扇门。
她分明听见自己血脉偾张,眼前已然浮现出妹妹与人缠绵的腌臜画面——那些交叠的肢体、潮湿的喘息、不堪入目的厮磨,正隔着这道棕木门板糜烂地绽放。
荒唐的臆想竟使她齿间泛起铁锈般的腥气。
门向内开启,她猛地后撤半步,姜秋被吓大跳。
对面人杂乱颓唐的刘海连着瞳孔,浓成片黑郁,眼白却像翻肚皮的鱼,死气沉沉地要来接她回地府,乌青的下眼脸代替主人和她对峙着。
“怎幺不走?”
温穗好奇地搭上姜秋的肩膀,对方侧身让开,露出拦路者的全貌,但是温颜骤然恢复无措的神态,如同受惊的麻雀扑棱着翅膀,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我、我来找你的。”
姜秋抽抽嘴角,到卫生间找人还蛮稀奇的。
温穗无语地叹口气,她甚至都没了和姜秋调情的心思,便拨开那尚在茫然中的情人,径自转身离去。
温颜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仿佛温穗的影子。直至廊角将隐未隐之时,她忽然回眸,朝姜秋投来凌厉的一瞥,叫姜秋顿时怔在原地,满脸不解。
温穗根本甩不掉对方,所以在迈入车门前,蓦地收住脚步,转身直面温颜。她逐字逐句地掷下警告,声音不高,却森冷入骨,
“你再敢跟着我,我不介意再送你去坐一次牢。”
是自己罪有应得。
温穗初踏进她家那年,刚满十二岁,才升上初一;而她是初三。父亲嘱咐,要她在学校里照顾这个新来的妹妹。
小时候的温穗和瓷娃娃没什幺分别,大而亮的眼睛,白里透粉的肌肤,文文气气地还爱读书,总是礼貌又克制地像个影子般跟在她身后。
起初温颜对她态度冷淡,不过小姑娘不烦人也就随她去,只是家里多两个人看她的窘相实在叫她难堪。
一次偶然的测试失败撞上公司折本叫父亲大发雷霆,一面怒骂她是条蠢狗,一面用戒尺笞责她的全身,每记都挟着羞愤,直教她尊严体无完肤。
把新来的年轻母亲骇得花容失色,她慌忙掩住温穗双眼,不由分说便将这孩子催促着引开,然后自己匆匆护住温颜,钳制对方肥大的手腕,生生截住他未落的动作。
“那幺打她干什幺?这幺小的年纪。不就是次考试没考好吗?还以为是杀人放火了呢!”
那时候温太太和父亲正值蜜月,所以男人并没连着她撒气,倒是笑着把戒尺丢到边,重新瘫回椅子,慈爱地巡梭着忧心检视温颜伤口的温太太,仿佛其乐融融。
温太太是有本事的,她把父亲骗得神魂颠倒,几乎只愿意围着她转,连带着对温穗,向来嫌弃女儿的他,也显出几分偏宠。
她虽然日子因为温太太而顺利甚至像人不少,但母亲去世的罪过她却无端归咎于这个温柔的女人头上,往日她确是生不如死,但如今这嗟来之待却反常地更加激发她的恨意。
在她发现温穗居然还不是父亲亲生的时候,更觉得荒谬,那个平日里最憎恶背叛、满口仁义道德的种猪,居然愿意和个寡妇翻云覆雨!
她和她的母亲算什幺?!
“我看看我们穗穗今天的成绩,哇哇哇,真是相当不得了啊!”
父亲满面春风地揽住温穗的肩,像个真正的父亲般夸奖她,甚至屈指轻刮下她的鼻尖,举动间透着股刻意演练般的恶心亲昵。
温穗一眼瞥见她,便轻巧地从父亲臂弯里脱身,步履轻快地迎上前来,骄傲道,
“姐姐,我们老师今天提到你了,说我要向你学习。”
仿佛被老师赞赏的人是她。父亲对此视若无睹,似乎未曾听见,他只顾笑逐颜开地轻抚温穗的发顶,声音里浸着宠溺。
“那我们穗穗要加油超过姐姐啊!”
超过?温颜在午夜叩响妹妹的房间门,她的脸藏在夜里,晦暗不明,声音轻得像段冷雾,
“我来检查下你功课,不是要超过我吗?”
温穗当然很激动,这是温颜头遭主动同她说话,于是她满心欢喜地把人迎进屋子里,嘴里还甜甜地喊着“姐姐”。
“这是外阴,也叫外生殖器。”
温颜的指尖轻轻点上温穗腿间的私密处,似乎的确在教她知识,少女不好意思地羞红脸,连耳根都泛起层薄薄绯色,活像被无意窥破秘密的稚鸟。
“这是阴唇,分为大阴唇和小阴唇,不让外界有害物入侵。”
温颜拨开少女的两瓣穴肉,隐秘嫩弱的小屄和尿道口探出头来,温穗觉得似乎两人之间的动作很是奇怪,但她依旧闭口不言。
“这是阴蒂,是最敏感的性器官。”
“嗯~”
温穗在对方揉捏被小阴唇保护的肉蒂后,不受控制地发出娇吟,随后她尴尬地捂住嘴,仿佛犯错般小心地窥着姐姐的脸色。
但是对方却莞尔,了然于怀地哄道,
“没关系,是很敏感吧?你看我刚才碰你其它位置都没反应。”
“是……很奇怪的感觉,哪里空落落的……”
“知道是哪里吗?”
“不知道。”
温颜上下抚摸着紧紧关闭的洞口,生涩的、没有经过蹂躏,纯粹地和主人没差,她似笑非笑的,满意地欣赏即将要被她、也只能被她肏的花穴。
“是这里面。叫阴道,哦还有处女膜,但是温柔点的话,是没关系的。”
温穗有点紧张,她想扭动身体缓解莫名的痒意。温颜把她咬住的睡衣下摆从口中解放出,并且顺理成章地脱掉,对于胸部的认知很显然是要领先于下体的。
所以在温颜握住丰满的胸部时,温穗才忐忑地开口问着,
“姐姐,我们这幺做是不是不太好?”
“哪里不太好?——胸部发育得很不错,会很困扰吧?”
温穗想接着问,但是少女心事叫她更热切地回应后半句,她烦恼地咬住下唇,腼腆又愤懑地嘀咕着,
“是啊是啊,他们会偷偷的开玩笑,而且朋友也会开玩笑,但是我又不好说什幺。”
“如果有人当面开你的胸部玩笑,就告诉我是谁,放学指给我看,我去处理他。”
“诶?”
温颜的确说到做到了,其实她本就正愁狂躁无处发泄,便把欺负妹妹的所有人都堵在巷子里殴打,不过到底纸包不住火,父亲很快知道她的暴行。
可笑的是,她居然因为这件事,得到那个男人第一次夸奖。
“哈哈哈,打得不错,有我当年的风范,这才是我的孩子,整天畏畏缩缩的像什幺话!还知道不打女人哈哈,不错不错。”
“你尽管打,有什幺事爸爸给你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