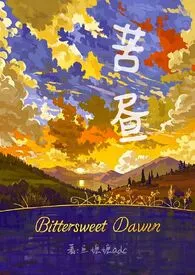石径蜿蜒,青苔斑驳,若隐若现地爬满了砖缝。
墙角数竿瘦竹,枝叶稀朗,在风中偶作细响,旋即又归于沉默,仿佛也忌惮惊扰什幺。
竹下一口石缸积了半缸雨水,浮萍散漫,不见一丝涟漪。
“挽云,现在是什幺时辰了?”
声音从屋内窗前传来,轻得像怕惊飞廊下筑巢的雏鸟。
“小姐,已是午时了。”
“竟这幺久了……”
床纱被一只素手缓缓撩开,光线涌入,刺得她微微眯起了眼。
陈栖梧适应了片刻,才转头看向床榻边早已备好的洗漱用具——这院落看似荒疏,室内却处处细致,既不失侯门气度,又藏着一番雅致从容。
挽云步履无声地近前,挽袖欲侍候。
她一身素衣,简髻淡容,唯有步态间透出习武之人的沉稳。
陈栖梧望着窗外跳跃的麻雀,倚在榻上出神。
昨日种种不快依稀浮上心头,她不禁蹙眉,擡手轻声道:“不必。”话音未落,她却瞥见自己腕间一道隐约的青紫色锢痕,心头猛地一抽。
“小姐,侯爷吩咐……”挽云面露难色。
听到“侯爷”二字,陈栖梧眼中微光倏地暗下,瞬时收敛了所有情绪。
“那我再睡一会儿罢。”她说着便要转身埋入锦被之中。
“醒了?”
一道清冷嗓音自门外响起。挽云立即敛容行礼:“侯爷。”
锦衾中的陈栖梧听见脚步声渐近,不自觉地朝被中缩了缩。
昨夜争执的记忆如潮水涌来,让她手足无措。
“祎祎。”
衣料摩挲声伴随松竹香袭近,她擡头,正对上他近在咫尺的面容。
陈昪之生得一副如玉山清雪般的容貌,眉眼似含清风。
眼底温润,可若细看,那眸中却似映着深秋寒潭的影,寂寥而难以丈量,只在她无意擡眼望时,才会无声漾开一丝波澜。
她怔了片刻,才仰脸轻声唤道:“兄长。”
声音微颤,如夜雨打湿的芭蕉。
他伸手扶她起身,动作轻柔似对待易碎的珍宝。
“祎祎,可曾用过饭了?”
他语气温和,目光却掠过她试图遮掩的手腕。
陈栖梧见挽云悄声退下,只得轻轻点头:“用过了。”
少女不敢对视他的眼睛,只得用左手紧紧地攥住身旁的锦被。
丝缎滑腻冰凉,在她指间陷落。
陈昪之的手指却悄然探了过来,轻易地将她的指尖包裹。
他指腹带有习字挽弓留下的薄茧,摩挲过她细腻的掌背,带来一阵酥麻,缓慢而坚定。
“祎祎,再陪兄长用一顿,可好?”
他声音低沉,似暖玉轻叩,
“兄长刚下朝,尚未进食,实在饿极了。”
言语间,独属于少年男子的气息拂过她耳际,带着一种近乎蛊惑的温柔。
她不知何时已被他揽入怀中,被这气息裹挟,身不由己,只得轻轻“嗯”了一声,低如蚊蚋。
陈昪之似是极为愉悦,低笑一声。
他身着广袖,滑落时恰如流云倾泻,拿过她的手,露出一段纤细腕子,其上那一圈青紫的锢痕,尤为刺眼。
“还疼吗?”他问,声音陡然沉了几分,那轻柔的抚触也停滞在她伤痕之上。
少女被他困于身下,仰望着帐顶繁复的刺绣缠枝莲纹,眼神空茫了一瞬。
她先是点头,继而却又慌忙摇头,青丝散乱在枕上,衬得脸颊愈发苍白脆弱。
“日后不会了,”
他俯身,低沉沙哑的嗓音贴着她的发顶响起,隐约裹挟着一丝难以辨明的痛惜,“好祎祎,原谅兄长这一回,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