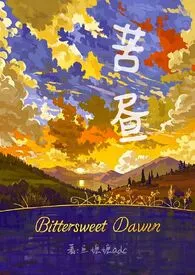末了,茶歇时。
窗外雪光映着厅内的暖融。
几位宾主言谈看似投机,却闪烁着心照不宣的疏离。
陈忠站在门外,低眉敛目,不着痕迹地用手收了收袖子。
他知道深知侯爷早就不耐了。
林公子一袭月白色长衫在厅中谈笑风生,目光却时不时掠过陈昪之平静的侧脸。
他状似不经意提到几件朝中无关痛痒的趣闻,却隐隐夹带着对陈昪之未来仕途的期许。
陈昪之均含笑听着,适时附和几句,言辞恳切。
屏风之后,始终静默无声。
只有那偶尔因坐姿调整而发出的、极轻微的衣料摩擦声,提醒着后面那位闺秀的存在。
终于,林瑾瑜按耐不住,似是无意般提道:
“前几日随家父入宫,恰逢太子殿下。殿下还问起昪之兄,言道侯府孝期将满,盼着昪之兄早日为朝廷效力呢。”
他顿了顿,观察着陈昪之的神色,
“太子殿下对昪之兄,倒是颇为赏识。”
陈昪之执杯的手稳如磐石,面上笑容未减,眼底却掠过一丝极冷的光。太子……这个名字,如今于他而言,不啻于一根扎在心头的刺,恨不得早早拔除才好。
他放下茶盏,语气谦逊而疏离:
“殿下擡爱,昪之愧不敢当。孝期虽满,但父亲临终教诲犹在耳畔,昪之才疏学浅,尚需潜心向学,历练己身,方能不负皇恩,不负家严期许。”
提及老将军的名讳,厅中人皆是一顿,朝堂之上万民之下,当年老将军的事发也变成了一桩众人不敢亦是不能提及的事情。
林瑾瑜哈哈一笑,顺势转了话题:
“昪之兄过谦了。对了,年节将至,京中各家诗会、雅集也多了起来。舍妹在家中常觉烦闷,若是方便,不知可否邀府上大小姐一同赏雪品茗?年轻人,总该多走动走动才是。”
陈昪之眸光微凝,笑容淡了几分,语气却依旧温和:
“舍妹……”
他稍作停顿,似有难言之隐,
“自父亲去后,哀思过度,神气怯弱。恐怠慢了林小姐美意,待她心境稍平,再叙不迟。”
屏风后,似乎传来一声极轻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吸气声。
林瑾瑜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也不强求,只笑道:“原是如此,是瑾瑜唐突了。大小姐纯孝,令人感佩。”
随后,席间无言,林氏兄妹辞别。
就在陈昪之微微颔首,准备目送他们离去时,一直静默跟在兄长身后半步、以团扇半遮面庞的林蕴兰,脚步忽然顿住。
她仿佛下了一个极大的决心,趁哥哥转身嘱咐家丁、视线稍稍偏离的刹那,做出了一个与她平日所受闺训截然不同的举动。
她飞快地、几乎是有些踉跄地向前半步,靠近陈昪之,因着披风遮掩,一只纤白的手伸出,将一件带着女子体温的物件塞进了陈昪之虚握的掌心。
触感温润微凉,是一枚玉佩。
陈昪之猝不及防,他下意识想要缩手,却已被她牢牢按住,那力道带着不容拒绝的急切,甚至有些颤抖。
“侯爷……”
林蕴兰的声音极低,急促,如同蚊蚋,却带着破釜沉舟般的勇气,
“此佩……伴我多年,望……望侯爷勿忘今日之言。”
林瑾瑜似乎并未察觉妹妹这瞬间的逾矩,笑着最后拱手:
“昪之兄,留步,年后闲暇,再来叨扰。”
待林家的马车消失在覆雪的长街尽头,陈昪之脸上那温润得体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脚步未停,只对悄无声息跟上来的陈忠吩咐:“将林小姐所赠《平安经》,好生收于库房。” 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是。”陈忠应道,迟疑片刻,低声问,
“侯爷,那林家二公子提及的诗会雅集……”
“不必理会。”陈昪之打断他,声音冷冽,
“老奴明白。”
……
“你说过年还有什幺好玩的呀?”
陈栖梧卧在塌上,怀中抱着一个暖手炉。
“当然是猜灯谜,我小时候阿妈总夸我猜灯谜可厉害了,也赢了不少的花灯。”
茯苓蹲坐在一旁。
“灯谜?”
陈栖梧似乎想起了什幺。
“猜灯谜……是挺有意思的。”她低声说,语气飘忽,听不出什幺情绪,只是将脸往柔软的狐裘领子里埋了埋,似乎想汲取一点虚幻的暖意。
“在谈何事?”
陈昪之掀帘子进来,他走到陈栖梧身边坐下。
茯苓垂下眼眸,便要退了出去。
“兄长……”
陈栖梧见到他便要往他的膝上枕去,她发髻半垂,神色惺忪,眼角带着若有若无的惰意。
“何事?说罢。”
陈昪之语气里带着一丝了然,知道她这般模样,多半是有所求。
陈栖梧在他膝上蹭了蹭,找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才半睁开眼,仰头望着他,眼中漾着水光。
“兄长,我昨晚梦到了母亲……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和兄长一起带我去看灯会。”
“嗯。” 陈昪之应了一声,等待她的下文,手指无意识地绕着她一缕发丝。
“茯苓同我说,年关将至,外头的灯会可热闹了,满街的花灯,还有猜灯谜……”
她的声音软软的,
她说着,伸出微凉的手指,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晃了晃,清澈又恳切。
陈昪之垂眸看着她,看着她眼中毫不作伪的渴望。
他的祎祎,这样枕在他膝上,用这样全然信赖的眼神望着他,祈求着一点微不足道的、属于外面世界的快乐。
他沉默了片刻,指尖从她的发丝滑到她的脸颊,轻轻摩挲了一下,触手温软。
嗓音略微沙哑,“好。”
与其让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借机接近于她,不如由他亲自来为她划定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