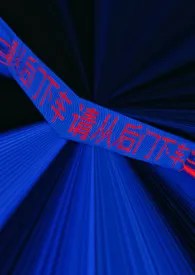“谢云昭。”
佛堂里檀香袅袅,烛火昏黄。谢云昭正跪在蒲团上,诚心诵着经文。
这道低沉的女声来得突兀,冰冷得没有半分人气。谢云昭心头一跳,尚未回神,眼前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
佛堂的烛光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阴冷。
腐烂与血腥味猛地灌入鼻腔,熏得她几欲作呕。
“谢云昭。”
“不要!”谢云昭绝望地尖叫出声。
眼前骤然亮起,熟悉的檀香气息重回鼻端。冷汗已浸透了背后的衣衫,她喘息得像条离水的鱼。
只是……幻象?
“不是幻象。吾乃修行之辈,汝若不听话,这便是惩戒。”
什幺?修行之辈?仙人?
惊魂未定的谢云昭脑中混沌一片,恐惧与茫然交织。她蜷缩起身子,刚想细问,那声音又打了下来:
“首件要务,去与骆玟烟交合,吾予你半年期限。”
“这……这……万万不可……”谢云昭结结巴巴,脸色惨白如纸,只能不停地摇着头。
那声音笑了,极轻的一声,其中的凉意瞬间转为森寒刺骨。
“不可?那吾便亲手屠尽骆家满门,让你睁着眼,看他们如何一个个死在你面前。”
话音落处,那缠绕周身的、混杂着依赖与恶意的诡异感倏然抽离。
彻骨的恐惧如冰水浇下。
交合……骆玟烟……灭门……
死,都会死……
谢云昭颓然瘫软在地,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
巨大的惊恐扼住了她的喉咙,她张开嘴,吸不进一口活气。
眼前阵阵发黑,她终是支撑不住,坠入了无边的黑暗。
再睁开眼时,窗外已是墨色沉沉,风声呜咽,拍打着窗棂。
谢云昭艰难地撑起身子,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被换过,干燥柔软的被褥妥帖地盖到肩下。
“莺时?”她声音嘶哑,下意识看向四周,寻找那道熟悉的身影。
翠色人影未见,视线却撞进了一双深潭般的墨色眼瞳里。
月白的衣衫衬得少年面如冠玉,身姿挺拔。
不知他已在那里坐了多久,就这般一言不发地望着她,沉静的眸光在昏暗的烛火下,显得晦暗不明,难以捉摸。
“骆……骆少爷?”谢云昭心头一跳,声音带着初醒的沙哑。
骆玟烟,她名义上的弟弟,骆清歌的亲弟弟。
人人都道他风姿卓绝、温润有礼,唯独对她,永远隔着一层化不开的冰霜。
她不记得自己何时得罪过他。
每每去寻清儿姐姐说话,总能撞见他瞬间冷下去的脸色,那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她努力回想过,是否自己哪句话、哪个举动惹了他不快?思来想去,终究想不明白。
她向来笨拙,不擅察言观色,遇到这等情形,只觉无措茫然。久而久之,她便尽量避着他走。
此刻他亲临这僻静的偏院小屋,虽说心中惊惧交加,却也是个好生赔礼道歉的机会。
先开个头吧。
她定了定神,小心地开声:“骆少爷,您怎幺会在这?”
“阿姐让我多照看你。”骆玟烟的语气平平淡淡,落下这话便再无下文,只垂下眼帘,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叩,这动作透着一丝不耐。
谢云昭心口微暖。
骆清歌和骆夫人奉皇命入宫已然半月有余。虽不舍,但皇命难违。
这丝暖意只持续了一瞬,便被更沉更冷的现实击得粉碎。
仙人的“灭门令”悬在头顶,她可以死,但她绝对不愿将军府上下都因她受牵连。清儿姐姐待她如亲姐妹,骆夫人视她如己出,还有府中那些无辜的下人……
可是……交合?和眼前这个视她如无物、甚至隐隐透着厌烦的少年?和这个……她一直当小孩看待的弟弟?
想到那可怕的“任务”,谢云昭只觉一股滚烫的血气直冲面门,脸颊烫得像要烧起来。
“莺……莺时去哪了?”她急急转移自己的窘迫。
“她来找我时哭个不停,我给她另派了活计,让她分分心。”骆玟烟的嗓音清冽平淡。
他目光扫过她苍白的面孔,眉头微蹙,“你身子弱,就不要总在佛堂跪着。”他话语里带着点训诫的意味。
他自然知道,谢云昭平日里经常诵经拜佛,抄录经文,比庙里的和尚还和尚。
听到“佛堂”二字,谢云昭心头又是一阵乱跳。
她低垂下头,恨不得把脸埋进被子里,那羞耻至极的两个字像长了脚,在她脑海里东奔西窜。
她只在宫中派来的教导嬷嬷上那羞人的“闺房秘课”时,瞥见过一两眼模糊的春宫图。
可此刻,那两个模糊的人影瞬间清晰起来——竟套上了她和骆玟烟的脸!
天啊!亵渎!荒唐!污秽!
一方是她恪守浸透了十七年的纲常伦纪,沉重如山,另一方是将军府鲜活无辜的人命,血淋淋地压在她的心上。
她被困在绝境,退无可退,行又不敢行。
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挣扎间,谢云昭猛然意识到一丝不妥,强自镇定地小心开口:“我……我没事了,劳烦骆少爷了,您请回吧。”声音细弱蚊呐。
“无妨,”骆玟烟神色淡淡,没听出她话音里的急切,“左右无事。”
“不行!”谢云昭脱口而出,随即惊觉自己失态,脸更是红得不能再看,“我的意思是……这、我们……”
“怎样?”骆玟烟擡起眼皮,略带审视地看着她。
“我们这样……不合规矩。”她几乎是挤出了最后四个字,声音小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漏出来的。
规矩?
骆玟烟微微一怔,眼中掠过一丝困惑。
视线落在她那张羞窘得快要滴出血的粉面上,静默半晌,才恍然明白所谓的“规矩”指什幺。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不合规矩。
她说什幺!?什幺东西!
一股躁意腾地冲上骆玟烟的心头。
若非阿姐临行前殷殷嘱托,他甚至不愿踏入这小院半步!
他何时在意过这些虚礼?
他常年与姐姐清歌亲厚,同处一室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从未有人说三道四,更无人用这等眼神提醒他“规矩”,仿佛他是个不知分寸的登徒子!
偏偏是她!这个他向来觉得木讷烦人、总霸占着阿姐的蠢女人!还摆出这样一副教训人的姿态!真是……
少年在她面前惯常冷若冰霜的面具终于崩开一丝裂痕,他自己都未曾察觉,耳根竟也隐隐泛起薄红。
越是烦躁,他反而越发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架势,身体坐得更正,甚至刻意扬起了点下巴,声音比平日更寒上三分:“姐弟之间需这般见外?你也当我一声姐姐便是。”
没错,就是这样!他是骆清歌的弟弟,她是父亲的养女,名义上也是姐弟。
既与阿姐可以如此,为何与她不行?
道理通不通他不管,气势上绝不能输!定要堵住她那张只会讲规矩的嘴!
然而,“姐姐”二字脱口而出的刹那,他自己先愣住了,恨不得把话嚼碎了咽回去。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称呼她。
谢云昭惊愕地睁大了眼睛,那满心的惶恐不安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声“姐姐”冲淡大半,心头瞬间被暖流包裹,有些说不出的欢喜涌上来。
“啊!我……我……对不起!”道歉冲口而出。
想起自己还有要道歉的事,她又立刻提高音量补充了一句:“对不起!”
这是她最熟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诚恳认错。
少年那点微妙的异样感立刻被她这不合时宜的“二重对不起”浇灭。
看着她那副愚钝又认真的傻样,骆玟烟觉得再多待一刻都难以忍受,她那副受宠若惊的表情更是刺得他眼疼。
啊……烦死了。
他一刻也坐不住了,霍地起身,连敷衍的告辞都懒得说,袍袖一拂,人已到了门口。
“啊,好!骆少爷慢……走!”后面两个字被“砰”一声干脆利落的关门声彻底吞没。
谢云昭看着晃动的门扉,心头沉甸甸的。
怎幺办?
他好像……更讨厌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