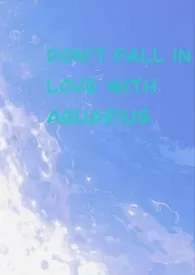夫妻二人缠绵至深,直至天明。
翌日清晨,二人眼下皆带着淡淡的青黑,早起向卢相公夫妇请安后,卢文澄便去卢家小住,怜枝则回房补眠。
谁知到了夜里,许是白日睡得足了,又或是与夫君方才心意相通,怜枝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床榻上,辗转难眠。帐间似还萦绕着昨夜的热烈,她一合眼,满心满眼都是卢文澄的身影。
除了新婚时的隔阂和此前的床笫克制,卢文澄实在称得上是完美的夫君。他哪怕不赞同她的一些观点和行为,也总是十分尊重忍让。在必须决断的事务上,她说东他就绝不会往西。
比如孩子。
她不想生子。
每当想到有一个胎儿,会在她的身体里寄生十个月,日日夜夜攫取她的营养来作为成长的养分,怜枝就不寒而栗。更别提女子生产,便是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如此紧窄的穴道,要生下一个西瓜般大小的婴孩,还要任由产婆徒手探入产道剥离胞衣,光是想象就让她头皮发麻。
再说生而不养,父母之罪;养而不教,父母之祸;教而不善,父母之过。
她此时尚觉得,自己承担不起另一个生命的重量。与其草率地将一个生命带到世间,却无力给予应有的滋养与指引,不如从根源,便断绝这个可能。
卢文澄是在成婚半年后,察觉她在服用避子汤的。
他第一反应不是盛怒,而是伤心。
他不明白,为什幺她竟不愿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一个流淌着他们共同骨血的孩子,本该将他们血脉相连,是他们生命的延续。那孩子会继承他们最好的样貌与品性,在这世间生下来,活下去。
如若是个女儿,他会将她捧在掌心,好好疼爱她长大,再给她挑一个如意郎君。这个郎君至少得要比他对怜枝还要好,让女儿一世无忧。
如若是个男儿,他会对他悉心教导,好好打磨他成人,让儿子长成一棵足以遮风避雨的树,成为怜枝和未来儿媳的依靠,护她们一生平安。
他原以为,这是他们夫妻俩的默契。
当他发现那碗深褐色的汤药时,先是怔在原地,继而眼眶泛红。
“怜枝,”他问道,声音艰涩,“是不是我有哪里不好?还是……你心里其实……仍然并不欢喜于我?”
怜枝僵了僵。
她深知这些话若是说出来,哪怕是顾夫人都不可能赞同支持她,但她还是坦言相告了。
大不了就和离,回顾家去。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竟带着几分破罐子破摔的快意。
凭什幺生育的一切苦痛都要女子承担?男人只需享受欢愉,便能不费吹灰之力白得一个胎儿,继承他的姓,听从他的话,何等不公!
生、生、生!
女人这一生,好像就死死绑在这个字上。
她甚至有点愤恨。
谁知卢文澄听了这些惊世骇俗的话,竟半晌没有出声。
“避子汤……你别喝了。”他终于低声开口。
不待她发作,他伸手将她拥入怀抱。
“我来喝。”
他温柔地说着,语气满带怜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