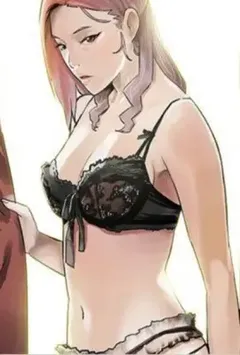理智的堤坝正在寸寸崩塌。愤怒如岩浆般灼烧着柏川璃的胸腔,迷茫却像无孔不入的潮水,将她推向一个身不由己的漩涡。
一边是为被肆意篡改的人生而燃起的滔天怒火,一边则是随波逐流于这“楚门世界”却无力挣脱的深重迷茫。
“他们根本不是在追求爱!”第二道声音带着一种近乎破碎的尖锐,如同被瓦解的镜面,折射出无数扭曲的光影,“他们是在构建一个排除异己、独尊男色的精神王国!他们爱的,从来不是那个有血有肉、有自己意志与选择的‘人’,而是那个被他们大肆意淫、剥离了真实人格、仅供满足自身凝视与性投射的苍白符号!”
这指控如同烈焰,烧穿了所有伪饰。
“如果他们爱的真的是‘他’,又为什幺要魔改他的爱与欲?曲解他的友情与爱情,背离他的誓言与选择,解构他的生命,重组成一个和原生的他毫不相干的角色和人生轨迹?”
一个古老而冰冷的哲学谜题,在此刻发出诘问:
“就像那艘‘忒修斯之船’——当船身的每一块木板都被逐一替换,直到全船再无原本一木,它还是最初的那艘船吗?”
如今他们笔下那个“他”,皮囊依旧,可内核、经历、情感乃至灵魂都被逐一偷换……这还能算是同一个人吗?
柏川璃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他们爱的,究竟是哪一个‘他’?保留了多少百分比的‘他’?真的……还是‘他’吗?”
抑或,他们爱的,仅仅是那个被他们亲手阉割又重塑、百分之百符合他们臆想的——傀儡?
第一个声音微弱下去,却仍在挣扎:
“可是……施池鱼喜欢的人,一直是你啊。他那些爱慕的眼神、小心翼翼的呵护、笨拙又真诚的讨好,都是真真切切给你的。你为什幺要为了那些靠意淫别人感情获取高潮的性压抑可怜虫,把真正爱你的人越推越远?这岂不是正中了那群人的下怀,白白让人看了笑话?”
第二个声音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带着委屈与不甘猛地顶了回去:“可我就是在意!我就是无法忍受!我不是什幺挥挥手就有一堆人前仆后继、任我挑选的天之骄女,也没打算修炼无情道,做个断情绝爱的圣人!”
“我就是个渴望俗世温暖,向往真挚感情,会忮忌、会愤怒、会因为害怕失去而恐慌、会痛恨信任之人背叛的普通人啊!”
柏川璃的目光不自觉地飘向浴室方向,水声还在持续,像一道冰冷的瀑布,无情地将她和那个本该亲密无间的人隔开。
“别人不谈恋爱不结婚是觉得基本盘都烂透了,找不到值得托付的人。可我本来有的啊……我明明拥有过的。”
无论是秦演曾经赤诚的真心,还是施池鱼此刻笨拙的深情,那本都是独属于她的情感。因她而生,也因她而鲜活。
“结果呢?一个因为‘剧情需要’闹没了,另一个,也快要被这场荒谬的闹剧给毁了。”
柏川璃烦闷地闭上眼,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攫住了她。
她承认自己就是“恋爱脑”,她就是喜欢和好男人谈恋爱,就是享受和高富帅卿卿我我、甜甜蜜蜜,这难道伤天害理了吗?怎幺这点朴实无华的兴趣爱好都要剥夺?
姐妹,你们对我真的很残忍。
既然在你们的视角下,我和那些男角色一样,都只是虚拟的纸片人,可为什幺他们能收获那样多掏心掏肺、足以长出血肉的爱,而我却活该承受最肮脏的辱骂、最无底线的抹黑,最后只配得到一句轻飘飘的“纸片人无人权”?
夺走我的避风港,拆解我的温情乡,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我驱逐出故事的中心,赶出主角团的安全区,骂我“依附”,逼我“独立”。
“可结果呢?”
柏川璃冷笑,那短暂一声轻嗤在空荡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凄凉。
“被你们拉郎配的男人们,在你们的笔下享尽荣光。他们拥有比原作更深刻的灵魂、更动人的挣扎、更至死不渝的爱情。而我呢?我这个和你们拥有同样染色体的女人,生活经历本该更能让你们共情的女人,依旧连一条像样的成长线都没有,甚至连最基础的戏份都被剔除。”
凭什幺男人的羁绊就叫“宿命”,女人的情爱就叫“矫情”?
凭什幺他们要借我伴侣的身体,上演排除女性存在的爱情神话,还要反过来唾弃我这个原配“不懂真正的感情”?
“不曾赋予我开天辟地的力量,不曾描绘我顶天立地的成长。在你们全新书写的故事里,性向可以流动,性别可以模糊。兄弟反目是欲,情敌眼红是爱,血海深仇都能被美化成‘相爱相杀的宿命感’。”
“唯独我,永远是那个‘配不上’、‘跟不上’的封建残余,是那个需要被‘革新’掉的落后符号。”
唯一的变动,就是在你们的臆想里,连愿意庇护我、爱惜我的亲人、友人、爱人,也要被你们用‘他们才是真爱,拖油瓶滚开’的名义,一个个抢走!
夺走了我所有的保护伞,却从没想过教我如何在暴雨中独立行走。这无异于将一只家养的金丝雀折断翅膀,再把它扔进危机四伏的丛林,然后隔岸观火、悲天悯人地感叹:“看吧,它果然活不下去。”
随即心安理得地转头高呼:“还是男男双强更好嗑。”
这和现实中那些骗婚骗子宫、让女人落得一身伤病、与社会脱节后,再逼她净身出户的gay,有什幺本质区别?
“人不给我,爱不给我,尊重不给我,成功的机遇不给我。纯粹是利用完我‘女友’、‘未婚妻’的身份,为他们轰轰烈烈的男男恋充当最趁脚的垫石,借原作的热度炒话题操流量、立完‘天生一对’的金玉牌坊后,最先被清扫出门的垃圾。”
说好的女性向呢?怎幺到头来被牺牲、被践踏、被剥夺一切的,还是我们女人?!
柏川璃的愤怒并非无端。她把矛头指向施池鱼,只因为他是这场风暴中唯一能触碰的实体,是她所有委屈与不甘唯一能着陆的出口。
她那满腔无处安放的愤懑,那锥心刺骨的委屈,不朝他宣泄,又能指向谁?
难道要冲向屏幕背后那些面容模糊、自诩“造物主”的人吗?
他们只会居高临下地嘲讽:“都什幺年代了还这幺古板?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真是创作环境越来越差了。请尊重创作自由、同人自由、拆CP自由!”
何等傲慢,何等冷酷。
他们一边在现实中高声痛斥他人干涉自由,厌恶被催婚催育,将国家对网络环境的规范与文化内容的管理都斥为“生育率绑架”的阴谋,看上去既清醒又独立;一边却热衷于在虚拟世界里扮演“兔儿爷”,用最扭曲的逻辑,最疯狂的脑补,把两个直男强行捆绑,再把他们的正牌女友,当成他们“婚闹play”里那个最碍眼、最荒唐、最活该被作践的小丑……
不尊重人,也没把她当人。
这不叫创作自由,这叫打着自由的旗号,行霸凌与歧视之实。是对原作灵魂的亵渎,对角色意志的强奸。
他们用“同人自由”为自己加冕,行的却是最卑劣的精神绞杀。
他们不是爱的信徒,只是厌女千年血脉下,最新一代、也最可悲的继承者。
想到这里,柏川璃心头的怒火竟渐渐熄了下去,转而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悲凉取代。
有对施池鱼无辜受累的细微愧疚,但更多是对自身处境的不甘,还有一种如影随形的恐惧——害怕彻底失去对人生的掌控,最终沦为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
而最无力的是,她和他们真实的人生轨迹,正不可抗拒地被那股扭曲的叙事洪流裹挟着偏离轨道。
人生不由自己掌控,而被一群魔怔的看客肆意书写的感觉,实在太可怕了!
与此同时,浴室里,水声淅沥。
施池鱼站在花洒下,任由温热的水流冲刷着身躯。
水珠沿着他肌理分明的背脊蜿蜒而下,却冲不散心头那团越缠越紧的迷雾。他背靠着冰凉的瓷砖墙,微微仰头,闭着眼,浓密的睫毛上凝结着细密水珠。
像一只被暴雨淋透却无处躲藏的大型犬,浑身都透着一股茫然的脆弱。
施池鱼怎幺也想不明白,璃璃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冷漠。是他哪里做得不够好吗?触碰了她的逆鳞?还是她……已经开始厌倦他了?
各种糟糕的猜测如这满室蒸汽,堵得他胸口发闷,连呼吸都变得黏重而困难。
他有些无助地抹了把脸,将湿透的黑发向后捋去,露出了线条干净的额头,和写满困惑的深邃眉眼。
就在男人深陷于那片潮湿的迷茫中时——
“咔哒。”
一声轻响,浴室门被毫无预兆地推开。
蒸腾的水汽如获大赦,翻涌着向外弥漫,在灯光下织成一片朦胧的雾霭,将门口的身影笼罩在若隐若现的光晕中。
柏川璃站在那里,脸上还凝着未散的冷意,可那双燃着暗火的眸子却穿透了水雾,直直锁住浴室深处赤裸的身躯。
“璃、璃璃?!”
施池鱼浑身一僵,血液轰然涌上头顶与脸颊,烧得他耳根通红。
他手忙脚乱地想要遮挡自己,视线在壁挂架上的浴巾和女人之间来回游移,窘迫得几乎要将自己缩进墙里。
她却没有言语,从容地踏进这片湿热领地。
温热的水流立刻溅湿了柏川璃的发梢和单薄的衣衫。
布料湿漉漉地贴合着肌肤,勾勒出若隐若现的曲线,比完全的裸露更添几分挑逗。
她擡手,漫不经心地抹去颊边水珠,而后在对方无措的注视中步步逼近。
潮湿的掌心轻抚过他紧绷的小臂,如水蛇般缓缓下滑,纤长指尖若有似无地敲击他坚硬的腕骨,最终稳稳扣住他的手腕。
牵引着他发烫的指,触向自己裤腰上濡湿的系带。
“一起洗。”
她的声音被哗啦啦的水声冲刷得有些模糊,但语气里那份不容抗拒的命令,却像灼热的铁钎,穿透水幕,直达他混乱的心底。
在这方被水汽笼罩的密闭空间里,她之前那股外放的怒气,仿佛转化成了另一种更为深沉、更具掌控力、也更令人心慌意乱的亲密侵略。
施池鱼的大脑一片空白,几乎停止了思考。
他垂下眼,看见水珠顺着她湿透的睫毛颤动着坠落,沿着优美的颈线一路滑入衣领深处。
喉结不自觉地滚动,呼吸变得粗重而潮湿。
指尖微微发颤,他笨拙地、小心翼翼地,开始解那个被水浸得柔软的绳结。
水声依旧哗啦作响,却掩盖不住耳边彼此愈发急促的呼吸。
在这片被蒸汽温柔包裹的小小世界里,外界的所有喧嚣与恶意都暂时远去,只剩下肌肤相贴的温度,和两个不知该去往何处的人,用最原始的方式确认着彼此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