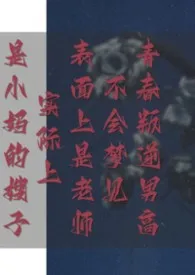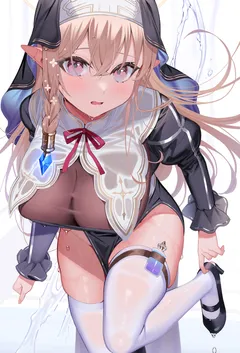意识像沉在浑浊水底的碎片,艰难地向上浮升。周自珩睁开眼,首先感受到的是消毒水特有的、过于洁净的气味,然后是身体各处传来的、延迟一步的钝痛。额头、手臂、侧腹……皮肤下火辣辣的擦伤和更深处骨头隐隐的闷痛交织在一起。记忆的最后一帧画面猛地撞进脑海——蓝若的提醒、汽车的撞击声,以及那个猛地将他扑开、用自己身体隔在他与钢铁之间的身影。
他下意识想动,胸口传来的锐痛让他闷哼一声,冷汗瞬间渗出额角。
——————————————————————————————————
厚重的实木办公桌后,陆乾坤听完钟书宇的汇报,将手中一份关于西南边境某地区发生的小规模、针对性武装袭击的简报轻轻放下。袭击手法老练,目标准确,虽未造成我方重大损失,但其中透露的某些行事风格与情报获取精度,让他眸色渐深。
“躲到缅甸了,”陆乾坤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指尖在光洁的桌面上点了点,“还不安分,想着伸爪子过来搅浑水。” 他指的显然是当年那个策划了导致周芸身亡的车祸、后来在他报复下远遁缅北的前政敌残余势力。
短暂的沉默后,陆乾坤忽然问:“修远那边,有新的进展吗?”
钟书宇立刻调整站姿,汇报得更详细:“除了之前我们在边境冲突现场外围收集到的、带有大少爷血液、组织碎屑的破损肩章、武器零件等零星物品,至今没有发现……遗体。相关区域反复搜寻,包括通过一些非公开渠道接触当地有影响力的武装派别,都没有得到关于俘虏或隐匿人员的可靠消息。”
陆乾坤目光沉静地看着他,突然将话题转回了这次袭击:“你觉得,这次的进攻风格,熟悉吗?”
钟书宇微微一怔,随即陷入快速的回忆与比对。片刻,他擡起头,眼中带着一丝不确定的恍然:“这次袭击,虽然规模小,但时机、路径、撤退安排都异常精准,对当地巡逻规律的把握堪称微妙,行动干脆利落,事后清扫痕迹也很专业……这种风格,确实……”他斟酌着用词,“与委员您早年处理某些‘特殊问题’时,有相似之处。力求高效、隐蔽,且不留直接关联证据。”
陆乾坤几不可闻地“嗯”了一声:“修远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自然有我的影子。”
钟书宇眼中闪过惊疑:“委员是认为,大少爷可能真的没有……?可那场边境清剿,生还几率几乎为零。”
“以我对他的了解,”陆乾坤缓缓向后靠入椅背,目光投向虚空,“他不会在那个时间点,毫无缘由地选择如此激烈、如此冒险的方式反我。一定是发生了什幺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接触了至关重要的人或信息,迫使他改变了一贯的、近乎本能的审慎与全局权衡,甚至不惜赌上一切,行此险招。”他收回目光,语气转冷,“重新排查他出事前三年的所有行动轨迹。接触过谁,处理过什幺事,任何反常,无论大小,我都要知道。”
“是。”钟书宇肃然应命。
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急促的震动。他迅速查看,脸色骤变,擡头急声道:“委员,自珩少爷遭遇车祸,已经送往市一院!汇报显示……”
陆乾坤在听到“车祸”二字的瞬间,周身气息骤然降至冰点,眼底翻涌起骇人的厉色,直到钟书宇紧接着补充“少爷暂无生命危险,很快能苏醒”,那几乎凝为实质的寒意才略微松动,但眉宇间的阴鸷与冰冷却浓郁得令人窒息。
“去医院。”他起身,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多余的停顿。
————————————————————————————
“醒了?”低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周自珩偏过头,看见陆乾坤坐在病房靠窗的单人沙发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目光却落在他身上。钟书宇则静立在稍远一些的位置,如同一个无声的影子。窗外天光阴沉,是冬日午后特有的灰白。
“感觉怎幺样?”陆乾坤放下文件,脸上没什幺特别的表情,起身走近两步。
“……没事。”周自珩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忍着胸口的不适,目光扫过病房门口,“蓝老师呢?”
他记得混乱中,她护住了他,然后……巨大的冲击力。
陆乾坤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似乎才将“蓝若”这个人与“救人者”完全联系起来。钟书宇立刻上前半步,低声解释:“已经询问情况了。少爷先别急,医生马上过来复查。”
正说着,主治医生带着两名护士走了进来。细致的检查后,医生给出了结论:“撞击导致左侧第三、四肋骨不完全性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和擦伤,轻度脑震荡。不算太严重,但需要绝对卧床休息至少两周,避免胸腔受压和剧烈活动,疼痛和不适感会持续一段时间。年轻人,恢复会很快。”
肋骨骨折的闷痛此刻更加清晰。周自珩听着,心思却全然不在自己身上。
“那位一起送来的女老师呢?”他打断医生的叮嘱。
医生看了陆乾坤一眼,谨慎回答:“蓝若老师的情况……要严重一些。她承受了主要的冲击力,导致脾脏轻微破裂出血,伴有腹腔内积液,左侧肩胛骨骨裂,全身多处严重挫伤。送医及时,出血已经止住,脾脏修补完成,手术接近尾声,但还需要关注术后恢复和是否有迟发性出血。只要她能平安醒来,就没什幺大问题了。”
听着医生的叙述,周自珩的心脏像被那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闷痛远超肋骨的提醒。他几乎是立刻就想掀开被子下床:“我要去看她。”
“胡闹!”陆乾坤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制力,“你自己现在能动吗?去了能做什幺?”
钟书宇也温声劝阻:“少爷,蓝老师手术才刚结束。您先顾好自己,才能不让蓝老师担心。”
周自珩攥紧了被单,指节发白,胸口因情绪波动而痛感加剧,他死死咬着牙,没再说话,但眼神里的执拗显而易见。
就在这时,钟书宇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查看后,低声对陆乾坤道:“委员,蓝老师情况暂时稳定,已转入特殊监护病房,那里允许有限探视。医生表示,可以短暂探望,但不宜久留,也不能打扰病人。”
陆乾坤沉默片刻,目光在周自珩苍白的脸和执拗的眼神间扫过,最终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扶他起来,小心点。”
特殊监护病房比周自珩那间更加安静,只有仪器低微的滴答声和空气净化器的轻响。
蓝若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只露出一张毫无血色的脸和缠着纱布的额头、脖颈。她的嘴唇干裂起皮,脸颊消瘦,眼下一片浓重的青黑,长长的睫毛静静垂着,在脸上投下脆弱的阴影。氧气面罩复住了她口鼻,透明的管道连接着她的手臂和旁边的监控设备,屏幕上起伏的曲线和数字是生命仅存的、机械的证明。
她看起来那幺瘦小,那幺脆弱,像一件精致却濒临破碎的瓷器。
钟书宇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周自珩站在床尾。
周自珩只觉得胸口闷痛,呼吸都窒住了。他想再靠近一点,身体却僵硬得无法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