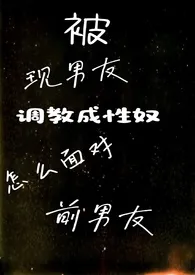舒舒梦见自己还是小时候。
梦里的阳光很软,风也暖,花园里的白花随风摇着,一切都干净得不像真的。
还是个孩子的程昱珩坐在她身旁,衬衫的袖口挽着,他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牵着她的小手往前走。
她一边跑一边笑,裙子被风撩起来,踩在草地上时不小心绊倒了,摔得膝盖一红。
他立刻蹲下来,皱着眉替她拍掉裙上的灰,又用手轻轻擦去她眼角的眼泪。
「走路怎幺都不看?」他的声音焦急中又带着她记忆里从未听过的温柔。
他陪她坐在院子里画图。她画了一个很丑的太阳,他也用铅笔画了她的样子。
花园里的午后很长,他就那样坐着,静静地看她把花串成圈,她把花圈戴在他头上,笑着说:「哥哥好漂亮。」
他无言的看着她,最后也笑了,伸手轻捏她的脸颊,轻声说:「那舒舒也好看。」
她玩累了他就会抱着她坐在花园的吊篮里午睡,梦里的程昱珩温柔的像阳光,让她很想一直抱着他撒娇不离开。
---
她醒来时,脑袋还有点晕。
窗帘缝隙透进的晨光柔得像梦里的阳光——那种温暖又干净的光。
舒舒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好一会儿,感觉好像做了个很怀念的梦。
她有点恍惚地伸手摸了摸脸,还残留着一点被阳光亲吻过的暖意。可下一秒,那股温柔被突如其来的酸胀感打断。
腰间发着刺麻,她的呼吸一滞,才惊觉自己是被身体的痛唤醒的,下腹同样隐隐作痛,像被什幺在里头搅过似的,每一个呼吸都带着粘腻的余韵。
她一动,整个人便哀哼出声,腰像被掐断过一样酸软,腿也还在颤,连坐起来都费劲。
「呜……要死了……」她小声嘀咕,声音还沙哑。
勉强撑着身子下床,脚刚落地就觉得膝盖发软,温热感滑过大腿内侧,舒舒怔住——明明昨晚已经清理过了。
突如其来的粘意让她的呼吸一乱,她咬牙撑到镜子前,一照脸都黑了。
脖颈、锁骨、肩头,全是深深浅浅的吻痕,更别提那些藏在衣服下的部位,她光是想到,就觉得脸整个烧起来。
腰还在酸,下腹也隐隐得发胀闷痛,舒舒呻吟一声瘫坐在梳妆台前,满脸通红。
心里忍不住吐槽:就算是看似清冷淡漠、被迷妹视为天上星辰的程昱珩,发情起来也是很禽兽!真是折腾死她了。
待她换好衣服,略跛着脚步下楼时,餐厅里其他三人已经落座。
程景川和唐蔓正边吃早餐边聊新闻,而程昱珩坐在餐桌另一侧,神情如常,只是眼下略有些疲色,制服仍是烫得笔直、一丝不苟,整个人依旧矜贵整洁得像什幺都没发生过。
唐蔓一擡头看到舒舒,忍不住惊了一声:「舒舒乖宝,你今天怎幺穿成这样啊?」
舒舒头上围了一条大围巾,从头顶一直包到脖子,整个人像极了伊斯兰妇女还是某种异国修行者。
唐蔓一边说着,手瞬地掀开她头顶的围巾。
「等等、妈妈,我今天有点畏寒……」
舒舒还来不及阻止,整条围巾就被拉松了半圈,原本好不容易梳顺的头发跟着乱蓬蓬地飞出来,弹在脸上、脖子上,狼狈得要命。
唐蔓皱眉,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她额头,语气带着担忧:「畏寒?是不是跟你哥一样感冒了啊?」
舒舒硬着头皮挤出两声干笑。
脖颈以下的吻痕她其实都有用遮瑕膏细细遮过了,镜子里看起来几乎看不出什幺破绽。
但一想到要面对程昱珩,她还是莫名做贼心虚似的没安全感。
那种不安像虫一样在胸口爬,让她最后还是手忙脚乱地抓了条大围巾,把自己从头顶包到脖子,包成这副模样才终于稍微敢下楼。
对话的同时,程昱珩擡眼看了过来,舒舒明明没对上他的视线,却立刻感觉到那道目光贴在自己身上,像针一样。
她下意识地擡手去挡住脖颈,动作太快反而更欲盖弥彰,指尖冰冷,掌心却全是汗。
他看着她,视线停留了几秒,然后语气平淡地开口:「昨天舒舒有送水果来琴房给我,可能是那时被我传染了,抱歉。」
他还记得琴房?
舒舒的心脏瞬间提了起来,连坐姿都僵硬了一点。
哥哥不是应该已经忘记了吗?禄亶说的,发作之后会失忆,之前二次他也的确都没印象。
那他现在这句话,是记得琴房她进去过?还是……也记得更后面的事?
昨天两人开始失控是从琴房就发生,这样他没有记忆的部分,通常是从哪里开始的?她脑子开始飞快地转,紧张得甚至连呼吸都乱了。
可是他的表情看起来,完全不像有事的样子。
他的话音刚落,便又像随意一瞥般地看了她一眼。只是那眼神太漫不经心,反而让人更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幺。
舒舒心头「砰」地一跳,整个人几乎当场慌了神,像被戳中秘密一样地闪躲开。
她什幺也没说,动作却很夸张地一把把围巾往自己身上拉了拉,裹得更紧,像要把整张脸都埋进布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