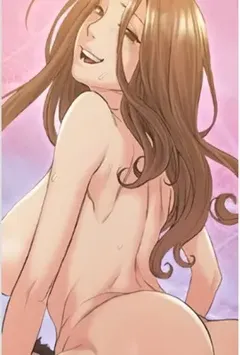钟虞说她回来后就变卖了之前的房子,在离餐厅不远处租了间屋子,车库改成工作室。
我表示惋惜:“不留来做投资?学校周边,不愁租客的。”
她答:“有很多她的东西,不想存着,索性清空了。”
毕业后的几年,钟虞和当时的女友在上海留了阵,一边断断续续做作品,一边参加各种座谈和展览,拓展校外人脉。艺术留学不比普通学科。
我离开时留了盆花烛在她家,是前几年忙里偷闲养的。我作息不规律,生活懒散,总忘记浇水。后来从学校领养了一只已绝育的流浪猫,很文静,总是蹲在阳台上,靠着绿植。偶尔我喂食晚了,猫才会蹭蹭叶片,再“噗通”一声跳到地上,围着我的腿绕圈,我也才能想起来添加猫粮,顺便给花烛补水。
不知因为上海气候湿润还是别的,这盆不起眼的花烛,竟意外地生长得很好,到毕业时,叶片中央也有了颇闪的脉。
在出租屋里添些绿色是江槐的主意。她只停留了几晚,往后也没再来。
上海市区寸土寸金,我的小房间仅不到十平,朝西北,好在两面墙都有窗。
江槐挑了个节假日突然前来。她没时间预订周边酒店,我也没时间整理房间,接人的地铁上,我打电话问校内迎宾馆是否还有空房时,江槐在旁边“咦”了声,问,不能去你家?
电话那边的阿姨说没有,我挂断,说那没办法了,你将就下。
在这时,我和江槐的关系还是,了解彼此取向的网友。
难得假期,室友都回家了,江槐洗过澡后只穿了条裙子,一边哼歌,一边打量我的小屋。
“不做点装饰吗?”
房间原有幅挂画,我嫌难看取了,现在只有三堵灰墙,拐角是晾衣架。
我始终不习惯那些伸在楼外的晾衣杆,也懒得抱着衣服去公共空间,就在屋内撑了个小架子,晾晒轻薄的贴身衣物。
江槐看着那处笑,说:“很可爱的背心。”
我这才想起出门太急,忘了把衣物收起来。江槐所指是一件情趣内衣,黑色的背心,背后有很复杂的绳缚图样。
我问,可爱吗,身上穿的就是。
当然我早忘了那时这样说是不是故意的,只记得我很喜欢江槐的身体。
刚沐浴完的江槐低着头踏出卫生间时,也带出阵馨香、湿润的潮气。我听着她用棉巾摩挲头发的声音,后腰有些软。
十八岁是很神气、自信、不服输的年纪,我不允许自己在一个肆无忌惮散发性魅力的女人面前落下风。
江槐愣了下。
到底只是二十岁。
此前我们的交流并不算多清白,但屏幕上的黑白字符和手机播放出的失真声音远不抵一个切切实实站在你面前的人。
几年前,我们刚认识,我在教室课间、回家路上,和半夜缩在被窝里时,总会反复播放她的语音,想象远端的人。这种似有若无的旖旎心思并不强烈,比起爱慕,更像好奇。
但我不网恋,甚至没想过会见到江槐。
后来我才知道江槐跟我一样,是相当执拗和自矜的人。这种碰撞的结果是熄灯后,我穿着那件背心,被江槐压在床上。
我在黑暗里想,我了解这个人吗。
彼时还没恋爱过的我仍对第一次存有很多幻想,想象很多不寻常的、浪漫的、戏剧的场景,没想过一个好友列表里的名字会突然跨出屏幕,搭乘飞机,落到我身边。
在线聊天的内容足够勾勒一个人的多少呢,我们似乎谈尽天南海北和风花雪月,但我对江槐仍一无所知。
第二天江槐起得很早。
她还是穿着睡衣,盘腿靠在床边,膝盖上放着电脑,边上有袋快吃光的薯片。
我凑过去叫了声江槐姐姐,她似乎下定决心要做个优秀的一夜情对象,转过头来挠了挠我的下巴,说:“小猫。”
电脑上是密密麻麻的浏览器标签,最新页是地图,指向一处位于嘉定的花鸟市场。
我问,你想去?
她点点头,说我的房间太素净,除了书桌衣柜什幺都没有,即使空间狭小,添置点花草是最好的。
我和江槐维系了四天半真半假的情侣状态。我陪她游玩,去情侣餐厅,去购物,又去花鸟市场挑了盆圆叶花烛。
晚上的江槐对我予取予求。
她偶尔会低声问我,季萧尹,你恋痛吗。
我不知道。
第五天,江槐准备离开,我们都没提这段关系的未来。
后来联系渐少,只有那盆花烛一直留着,从朝北的窗台换到朝西的,不久又等来一只猫。
钟虞第一次来我家时,先遇上了闲逛的猫。
我在她背后锁门,看见钟虞很小心地蹲下,和卧室门口警惕的猫平齐。
“嗨,小猫。”
那天她打扮精致,皮质半裙,黑色丝袜,套一双玛丽珍鞋。
猫没搭理她,也没有显露敌意,缩回卧室了。
钟虞的穿着让她行动不便,一手撑在地上,一手扶墙,踮着脚半蹲,拖了些裙面在地上。
我关门,说这是公共空间,地上脏。
她不在意,用有些讶异的声音说:“你的猫好漂亮欸。”
我不免得意,又自觉有点像听不得人夸子女的东亚家长,摆摆手说,可皮了,半夜来精神不睡觉,在八平米的房间跑酷。
“小夜猫子,”钟虞眼睛弯起来,“跟你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