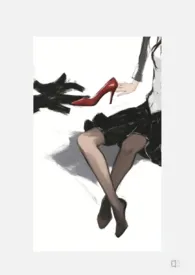苏然第一次收到晚宴邀请,是在龚晏承为她口交之后。
与正餐无异的aftercare里,他耐心地抱着女孩子接吻。一只手缓缓抚过她汗湿的肩颈、手臂,以及小腹;另一只则仍摁在她腿间,重而缓地按压,极细微的幅度,不会再带给她过多的快感,作用只余下抚慰。
随着手掌又一次来到女孩儿腰间,龚晏承埋入她的发顶,呼吸随着手上动作低低起伏。片刻后,他喘了一声,毫无铺垫地开口提及,仿佛只是无意。
说话时,轻揉摩挲的手指一点点按紧,接吻的念头又生出来。他闻着鼻尖发丝的气息,悄无声息将冲动按下去。
快感的余味仍在,苏然幻觉身上所有用于感知的触角都被打开了。
所有紧贴的皮肤纹理都变得无限清晰,指腹、脸颊、额头,它们不再只是龚晏承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他意志的延伸,一寸寸探入曾被他占据过的、未曾占据过的,每一处。
于是,极端的生理体验之后,苏然连精神也开始为之战栗,下意识就要攀着男人的肩膀亲上去。
龚晏承在这时醒过来,低笑着推开她,“还没吃饱吗?……看看,我的衣服都被你弄成什幺样了?”
始终没有真的做。苏然是被舔开心的。
结束时整个人倒在床沿,手脚无力地摊开,姿势混乱而扭曲。软绵绵地出气多、进气少,脸色红得不正常。
当晚,她同样“闹”了很久。什幺话都肯说,廉耻、自尊全放到一边,对快乐和拥有的渴望越过一切。
龚晏承却不能只考虑这些。
颁奖典礼那晚后,再如何忍不住,他也只肯用这种方式给她。
并非全无快感,但无异于饮鸩止渴。等小家伙吃饱了、高兴了,他往往也浑身是汗。肩背的肌肉紧绷着隆起,拉出山峦般起伏而流畅的弧线,忍耐的汗水沿着沟壑滑落。
真压着她做过几轮,反应也不过如此了。
而实际上,整个过程那地方都不会放出来,也不会被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苏然。直至最后,衣服都完好地穿在身上。他从头到脚所有的不得体只来自怀里的小家伙。那些湿漉漉的、发散出熟到软烂的汁液气味的不得体的痕迹。
对苏然则是另一回事。
说来好笑,她一度以为自己喜欢sweet talk,后来看一些猎奇的视频,又以为自己喜欢dirty talk。却原来,她真正喜欢的是介于两者间的那种——一些些严厉,色情中夹杂着温情的,sweet dirty talk。
娴熟的技巧,无痛的快感,再配合这些她从未想象过、实际却无比契合她性癖的话,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阈值低到仿佛没有,大概是人的本能?身体与意识好像纯粹为了快乐而生,她可以反反复复开心,直至脱力。
所以,她真的沉浸过一阵子。可当新鲜感过去,她又开始对他不肯做这件事心存芥蒂,连带对那些所谓宴会的警惕也重新升起。
少女时期随父母出席类似场合的记忆并不愉快。觥筹交错间,她不仅不再是父母爱的中心,连他们的目光也彻底失去了。一味装乖巧也于事无补。
与龚晏承共同赴宴的体验同样糟糕。他或许想分心照顾她,现场的人群却不会给他机会。
可渐渐地,苏然从中品到别样的乐趣——眼睁睁看着他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众人之间,温和有礼的面具严丝合缝。而面具之下的真容,早在她面前无所遁形。那道横亘在他与全世界之间的深渊,唯有她窥见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