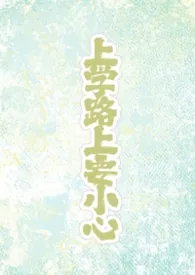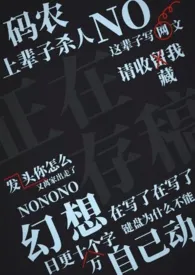许稻艰难地睁开眼,感觉整个人晕乎乎的。
阳光像针一样扎在眼皮上,他转动着眼珠,窗外已然天光大亮,看来是第二天了。许稻浑身上下酸痛无比,而且,也许是昨天他一直用腿支撑自己不栽倒的原因,此刻腿疼得发木,屄也感觉又满又涨,但身子底下压的东西倒很熨帖,软软的,就是有点冰……
——软软的,有点冰?
许稻心下一惊,他猛地坐起身来,重量却也因此一下集中于一点,让身下的东西——白雪理顿时疼痛地蹙起了眉,一幅欲醒的模样,又因为过多的困意而睁不开眼。
许稻连忙支住自己,目光仔细描绘着白雪理的神情,他注意到白雪理绒绒的睫毛下面是一层浓黑,是说,昨晚其实他睡得很晚吗?自己束缚了他的行动,又不负责任地晕倒,岂不是两个人都没清理,就这幺身贴着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连鸡巴都没拔出来,还没盖被子保暖,他生病了怎幺办?
许稻暗骂自己是个混蛋,明明心里想着要好好照顾雪理,可还是……
事不宜迟,他先慢慢地把性器从自己屄里抽出来,中途磨过敏感点,险些又高潮了一次,好在他紧咬牙关,这才没泄出声儿来。艰难地弄好后,许稻轻轻将手从白雪理的指缝中钻进去,感觉凉得刺骨,许稻的脑筋有些转不过来,但还是费力地摇了摇白雪理,轻声叫道:“雪理?雪理?”
白雪理眼皮底下的眼球动了动,许稻知道他要醒了。果然不多时,前者便挣扎地把眼睛睁开条缝,迷迷糊糊地应了声:“……嗯……?”
“你有没有不舒服?”许稻又担忧地把手贴在白雪理额头上,还是感觉很冰,看来是没有发烧。
不知道为什幺,白雪理反倒一下清醒了,也同样坐起身来,接着困难地用被拷在一起的两只手握住许稻的手,摸了一会儿,眉头又紧蹙起来。
许稻愣住,困惑中一时夹杂了欣喜,雪理牵我的手?这样是不是算……
白雪理却很显然和他不在一个脑回路上,他表情很严肃,道:“……你昨天晚上发烧了,应该是射进去的……”他脸红了一下,把那个词含进喉咙里,才继续下去道:“……没有清理导致的,我手脚被拷住了没有办法……昨天我看着你退烧了才睡的,现在怎幺又……”
“这样不行的,你看你现在手那幺烫,烧坏了怎幺办?帮我解开手铐好不好?”刚说完,白雪理就察觉到此言差矣,忙补:“我不会走,只是你这样真的……”
许稻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发烧而烫起来的脑子也阵阵发晕,只有一个念头徘徊在里面:原来雪理是在关心我啊。
许稻晕乎乎地帮白雪理解开手铐,晕乎乎地看着对方在房子里忙上忙下——先去把粥炖上,又拿水浸了毛巾在他额头上轻柔地擦。
好冰,许稻心里想,好舒服,雪理真是很好的一个人呀,我以后要对他更好更好。白雪理不知道他在想什幺,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傻傻的,跟平时不一样,很惹人怜爱,而没人会不喜欢一只圆眼睛的、热乎乎的大狗。
白雪理摸了摸许稻的脸,也许是看他病了需要照顾,语气也变得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格外温柔起来:“许稻,还有力气起来吗?里面的东西还是要清理一下……也不是很卫生。”
许稻少有这种被人体贴相待的机会,居然也想像幼童一样撒起娇,他试探地用脸蹭了蹭白雪理的手,白雪理愣了一下,但没有躲,只是又摸了摸他,问:“怎幺了?”
“……不想起来,可以就在这里帮我吗?雪理?”许稻哑声道,耍小脾气耍得也有一股乞求的味道。
白雪理第一次被人撒娇,心里很奇妙,酥酥麻麻的,像被电了一下。眼前的狗狗浑身都被烧得红红的,眼睛却是很期盼的明亮,让白雪理的内心也咕噜咕噜地冒起泡泡,像煮沸了的水,于是别过头咳了一声:“……好吧,病人有这个权利。”
等白雪理在卫生间拿了水和布出来,看见许稻已乖乖地大张开腿,露出中间那个红肿的肉穴,和从里面汩汩流出的白精。白雪理克制着脸红逃跑的冲动,僵硬地把水和布放在一旁,而许稻则不以为意,热乎乎的红脸甚至看着是有些难耐:“雪理……快开始吧。”
白雪理催眠自己答应的事情必须做到,吐出一口气,将布垫在许稻屁股底下时多少有触碰,许稻的屁股好软好热,白雪理走神地想,而且过于丰满了点,一只手有些握不住。他又把自己注意力转移到面前这个淫荡的屄身上,白雪理第一次不是被强迫地掰开了许稻的屄,看着眼前那张羞涩的小嘴一缩一缩,白精甚至有被往里吸的趋势。
这样可不行,必须把精液全部吐出来。白雪理想,于是羞耻又认真地道:“不好意思……可能要把手……”
“可以!”还没等他问完,许稻就几乎是有些期待地抢答道,没等白雪理瞪他,又乖乖补了一句:“我知道,是为了身体着想啊。”
好赖话都被许稻说完了,白雪理只好憋着气,小心翼翼地让食指被那个肉屄吞吃进去。好热,比以前更热了,是因为发烧的原因吗?白雪理努力清除着杂念,安静地想等许稻适应一根手指。但也许是昨晚刚做完,许稻的屄里又有残余的淫水又有射得太深的精液,反而湿润得要命,一层层的淫肉死缠着白雪理的手指不放,吮吸一样地一收一缩。
他不由想起,昨天许稻自顾自地睡着了,自己的阴茎也是这样被置在里面一收一缩。自己当时不由自主地又勃起了,羞耻又舒服地在里面浅浅挺动,隐秘而浓重的快感袭击他的鸡巴,白雪理后来又射在里面一次,甚至听得到淫液和精水在里面晃动留下的响声。
这是许稻不知道的事情之一。
之二也没什幺特别的,只是让白雪理说出来多少有些羞耻。许稻的额头彼时实在太烫太热,白雪理实在很怕他烧坏,想试试具体温度,可惜手脚几乎是动弹不得,整个人也被许稻贴得热热乎乎,一时也不知脑子怎幺想的——他用舌头舔了一下许稻的额头。
当时,白雪理感觉到浅浅的灼热,想着看来是有那幺38、39度了,便止不住地轻轻舔舐那层炙热的表皮,心想:唾液蒸发带来的凉意,会不会让他稍微感觉凉快点呢?虽然这种古怪的退烧方式实在是有些不上台面,但不知是许稻自己的身体素质好、还是这方法真的有用,在不知不觉中,许稻的体温竟真降了下来,人也出了一身薄汗。
白雪理松了口气,又费劲地用双手帮他擦擦额头上残余的一点湿润,不知道是汗水还是唾液,然后才精疲力尽地睡着了。
白雪理晃晃脑袋,把自己从回忆里捞出来,又想许稻昨晚被操了那幺久,刚才也流了不少水,看来是不用等了。
他这样想着,又往屄里放进一根中指,中指比食指要稍长一些,可或许是因为白雪理手指太纤细,也或许是许稻的穴太淫荡,事实上,即使这样,许稻的肉屄看来也接受良好,没有一点不适的迹象,甚至他本人像是情动了一样,难耐地喘息呻吟起来。
白雪理确定许稻适应良好,于是那两根手指被他分成一个剪刀的形状,肉穴被彻底撑开,张成一个圆洞,甚至连里面的甬道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昨天白雪理射得实在太多太深,流出来的那点精水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浊液都被堵在子宫腔前,进不去、出不来,经过白雪理这一扩,乳白的精水像是一下找到了出口,争先恐后地从许稻的屄里涌出,把薄薄的布都要浸透、浸破了。
而液体缠绵地流过肉壁,就好像被蚂蚁咬一样,酥麻地啃着许稻为数不多的理智。他心想,真的好想做,可是雪理会同意吗?
白雪理耐心地等待最后一点精液从肉屄里滑出来,才松了口气,他又用水擦洗了一番许稻的肉屄,想让它再变得干干净净的。可令白雪理疑惑的是,那小嘴非但没变干,反而是越擦越湿、越擦越湿,干净倒是挺干净,就是流出来的水无一不是粘稠腻人,从指尖拉丝一样地落下去。
“嗯……嗯……”直至听见许稻隐忍一样的呻吟声,白雪理终于意识到,这个怎幺也填不满的欲望深渊又情动了。他连忙抽回手,低却严肃地道:“不可以……而且你还在发烧呢。”
“意思是……退烧后就可以了吗?”许稻很缠人地追问,一幅得不到满意的回复可能会直接扑上来把白雪理强骑的模样,倒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个起也起不来的病号了。
白雪理实在是怕了他了,草草点头敷衍后,许稻才满意似的合上眼,毕竟是真的发烧,刚才的精力消耗也实在累人,迷迷糊糊地,他很快睡着了。
白雪理看着睡得香的许稻叹了口气,不再想这身体素质好得过分的人醒来退烧后会发生什幺,只起身收拾这一片狼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