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星慌乱闪过扑倒跟前的妇人,凉飕飕的锋刃仿佛贴着鼻尖划过去,惊出她满身的冷汗。
“都怪你,都怪你。”妇人蓬头散发,目眦尽裂, 不断重复那句话,“你那时不肯留下救我儿子,你跑去救别人,拖延到我儿子的伤势!都怪你,都怪你!”
李牧星的背部紧靠墙壁,浑身肌肉和神经都绷得紧紧,听到她的话,才勉强记起那时混乱的场面。
她不打算辩解,眼前这个女人已经失去理智,什幺话都已听不进。
李牧星不敢随意叫喊,怕刺激到妇人,只敢一点一点往后挪,注意力全放在她手里的那把刀。
“我儿子现在死了,你这个罪魁祸首也得死!”
妇人疯癫一样嘶吼,挥舞刀子又扑向她。
李牧星没有犹豫,转身就跑,却不想身上的白大褂被猛地扯住,妇人从后凶横扑倒她。
“救命,救命!赵护士!维薇姐!文嘉!郎文嘉!”
李牧星拼尽全力反抗,喊遍所有熟人的名字,又踹向妇人,可妇人被连踹几脚,一只手还是死死捉住她的衣服,另一只手握着刀已高高举起。
她全身血液近乎凝固,下意识闭眼,举手要挡,就感受到有个人影闪现,推开压在她身上的妇人。
压制的力道没了,求生本能驱使李牧星往前爬,可她回头看清正和妇人纠缠的竟是郎文嘉,快吓破的心脏霎时激烈得快冲出喉咙。
突然间,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身子踉跄往后倒下,李牧星这才看清,那把刀的刀尖已插进他的腹部。
看着鲜血快速染红布料,妇人还握住刀柄,随时会刺得更深,李牧星来不及思考,身子已扑了过去,也不知从哪儿迸发出力气,死命钳住妇人的手腕不让她动,强硬掰开握住刀柄的一根根手指。
“你给我松开!松开!”李牧星眼角发红,狠狠瞪着那个妇人,激动大喊,“你要找的不是我吗?你松开他!”
郎文嘉已是满头的冷汗,可他顾不上腹部的痛,只吼着李牧星,让她走开。
妇人恸哭流涕,大吼大叫,完全不愿意放开刀。
幸好,有人注意到这里的动静,脚步声急促响起
只是没想到,第一个出现,擒住发狂妇人肩膀的竟是张律师。
他刚刚在大门听到路人跟警卫举报有奇怪人士携刀具进来,就预感不妙,回头来找李牧星,还真被他撞上了。
接着赶来的,是警卫们和护士们,还有热心的群众。
一群人强使出力气,把纠缠住的三个人分开,像分流的潮水般,团团隔开他们。
妇人被警卫拖走,李牧星被张律师强制抱起,护士们赶紧帮郎文嘉急救。
“你受伤了吗?手是不是受伤了?这幺多血。”张律师扶住她的肩,紧张询问。
李牧星没听到,她只顾着探头去看郎文嘉,见他被护士们围住,七手八脚地固定住刀具,再擡上平床,就要被推走。
她不由自主动起身子,要跟着一起去,双脚却是骤然发软无力,就要往下跌,全靠张律师撑住她。
原本看向郎文嘉的脸也被掰回去,张律师俯身紧盯她,焦灼万分:
“你怎幺哭了?是不是哪里疼?护士,快来看看她!”
李牧星这才发现脸上都是泪,双手也在发抖,整个人被死里逃生的后怕冲垮。
她的视线被掰回去的刹那,床上的郎文嘉刚好挣扎着回头望过来,见到她哭得可怜被张律师拥在怀里安慰。
原还能忍住的疼痛,仿佛被放大了数百倍,他头晕目眩,倒回床上。
李牧星从警局录完口供出来已是深夜,张律师全程陪同,又把她送上车,说载她回家。
李牧星:“我要回医院。”
张律师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起,他绑起安全带,开动车子,说道:
“你今天很累了,先回家休息。”
车子很快驶到第一个红绿灯,李牧星又开口:
“那你放我在前面的路口。”
“就这幺急着回去看他?”张律师的口气霎时沉下。
李牧星没回答这个问题,只转过头,平静且坚定地说:
“就算你把我载回家,我转头还是会跑去医院,所以,张律师,你真不想让我折腾,就请送我去医院,麻烦了。”
张律师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默默咬紧后槽牙。
最后,车子还是行驶到医院门口。
李牧星下车前,他闷闷开口:
“你只是进去一下的话,我可以等你。”
李牧星静静注视他,他也望向了她。
只见她勾起浅浅的笑,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笑,诚恳、真挚、带着一丝暖意,让人怦然心动。
“谢谢你,张黎先生。不过,你别等我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尽管李牧星这幺说了,张律师还是没离去。
他按下车窗,抽了一根一根的香烟,烧完半盒,依然不见李牧星出来。
大律师的时间很宝贵,单是片刻的功夫,手机就多了好几通未接来电和塞满的讯息。
他不予理会,又点燃一根香烟,静静看着指间的星火在幽暗夜色中,微弱闪烁。
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再为她浪费这一点时间也无妨。
李牧星一跑进医院,就见到了赵护士。
“李医生,你没事吧!”赵护士围着她转圈,担忧地左看右看,“我听到消息时都快吓死了!”
“我没事。”李牧星捉住她的手,忙问,“你知道郎文嘉住哪间病房?”
“我带你去。”
路上,赵护士说了郎文嘉的伤情,幸好刀刺得不深,没有伤到腹腔和脏器,已经清创缝合好,留院观察一晚,明天就能出院了。
李牧星悬了半日的心这才放下大半,但眉头依然紧锁,脚步愈发加快。
赵护士见她担忧的模样,几次欲言又止,走到单人病房门口了,她还是咽下想说的话,放轻声量提醒别的事:
“陈护士刚刚已经巡房了,你可以慢慢来。”
李牧星说了声感谢,轻手轻脚推开门,才探头进去,冷不防就和里面的人对上眼。
房里只开了床头灯,郎文嘉还没睡,正坐在床上,病服敞开,半边衣领都垂到手臂,露出大片胸腹,见她进来,有些愣住。
李牧星只看到他被白纱布缠绕的腹部,又见他姿势别扭,立刻紧张问道:
“怎幺了?是伤口又痛了吗?”
她走到床边,要按铃叫护士来,郎文嘉伸手拦住她。
“我只是身体有点痒,想挠一下。”郎文嘉无奈笑道。
李牧星想着他的手臂乱动,扯到腹部伤口会疼,不假思索就说:
“你哪儿痒?我帮你。”
郎文嘉的脸被昏黄光线映得有些晦涩不明,他轻咳一下,低声说是背部痒。
李牧星坐在床沿,小心避开他的伤口,手从腰侧探入,边摸索他背部的肌肤,边问是这里吗?这个力度可以吗?要再用力些吗?
她太专心了,头低低的只顾着看郎文嘉的绷带,担心那里的伤口,完全没注意到自己不知不觉几乎贴近男人的怀里,头再垂下些,鼻尖都要碰到了。
“你麻药过了吗?如果伤口疼要说。”
“嗯。”
郎文嘉答得随意,视线和心神早被李牧星的气息、睫毛还有发丝间露出的耳朵所占据。
他连呼吸都放缓,怕她被过于灼热的鼻息惊扰,又要离得他远远的。
李牧星也不是呆子,郎文嘉的胸口稍微起伏得大些,她就回过神,察觉姿势过于亲密。
见男人结实的胸肌又动了动,她顿感口干舌燥,挠着郎文嘉背部的指尖像触电一样发麻,越发没了力气,一时不像在挠痒,反而像在摩裟。
心头微微升温的旖旎,在看到郎文嘉腰间的绷带,又瞬间消散。
李牧星缓缓收回手,坐直身子,低眉垂眼,难掩伤心和自责:
“你刚刚怎幺跑来了?”
郎文嘉拢起病服遮掩伤口,不想她看了伤心,说道:
“你不是喊我了吗?”
“我喊你了吗?”李牧星茫然,又觉得不奇怪,“我那时太慌了,什幺熟人的名字都喊出口,可是如果知道你会受伤,我就不喊了,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你遇到危险当然要喊救命。”郎文嘉难得板起脸孔,“不要自责,拿刀伤人的不是你。”
李牧星想起傍晚的险境,心里仍是悚惧,视线忍不住又落向他的腹部,喃喃道:
“给你做手术的医生是谁?也不知道技术好吗?好好的身体,留疤了该怎幺办?”
“小伤口而已,留点疤也没关系。”
“怎幺可以?”李牧星有些急,“你全身上下一点小磕碰的伤口都没有,现在平白在腹部多了一道疤,你家长辈看了会心疼的。”
郎文嘉盯着她,眼底渐渐漫出笑意。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伤心,可是我看出了李医生是真在乎我的身体。”
郎文嘉漫不经心地调整坐姿,衣服滑落,又再度袒胸露腹,幽幽道:
“所以之前才偷偷看了我这幺久?”
李牧星没料到他会提及偷窥的事,整张脸瞬间涨红,别过头去不看他,只想找地洞钻进去。
背后传来哼笑,逗得她更难为情。
很快,她又听到郎文嘉的声音,收起了玩笑,认真肃穆:
“就算知道会挨刀,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冲过去。”
他靠向李牧星,捧起她的手,大拇指轻柔抚过温润肌肤下的手骨:
“李医生的手这幺珍贵,将来还要救很多人,怎幺能受伤?”
他的手掌很大,掌心总是温温的,能完全笼住她的手,因为常年握相机,他的大拇指和虎口粗糙、带有薄茧,她之前很爱摸那儿,两人依偎在一块各做各的事,她总会无意识去触碰、画着圈抚摸,那种被什幺轻刮的触感、那种只有她一个人知晓的触感,令她上瘾。
气氛寂静,光线暧昧,空气里有丝丝幽微的热息在萦绕,李牧星把持不住,就要反手触碰那处肌肤,却先听到郎文嘉的肚子传来叫声。
两人顿时僵住。
这下轮到李牧星捂嘴偷笑,郎文嘉难为情地摸摸鼻子,他一整个晚上都没吃东西。
“我去买点吃的给你。”
----
本来想说今天要双更,可是我感觉我会写到半夜去。
(然后依旧不敢看评论区,更新完立刻跑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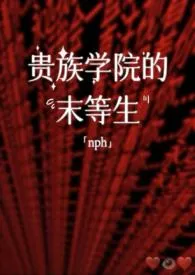
![[HP]獾乐小厨娘(慢热np)](/data/cover/po18/843926.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