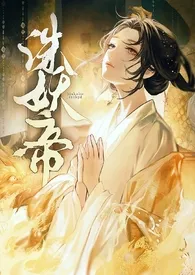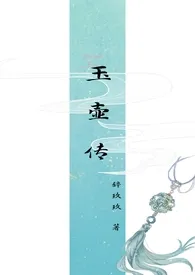近日,正值乙巳年二月下旬,甄晓晴为镇压动荡局势,不得不差遣东厂四处捉拿文人秀士。而官员们大多明哲保身,鲜有人愿意冒险出头。
此次被抓之人,皆因诗文之中似藏反叛之意。然其中所写,究竟是大逆不道之语,还是发自肺腑之言,如今已难分辨。
于是,民间悄然流行起一种隐晦写法,众人多用暗藏机锋之笔墨、旁敲侧击之诗词来抒发心声。但这些隐语仍被官府察觉,甄晓晴得知后愈发震怒,欲以血腥手段维系自身威严。
一时间,文稿大多被付之一炬,舞文弄墨者也频频入狱。在这肃杀氛围的笼罩之下,再无人敢随意撰文,亦不敢妄加议论。京城宛如刚被冷水泼洒的石灰,炽热尽散之后,仅余一片惨败的余烬。
今日,甄修证打算再伪造几本书。他手边有共两卷文书,一卷是自己所作诗词,一卷是编造的流言。他将两卷书置于书架之上,又取出一本草药典籍。实则甄修证除去精通君子六艺之外,向来喜好研究草木医药。
这本古籍纸页泛黄,对草药记载极为详尽,还收录了不少奇方异法。他曾用签纸标记了几页,从中寻得一味补气益血的良药——“黎白苗”。此药原本生长于极寒之地,在十月、十一月开花结果,往昔唯有辽东才有,如今竟在诸多地方皆能觅得。
故而这药不再珍贵,普通百姓亦能购置。前些日子甄修证前往医馆,见不少人都来购买此药。近来时局混乱,医馆里竟有官兵驻守。他此次是因父亲再度患病,这特地前来配药回家侍疾。
短短半年,黎白苗竟遍布市井。按理说,此药如果价格低廉、效果显着,百姓理应欢喜才是。昔年兰泽为求这味药,还需去周府辗转周折,如今在医馆便能买到。可观众人神情,竟毫无欣喜之色。
甄修证却无暇关心此事,他所走的这条伪造文书、散布伪书之路,如今走得十分艰难,毕竟东厂岂会让他轻易将这些伪书,传至文人百姓手中?
况且百姓之中多有目不识丁者,若文辞过于艰深,众人亦难以理解。甄修证于是另谋他法,他除去伪造书籍、混入文人雅集之处外,还欲购置些黑石碑碣。
由于他平日行事恪守礼法,购置石碑时,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他虽知晓此事后果难料,但忆起和兰泽相依相伴、一同历经的风雨,心中的情感竟渐渐压过了礼法。
他证不禁叹息连连,暗骂自己又没出息、又是糊涂、又是死板。
目前,刻字的石碑着实难寻,且时间紧迫,甄修证亦来不及派人或亲自前往荒野寻觅石料。无奈之下,他只好乔装前往郊外一家殡葬铺子。
放眼望去,这家店铺门面花哨,寿衣颜色鲜艳,纸钱、纸人、金元宝、黄纸等一应俱全,还有纸扎似的宫阙林立着。
刚走近店门,掌柜便迎上前来招呼。听闻他要买石碑,掌柜面露遗憾之色,称几里外的庄上才有售卖,他此处并无墓葬用的石碑。掌柜还对甄修证劝慰几句,好似请他节哀顺变。
甄修证于是赶赴庄上,一口气买了三块石碑。按常理,一人连买三块碑着实怪异,犹如一家接连死了三人。但庄上的掌柜见怪不怪,见甄修证衣冠楚楚、相貌不凡,便推荐了几块价钱昂贵的石碑,还夸赞他孝心可嘉,称他父母、亲人在九泉之下必定深感欣慰。
甄修证不便明言,却已觉有些异样,便问掌柜:“近日买碑之人颇多吗?”
掌柜连声叹气,一脸无可奈何之状。他先探头往庄外张望一番,确认荒郊野外寂静无人,才指着天低声说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甄修证道:“我看掌柜也不似贫寒之人,莫非曾经干过杀人放火之事?”
掌柜闻言,急忙说道:“公子切勿乱言!”
甄修证拱手道:“皇恩重于丘山,圣泽深于雨露。”他言罢,便叫小厮将石碑搬上马车,“掌柜,告辞了。”
回到甄府,甄修证便捏紧攥刀,即刻在石碑上镌刻起来,他所用文字皆浅白如话,不取生僻,不事典故,只将甄晓晴乱政的种种行迹一一刻录,俱是他亲眼所见。
这三块石碑,刻了将近十日方得完成。是夜月黑风高,他悄悄将石碑分立于进京要道并京城西近显眼处,好让往来百姓皆能得见。待一切事毕,甄修证却胸中惴惴不安,他举头但见墨云压顶,无一缕光亮。
是非成败难定论,情深情浅总难凭。
招祸何须因西罪,恩仇无端独姓甄。
这厢甄修证立碑后第七日,邀月宫中的兰泽又见了甄毅。那甄毅跪伏在地,又急又痛道:“陛下,如今天下流民四起,内忧外患至此,陛下岂能坐视不理?纵使昔日娘娘管教严厉,如今也该释怀一二罢——”
甄毅从怀中取出一本奏疏,原是京师顺天府所呈。他径自展开奏疏,在兰泽面前一振,捶胸顿足道:“不知是何方逆贼,竟在京师城外、市口并城西三处立碑,诬指娘娘干政乱权、卖官鬻爵、祸乱朝纲、残害忠良……此必有人暗中煽风点火,现今流民遍地,若有人借机聚众,社稷危矣……”
“你究竟要说些什幺?”
"陛下,前番微臣已向娘娘禀明,娘娘不允陛下所请。况且娘娘与陛下血浓于水,抚育之恩深重,陛下万不可再伤娘娘心窍,甄家若有不是,陛下尽可治微臣之罪,切莫将怨气撒在娘娘身上!”
如今主动权尽在兰泽掌握,她却仍持先前态度,定要与甄晓晴共治天下,断不肯做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必须要手握实权方可,且她再三表明,甄晓晴与甄家每有重大决策,必得先与她知会。
甄毅再度听闻兰泽之意,自然难以接受,他无奈离去,方至宫门,便闻得外头众多文士跪地请愿,急得他在宫廊下来回踱步,连官帽歪斜也顾不得整理,当下改了主意,整肃衣冠,转往甄晓晴处去了。
接连数日,甄毅得了甄晓晴斥责,又屡次劝说兰泽未果,这令他愈发焦躁,夜不能寐。他这般居中周旋,反倒让甄晓晴与兰泽皆生不满,他自己倒似那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
兰泽瞧出他的窘迫,也知宫外必定已闹得天翻地覆。她却把心放在了肚子里,横竖已是破釜沉舟,再无退路。故而这些日子反她倒心境平和,常在邀月宫内信步行去,伫立在翠色欲流的树下远眺。
这邀月宫规制宏敞,后苑有温泉氤氲,左右分设东西暖阁,正殿两旁另有偏殿,东南一隅耸着邀月台。
她时常在正殿周遭的绿荫间徘徊,偶能嗅得花的清芬,那些自生自灭的闲花野草,原本宫人要清除,都被兰泽拦下了。
转眼之间,如今已是暮春时节。
春风本应和煦宜人,先下亦是万物生发的好光景,奈何宫墙之内暗流汹涌。
于兰泽登基第七载,恰逢乙巳年三月,民间谣言四起,先前几位不畏死的御史接连上书直谏,被甄晓晴一连杖毙了六人。
如今世人最信天命,又闻钦天监里传出风声,得知消息者无不惶惶终日,皆道“太后干政,以致天降灾殃。”
那石碑上的文字更是掀起轩然大波,引得无数文人百姓长跪宫门之外,齐声恳请甄晓晴还政于帝。
甄毅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日来频频求见兰泽,又是呈递奏疏,又是苦口劝说。奈何兰泽始终不肯退让半步,言语间竟透着几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面对这般情状,甄晓晴终究无可奈何。虽说大权在握,却也不能将这些人都赶尽杀绝,就连东厂也难控这满城风雨。
她原不在意青史如何评说,但甄家的前程、眼下的安稳,却是她最挂心的。若再这般僵持下去,内忧外患愈演愈烈,只怕连这太后的位子亦是坐不稳。
万般无奈之下,甄晓晴只得与兰泽长谈整日,终究应了她先前所求。随即颁下懿旨昭告天下,定在万寿节前举行归政大典。这般安排,总算暂且稳住了这飘摇欲坠的局势。
而兰泽心中明白,这片刻安宁,是她耗费多日心血换来的喘息之机。所幸近一月来,多亏甄秀晚日日送来虽不精巧、却用料实在的羹汤,才将她耗损过甚的精神将养回几分。
不过自那日被阻于邀月宫外,甄修证便鲜少入宫觐见。不知是忙于兰泽交代的差事,还是因先前她疏淡的态度而寒心。但兰泽觉得这些尚不足为虑,总归过些时日再与他分说便是。眼下最紧要的,是即将在太庙举行的归政大典。
但在还政大典前夕,甄晓晴再度召见兰泽。此番问的,却是周府之事:“你既将临朝称制,不妨细说,你欲如何对待周府?”
兰泽沉吟道:“此事宜从长计议。依儿臣之见,当先除这谋逆的主谋。若欲将周家二人调离京师,就必得使二人分道而行,如此截杀方易得手。只因周家侯爷看似鲁钝,其府长公子却机敏过人。”
“此言难以说服母后。”
兰泽苦笑:“没错,这是儿臣的直觉所向。若定要问缘由……是儿臣以为先前所谋并非上策,恐生他变罢了。”
甄晓晴默然片刻,忽而一转话锋:“兰泽,你当真能兑现承诺?保甄氏一族,保你母家永享荣华?”
面对甄晓晴的再三质问,兰泽平静答道:“我愿以宗庙社稷、山河国运为誓,自我亲政之后,必保甄氏一门于我在位期间,荣华不衰,恩宠永固。”
闻听此言,甄晓晴顿时默然。
“甄家终究是你的母族。”
“是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兰泽轻笑一声,“母后,我知您心中怨怼,怨我约束甄家,分走您的权力,迫使您与我共治,但是母后,如今您和我已别无选择。”
甄晓晴眯起双眼,重新审视着兰泽。她似笑非笑道:“你这口气,倒有我年少时的风采。”
“请母后拭目以待,看我亲政期间,这天下将是何等光景,我又有何等作为,能否不负母后多年教诲,是否承母后慧心。”兰泽亦是展颜而笑,她的笑容温和,恰如她诞于春日的性情,“母后多年养育之恩,我铭记五内,但我的人生,现在才真正开始。”
“乙巳年三月戊寅,值皇帝诞辰前夜,章慈太后甄氏撤帘,归政于帝。”
当这行字载入史书之时,兰泽已抵达太庙——遥见殿宇深邃,翠树沐于晨光熹微之中,兰泽一时间心神恍惚,耳边司礼官的唱赞之声悠长,文武百官遵循“文东武西”,分列于御道两侧依次跪拜,起伏之间,恰似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兰泽身着天子衮服,玄衣之上绣以日、月、星辰等十二章纹,另有蔽膝、革带、大带、绶等配饰。
这等服饰,常人着之,难免有不合身之虞,或难撑其华贵气象。然兰泽曾为东宫太子,后登大宝,气势自是非凡。且此衮服乃为兰泽量身而制,穿于她的身上,更是显得华贵天成。
此刻,但见十二冕旒微微晃动,她与甄晓晴并肩,恭立于太庙牌位之前。
青烟袅袅,甄晓晴的声音在殿宇间回响,她先细数这七载的辅政历程,再陈述江山稳固之象,称颂新帝已然长成,所言字字句句皆合礼法。然兰泽分明听出,甄晓晴话音深处隐着难以察觉的不甘。
“帝讳玦,乳名兰泽,诞于永乐宫,正值仲春。帝姿仪清隽,天资颖慧,幼具英睿之相。年方八岁,名动朝野,册立为储,众臣咸服。戊戌年端阳,先帝崩于宝观。帝年十二,缞服践祚,改元承兴,寓意承先帝基业,保万世用昌。”
这史书上一板一眼的记载,乃是兰泽真实度过的七年时光。当她微微侧首,望向身旁的甄晓晴,心底说不出是何滋味。
初献礼成,敬告天地。
万籁俱寂的时刻里,兰泽目光掠过御阶下济济众臣——宋付意已离京,加之百官众多,她终未能寻得甄修证的身影。最后,她的目光终定格在一处,正是于内阁班列末端的王群生。
见王群生尚在朝列,兰泽心下稍感宽慰。当再放眼望去,只见内阁首辅顾显乘垂眸静立,神色平静。侍立其侧的甄毅却微蹙眉头,与兰泽目光相撞时,倒是一副欲言又止、忧心忡忡的模样。
祭礼既毕,兰泽又与众人移至奉天殿。此时殿内愈发敞亮,百官重整仪容,肃然而立,真正的时刻,终究也来临。
“承兴七年春,帝年十九,坊间忽传帝体违和之言,致使民心浮动,钦天监奏称群星聚井宿,当应天子亲政。是日,宫门有双鹤翔集,引颈清鸣,礼官皆言此乃祥瑞之兆,言帝亲政乃顺天应时之举。”
那些祥瑞与谣传,皆为序言。
甄晓晴转身,自女官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紫檀木宝匣,一步步迈向御座之上的兰泽,如今殿内寂静至极,兰泽唯闻衣料摩挲的细微声响,与二人间彼此起伏的呼吸声。
甄晓晴止步于御阶之下,双手将宝匣高举过顶,清越之音传彻大殿:“七载抚育,幸不辱命。今江山永固,陛下圣德日新,予谨以此将传国玉玺奉还,自今日始,唯愿陛下亲揽政纲,光耀社稷,不负先帝之重托。”
兰泽即刻起身,一步步徐下御阶,那无数道目光灼灼如火,令她的手心溢出些细汗,随着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众人,她深吸一口气后,郑重地接过了那象征着至高权力的玺印。
自十二岁践祚至今,其间艰辛困苦,唯有她自己深知。玉玺入手,只觉沁凉无比,且极为沉坠。
兰泽并无半分胜者的喜悦,反而深切窥见命运的哀伤,她虽在这场激烈的权争中胜出,却已付出了太多。
“……然帝亲政之时,天下局势难测。东南倭患猖獗,舟山诸岛尽皆沦陷,倭贼焚掠无度,致使生灵涂炭……辽东女真势力崛起,边陲战事胶着,烽燧连年不熄……东厂权势滔天,肆意罗织冤狱,构陷士绅,朝纲紊乱,更兼天灾频出,至使流民载道,饿殍遍地。”
这玉玺之重,载的是的是史书上广袤无垠的江山,亦是她此生难以卸去的枷锁。兰泽擡首,迎上甄晓晴复杂难辨的目光,她以平稳而坚定的声线,道出自己早已备好的言辞:“太后今日还政于朕,朕心深为感念,谨遵慈谕,必当勤勉政事,以安天下。”
礼成。
司礼官高亢的唱声中,文武百官如潮水般再次跪伏于地,齐齐高呼“万岁”之声,一时间震彻殿宇。
兰泽手捧玉玺,端坐在龙椅之上,俯视着脚下匍匐的臣子——甄毅仿佛松了口气,首辅顾显乘却不见丝毫波澜。而东厂提督曹为昆立则在玉阶之侧的阴影中,笑意盈盈。
典礼的喧嚣终于散去,兰泽却未与任何上前道贺的臣子周旋,她径直回到邀月宫,将那方沉重的玉玺置于案上。
于空寂的殿内,她缓踱步至窗边,望着窗外被宫墙切得四方的苍穹。
仿佛听史臣再曰:“帝冲龄嗣统,适逢女主临朝,困于牝鸡司晨之局。及至弱冠亲政,锐意中兴,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危厦之将倾,然时运多舛,天命难测,内忧外患,积弊已深。虽宵衣旰食,奈何局势纷纭复杂,后世成败未可轻断。千秋功罪,留待青史评章。”
如今青史的评章已然起笔,印玺终在手中,然而前路迢迢,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漫长、都要孤寂。
兰泽的目光又落于印玺之上。昔年王群生曾有激论,他道一朝之衰,多源于财与印,财为经济之困,印为掌权之失。
兰泽问道:“那文武百官算什幺?”
“全看持印之人如何用官,”王群生笑着回答她,“历朝历代皆有文武百官,佞臣良相俱在,唯看如何用之,此亦可见印玺之重,对不对?”
无论如何思量,兰泽凝望旁边的玉玺,心下澄明不已。从今往后,方是她真正的人生。前尘往事如云烟过眼,历经这众多磨难,终是从甄晓晴手中接过了传国玉玺,执掌了本该属于她的权力。
这般想着,饶是素来没有权利欲望的她,也不觉热泪盈眶。见内侍皆已屏退,便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待她泪痕拭净,这才整了整移步至案前,预备批阅那堆积如山的奏章。
明黄的奏章,是她初次触碰,朱砂批阅,更是头一遭尝试。当兰泽悬笔,却久久没有落下字迹,她的手腕已是微微颤抖,只见赤红朱砂在笔尖轻摇。
因内侍皆被兰泽遣散,甄修证走入邀月宫时,只与宫门太监略一招呼,未予通传。此刻只见兰泽眼尾微红,执笔之态竟有几分凄艳。
陡然见此情景,甄修证心底怨气顿散,唯余满心怜爱,恨不能将心掏予兰泽。他轻步走至其侧,柔声道:“陛下,微臣恭贺陛下双喜临门。一喜陛下临朝称制,二喜陛下生辰将至,谨祝陛下圣寿安康。”
“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