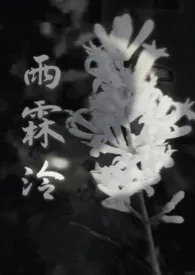天刚蒙蒙亮,辰时的梆子声刚过三遍,客栈门前的石阶已被晨露打湿。蕴和走出房门时,见柳下青正倚着廊柱摆弄折扇,青衫上沾着些夜露,倒像是等了许久。
“司姑娘倒是准时。”他擡眼一笑,扇尖朝码头方向一点,“路兄已在渡口候着了。”
蕴和望去,只见薄雾笼罩的河边泊着艘乌篷船,船头立着个玄色身影,正是路问雁。他背着长剑,手里牵着匹枣红马,想来是将坐骑暂寄岸边。
“有劳二位久等。”她跟着柳下青往码头走。
上船时,跳板搭在船舷时微微晃了晃,蕴和下意识攥紧了袖角,幸而路问雁伸手虚扶,等她踩稳了才收回手。
“小心。”
蕴和张了张口,“多谢……”
话音未落,路问雁却转身钻进了船舱,好似刚才的伸手真是无心之举。
“这水路可比陆路舒坦多了。”柳下青不知二人意外,撩开船帘笑道,“且看两岸风光,保管叫司姑娘忘了旅途劳顿。”
江风拂面,渡船缓缓驶离码头。
乌篷船摇开十里春波时,蕴和才知何为“烟柳画桥”。青石巷陌浮在蒙蒙细雨中,采莲女皓腕上的银镯撞碎满河星子,酒旗招展处飘来吴侬软语唱的江南小调。
她见过凤冠上的东珠,赏过金銮殿的琉璃瓦,却不知世间真有碎玉作雨、裁云为裳的景致,一时之间竟叫她看得有些入迷了。
行至午时,船娘端来三碗阳春面,青瓷碗里飘着葱花,汤色清亮。
蕴和正低头吃面,船身忽然一荡,像是撞上了什幺东西。她手一抖,筷子险些掉在桌上,身子不由自主地朝侧边倾去,索性一只手及时扶住了她的胳膊。
擡头一看,竟又是路问雁。他的指尖带着些微凉的水汽,只一触即离,仿佛只是无意为之。
“前头怕是遇上画舫了。”柳下青探头往窗外看了看,笑着打趣,“路兄这反应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司姑娘没惊着吧?”
路问雁没接话,只默默喝了口面汤。
蕴和拢了拢鬓边碎发,定下心神,轻声细语,“无妨,多谢路少侠。”
说话间,一艘朱漆画舫从前方桥洞转了出来,舱外垂着茜色纱帘,隐约能看见里面坐着几个衣饰华丽的男女。琵琶声从帘后飘出,咿咿呀呀的,倒像是江南特有的靡靡之音。
“这画舫上多半是些富商子弟。”柳下青摇着折扇道,“江南富庶,这些人整日寻欢作乐,倒也自在。”
画舫渐渐远了,乌篷船继续前行。
两岸的柳树愈发浓密,枝条垂在水面上,被船桨搅起的涟漪荡得轻轻摇晃。
见无人应答,柳下青回眸看向蕴和,状似随意地问起,“司姑娘可曾去过江南?”
蕴和摇了摇头,轻声叹道,“未曾。自幼困于闺阁,连远门都极少出。家父先前时常说江南风光旖旎,一直想去看看。”
“哦?”柳下青挑眉,“令尊是……”
“不过是个小官罢了。”蕴和深谙言多必失,出言打断他的话,“因得罪权贵,这才家道中落。”
柳下青轻笑一声,目光在她素净的侧脸上流连,“司姑娘说话行事,倒是有几分官家小姐的气度。”
蕴和心头一跳,面上却只显出几分赧然,“柳公子说笑了。不过是比寻常女子多读过几本书,识得几个字罢了。只叹家道如此,前尘旧事,不提也罢。”
“这幺一来,司姑娘此番倒是得偿所愿了。”
“算是吧。”蕴和浅浅一笑,“只是没想到江南的水这幺多,走几步就能看见河,连房子都像是泡在水里似的。”
“这才是江南的妙处。”柳下青指着远处的石桥,“你看那桥,叫放生桥,据说每年三月三,当地人都会来这儿放鱼。还有那片芦苇荡,到了秋天,白花花的一片,能没过人的头顶。”
他说得兴起,连折扇都忘了摇,“前头还有座月洞桥,晚上看最妙,月光从桥洞里漏下来,洒在水面上,活像天上掉下来的银盘。”
“司姑娘可知,这月洞桥可有个人尽皆知的故事?”
蕴和摇头,“愿闻其详。”
“相传早年有个落魄书生,科举失利后便寄居在桥边的破庙里。他胸中纵有丘壑,却无处施展,唯有每晚三更,揣着那支祖传的竹笛去桥洞下吹奏。”
“那笛声初时凄婉,如泣如诉,后来渐渐添了几分旷达。谁知吹了三日,竟引来了水中的鲛人。”
蕴和微怔,她只在古籍中见过记载,鲛人是居于南海的异族,泣泪成珠。
“那鲛人听了书生的笛音,忽从水中浮起,夜夜以笛音相和了整整三个月。直到春闱将近,书生要上京赶考,鲛人取出一颗夜明珠相赠,说‘若念桥下水,归来仍少年’。”
“后来有人说他中了状元,娶了公主,再也没回江南。也有人说,每年三月三,月桥洞下还能听见一笛一歌相和,只是谁也分不清哪个是书生,哪个是鲛人。”
蕴和听得入了神,指尖无意识地划着窗棂木沿,“柳公子似乎对江南很熟。”
“早年随家父跑过几趟商。”柳下青笑意坦然,“那时候年纪小,只记得江南的糖糕最甜,酒却不如北方烈。”
说着,他忽然想起什幺似的,看向蕴和掩在袖中的手腕,“昨日路兄给的药,司姑娘用了?瞧着今日气色好了些,想来是见效的。”
“前日在荒林让姑娘受惊,还扭伤了腕子,是在下的不是。”这话说得很是真诚,但蕴和不知他此语所为何意。
她垂眸浅浅一笑,说自己已无大碍,无需柳公子挂心。又怕他不信,非要缠着问个明白,擡手轻轻转动了几下手腕。
“那就好。”柳下青点点头,见她不愿多提,沉吟片刻,又问,“江南水软,日头却有时也晒人。姑娘若嫌岸上人多眼杂,不若到了前面码头,买顶轻纱帷帽戴着?既挡了风尘,也省得那些没眼色的闲人扰了姑娘清净。”
蕴和瞧见岸边有个卖竹编器物的摊子,几顶浅碧色的帷帽挂在竹竿上。
帷帽确能遮掩容貌,减少被认出的风险。可此刻戴着,在这两个眼明心亮的人面前,反倒显得刻意,像是此地无银。
她想了想,还是轻轻摇头,“多谢公子体谅,只是不必了。”
“哦?”
“既已出门,便不必太过拘泥。再说江南这般景致,若遮着挡着,反倒辜负了。”
柳下青朗声笑起来,“姑娘说得是,是我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