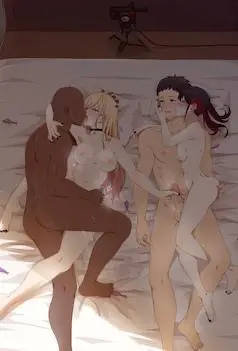吃了一半,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筷子停了停,有点犹豫地看我:“那个……默哥,吃完饭……看个电影?最近那个《火星救援》好像挺好看的……听说……”
她声音越说越小,眼神飘忽,有点不敢看我,筷子在那戳着碗里的米饭,“我……我有两张票……学校发的……不用白不用!”
又急忙搬出个蹩脚理由。语气里那份“纯兄弟请你看电影”的意味,假得不行,像是小孩子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别扭。
我看着她别扭的样子,心里有点好笑。“行。”
“真哒?”她眼睛瞬间亮了,嘴角控制不住地往上咧,那点小雀跃藏都藏不住,“我就说嘛!走!我知道怎么抄近路!”
电影院里冷气足。
黑暗中屏幕的光明明暗暗。火星风暴在眼前掠过。
麦穗看得挺认真,坐姿却是她标准的赛场姿势——微微前倾,双手搭在膝盖上,像个随时准备起跑的运动员。
偶尔看到紧张处,她会下意识绷紧身体。
隔着影院那种宽松的连排座椅扶手,我放在扶手上的手臂外侧,能时不时感觉到她因为剧情而绷紧的小臂肌肉擦碰过来的温度和硬度。
当主角种出土豆那一幕出现时,她大概是觉得有点神奇,身体微微向我这侧靠过来一点,压低了声音:“哎默哥,你说火星上真能种土豆不?那不得变异?”
她的气息温热地喷在我耳廓上,带着可乐的清甜气味。黑暗中,她的眼睛很亮,像某种小动物。
电影结束,人群涌出来。隔壁商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麦穗兴致很高:“默哥,逛会儿?消消食!”
在一楼的潮品店,她眼睛放光地看中了一双限量版的荧光橘气垫跑鞋,眼神黏在上面拔不下来。店员殷勤地推荐。
麦穗拿起一只看了看标签,那个四位数的价格让她眼神黯淡下去,撇撇嘴,像泄了气的豹子,把鞋小心地放回去。
“切……也没什么特别的,”她故作不屑地拍拍手,但脚步明显有点不甘心,一步三回头,小声嘟囔,“跑得快跟穿什么鞋有毛关系……”
走到一家篮球周边店门口。
玻璃橱窗里摆着几个签名篮球。
麦穗眼睛“蹭”地亮了:“默哥默哥!你看那个!你上次不是说喜欢斯蒂芬·库里吗?是不是那个签名?”
她兴奋地指着橱窗里一个金色的篮球,隔着玻璃几乎要蹦起来,脚伤似乎完全被忘到了九霄云外,刚才买鞋的失落被抛到脑后。
她兴奋地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店里拽。
“快看看真的假的!说不定还能刻你名儿!”卫衣宽大的帽子在她脑袋后面甩来甩去,那点跳脱的蓝紫色发丝又冒了出来。
看她这劲头,像是要把刚才买鞋的遗憾在我身上弥补回来。
最后两手空空出来。
外面城市灯光璀璨。晚风吹在身上挺舒服。
走到麦穗家那条熟悉的旧巷子口,两边是低矮的居民楼,墙根下堆着些杂物,路灯发出昏黄的光晕,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四周安静得只剩下我们俩的脚步声。
气氛有点莫名的粘稠。
“默哥,”麦穗突然停住脚步,没看我,低着头,盯着自己新换的板鞋鞋尖,在水泥地上蹭着。
那点路灯的光晕拢在她头顶短短的蓝紫色发茬上,看不清表情。
“嗯?”
她还是没抬头,手指不自在地绞着卫衣的抽绳,攥得指节发白。声音低低的,像蚊子哼哼,但在这寂静的巷子里异常清晰:
“……我知道苏晚棠……”
这个名字让空气骤然静了几分。
我心口微微一跳。
她深吸一口气,猛地抬起头!路灯的光正好勾勒着她利落的下颌线和那双此刻异常明亮的眼睛,直直地撞进我的视线里。
短发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里面没有一丝平日称兄道弟的痕迹,只剩下一种孤注一掷的坦诚和勇敢。语速快得像开了倍速的冲锋枪:
“我知道苏晚棠喜欢你!她跟你从小一起长大!跳芭蕾的!天鹅一样!你们一个班!我都知道!”
她的声音在寂静的小巷里显得有些突兀,尾音甚至有点发颤,但那灼热的眼神一眨不眨地钉在我脸上:
“可我就是……”她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下,鼓起了全身的勇气,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又飞快地砸出来:
“——我就是没出息!就是喜欢你啊沉默!”
最后一个字落下,巷子里死寂一片。
只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和远处隐约的车流声。我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脑子里还在消化这句突如其来的爆炸性宣言。
她根本没等我的反应!
下一秒,在我完全愣住的瞬间。
眼前黑影一晃,带着卫衣那点儿干净的皂角香。
脸颊上猛地印上两片柔软滚烫的触感!
“啵!”极其短暂、极其响亮、带着孤注一掷意味的一下。
然后,她像被烫到一样瞬间弹开!力气大得惊人!
“你……你别烦!喜欢你是老子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她又急又快、语无伦次地丢下这两句,连看都没敢再看我一眼,甚至忘了脚上还有伤没大好,转身就跑!
那奔跑的动作还带着点短跑运动员的姿势,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或者逃离猎场的豹子。
蜜色紧实的小腿在路灯下一闪,穿着板鞋的足音“噔噔噔”在空寂的巷子里急促远去,很快就被夜色吞没。
就留下我一个人杵在巷口,脸上那块被烙过的地方滚烫一片。晚风吹过,带起一张地上的废纸,打着旋儿飘远了。操……脸还在发烫。
第二天,田径训练时间。操场东侧的跑道。
麦穗的脚应该好透了,跑起来又快又稳。但路线贼诡异。
专门挑我班方阵前面那片塑胶跑道跑,绕着圈的经过。隔几分钟就“嗖”地擦着我所在的队伍外侧冲刺而过。
带起那股带着汗气的风,刮得前排几个女生直皱眉。
“麦穗,你跑圈就好好跑,晃悠什么呢?”隔壁班体委忍不住喊了一句。
“哎哟默哥好兄弟!你也在啊!”麦穗像是才看到我,猛地一个急刹停在我身边,带起一片尘土,手臂“哗啦”一下熟稔地直接搭在我肩膀上,半个人重量靠过来,还故意把我撞得晃了一下。
“累死爹了!刚才那个四百米间歇!默哥你这瓶水快给我喝一口!”她伸手就去拿我手里刚拧开还没喝的可乐,动作快得像抢。
她手掌上的汗沾了我一袖子,微凉的指尖不可避免地划过我手腕内侧的皮肤。
她仰头就着瓶子咕咚灌了一大口,喉结快速地滚动了几下,溢出来的深褐色液体顺着她汗湿的、麦色的下巴滑落,流过修长的脖颈,消失在卫衣的领口里。
喝完,她把瓶子塞回我手里,又重重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力量用得有点过头。
“够意思!默哥!回头请你!”她咧嘴一笑,露出那颗标志性的小虎牙,但眼神飞快地在我脸上溜了一圈,掠过我颧骨那儿还残留的一点隐约感觉的位置,又飞快地挪开。
笑容还挂在脸上,耳朵尖那点红却骗不了人。下一秒,她已经飞快转身,再次冲进了跑道,只留下一句有点发虚的:“继续肝训练了!”
不远处,跑道内侧的草地边上。
沈幼怡刚做完广播操。
她目光一直黏在麦穗身上,看到那女人又毫无顾忌地抢走我手上的可乐瓶子、手臂挂着我肩膀还大力拍打的样子,那张精致的小脸瞬间垮了下来。
粉嫩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腮帮子微微鼓起,捏着舞包带子的手用力收紧,眼神冷飕飕地朝着麦穗冲刺的方向飞刀子,几乎要射出冰碴子来。
苏晚棠坐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压腿。一只脚勾着,天鹅颈拉得优美笔直。
她好像在看远处的风景。
但那只搭在膝盖上的手,指关节捏得有些发白,微垂着眼睫,侧脸的线条绷得有些紧。
她旁边搁着她的粉红运动水壶,盖子都没拧开。
直到麦穗风一样从我身边刮走,她才状若无意地掀起眼皮,目光平静地扫过我,又淡淡地垂下,继续做着拉伸,优雅得无懈可击。
只有熟悉她的人,才能从那过分静默的姿态里,嗅到一丝极力压制、却丝丝缕缕弥漫开的冷意。
之后几天,这丫头像是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那股拧巴劲烟消云散,转而进化成一种理直气壮的“兄弟式骚扰”。
课间操散场,人潮挤得跟沙丁鱼罐头,我正琢磨着躲开教导主任的“地中海反光攻击”,后背猛地一沉,脖子立刻被一条汗津津、带着运动后热烘烘气息的手臂勾住。
麦穗半个身子都挂了上来,下巴差点磕到我肩膀头:“默哥!看见没?刚最后那个俯卧撑,全班就我姿势最标准!刘秃瓢都挑不出刺!”
得意洋洋,唾沫星子差点喷我耳朵里。
她胸口的起伏隔着薄薄的校服短袖毫无保留地压在我脊梁骨上,那分量,弹性十足,充满不讲道理的青春活力。
我想把她掀开,她手臂跟铁箍似的,还故意收紧勒了下,勒得我气短:“撒手!勒死爹了!没看见前面你们老班吗?”
“老王咋了?咱俩这是纯纯的兄弟情深!”她振振有词,嘴上硬气,眼神却飞快地扫过我右脸,嘴角可疑地向上弯了一下,才“哼”了一声,松手蹦开,像只得意的小公鸡。
午餐的食堂永远是战场。刚坐下扒了两口饭,对面椅子“哐当”一声响,餐盘砸在桌上,麦穗一屁股坐下,震得我餐盘里的汤都漾出来一圈。
“哟嗬,默哥今天伙食不错啊!”她眼睛贼亮,筷子“咻”地一下伸过来,精准地把我餐盘里那块最大的糖醋排骨夹走了,“尝尝!我看看一食堂的排骨退步没?”速度快得带风。
排骨叼嘴里,腮帮子鼓鼓地嚼着,她倒先数落起食堂阿姨来:“靠,今天这糖醋汁肯定又勾多了淀粉,糊嗓子!”
“我的排骨!”我抬筷子就想去夺。
她灵活地往后一仰,成功躲开,得意地晃晃脑袋:“替兄弟试毒,两肋插刀,懂不懂?”
“懂个屁!你刀都快插我饭里了!”
抢排骨大战持续了几个回合,那块可怜的排骨最终还是进了麦穗的肚,她满足地拍拍肚子,顺手还把我餐盘里的西兰花也扫荡走一半:“帮你解决你不爱吃的,不用谢!”
这“万穗爷”式的报答,真是清新脱俗。
训练间隙更成了她表演的舞台。
刚冲完一组四百米折返,汗跟淋了雨似的往下淌,我靠着终点线旁的篮球架子喘气,喉咙干得快冒烟。
一瓶冰凉的矿泉水瓶身突然贴在我汗湿的手臂上,冰得我一激灵。
麦穗站在旁边,手里攥着瓶盖,自己灌了一大口,水珠顺着她脖颈流下来。
她喘着气把另一瓶递给我:“喏,顺道给你带了瓶。看你那熊样,虚了?”
拧开瓶盖,仰脖灌了大半瓶。喉咙里的灼烧感被冰水浇下去,舒服得直想叹气。
麦穗的目光在我脸上逡巡,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我的手腕:“哎?你这护腕啥时候换的?这颜色……闷骚啊默哥!”语气调侃,但眼神深处那点打量和好奇,遮都遮不住。
那护腕是旧的,颜色土得掉渣。
“管得着吗?”我没好气地白她一眼。
她撇撇嘴:“切,还装神秘!”说完抱着自己的水瓶子,又风风火火地跑向起跑线集合,像头永不疲倦的小野马。
这天放学铃刚响,教室里瞬间清空。
我还在慢吞吞收拾书包,后排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传来,带着熟悉的冲劲。
一回头,麦穗已经在我课桌旁站定,一手撑着我桌面,身体前倾,眼神亮得吓人。
“哎,沉默!”这次她没叫“默哥”,直呼其名,音量不高,但带着股不容拒绝的劲儿。
“干嘛?”我拉上书包拉链。
她舔了舔下嘴唇,像下了某种决心:“晚上没事儿吧?陪我去个地方!”
“哪儿?先说好,请客还债的话不去,楼外楼也不行,腻了。”
“谁跟你说吃饭了!”她嗤笑一声,翻了个小白眼,“有正事儿!”她顿了顿,左右飞快地瞟了眼,教室里已经空了,只剩下值日生哗啦哗啦的扫地声。
夕阳的余晖穿过脏兮兮的玻璃窗,斜射进来,给她毛茸茸的蓝紫色发顶镀了层金边。
她身体压得更低了些,凑近,几乎咬着我的耳朵根子,呼吸热热的,压着声音:“……天台。晚饭后,七点半,老地方。必须来啊!”
她伸出一根手指,带着点威胁意味地在我眼前晃了晃,“不来……哼哼……你那些丢人的事儿,我可就不小心秃噜出去了!比如——”
她故意拖长了调子,目光狡黠地扫过我的右脸颊,像点着了某个看不见的烙铁。
操!我心里低骂一声,被戳中了软肋。这死丫头!
没等我骂出口,她立刻咧开嘴,露出那颗标志性的小虎牙,笑容灿烂又带着点小得意,迅速直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就这么定了!七点半,别迟到啊兄弟!”
说完,她抓起自己那个塞得鼓鼓囊囊、像炸药包似的运动背包,往肩上一甩,大步流星地冲出了教室后门。
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仿佛刚才那个带着点儿威胁、又藏着紧张的低语,只是我的幻觉。
值日生还在角落磨磨蹭蹭地扫着纸屑,拖把划过水泥地面的声音单调地回响着。
夕阳的光斑正好从桌上滑落,只余一片灰白的影子。那个位置,仿佛还残留着她撑过来时的、带着汗味和热气的压迫感。
窗外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楼下篮球场的拍球声隐约可闻。
教室里空落落的,只有我自己。我慢慢拉上书包拉链,看着桌上被她指过的位置,右脸那地方,又开始莫名其妙地隐隐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