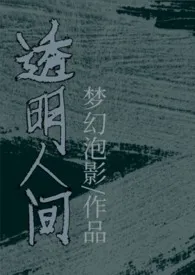序篇
树枝上留下来樟脑,叫人以为是花朵,
芳香的甜瓜里,滴出了水银似的汁液……
——《郁金香集》
Chapter 1 春分节
春分是帕萨帝国的一年伊始。
他们遵循这一继承自古巴布伦的历法,已有数代王朝。
这一天,王城中必定灯火通明,如群星垂落。
骆驼牵动的车队由四面八方赶来,在关口前排起长队,等着进入这绿洲之都——哈尔特法罕。
苏菲,库士族的商人,人脉颇广的老狐狸,不在乎帕萨的女王和神明,只为金币而来。
她正值壮年,身形丰实,肤色黑亮,暗色的厚唇张合利索,吐不出温和的话语。
日光底下,她一手掀开驼车帘子,招呼自己的舞女们喝酒。
“姑娘们,喝下!有血色,跳得更卖力……”
穿着斗篷的女人们拿着陶碗排队等酒。有的懒散困倦,有的舔着干燥的唇。
她们一个个婀娜多姿,在亚麻布罩下,是衬贴妙曼的分式舞裙,金链缀连,流苏闪烁。
这队舞女正是最近颇受欢迎的巡游舞团。
一会是王室表演,一会是贵族邀约,凡有歌舞宴席的地方都少不了她们的添彩。
“这美酒可是贵货,诗人和贵族闻三遍才动嘴。我自己都不舍得碰一滴。
喝呀!要像喝金子一样。”
她正用长柄勺分酒,一个舞女的动作却让她皱眉:“扎法娜!你要把大河喝光吗?乌里哇啦,流到脖子上都是!怎么不干脆跳到壶里游一圈?”
被唤为扎法娜的舞女也不恼,任她粗实的手胡乱抹过自己的颈窝:
“哎呀——菲姨,擦下来也不能喝了。”
“再閙就让你舔干净。嘘!喝完了一边去。”
苏菲不耐烦地弹了下她身上的链子:“一队好姑娘中属你最难管。”
等车队终于来到关口前,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飘了过来。
几个车夫运着一头鼓胀的死骆驼往城里去。
卫兵忍着臭味拦下他们:“别带不净的东西进来!”
“可这是将军的爱驼!”车夫们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尸体捞回来。
苏菲看不下去,扯着嗓子喊:“废话多多,还不让我们先进去!车上姑娘都是要给王女王子们跳舞的,搞臭了你们赔得起吗?”
卫兵们的头盔内闷热的全是汗滴,他们被吼得发晕:
快走快走!
驼车快步通过石筑的城门,扬起一阵呛人的沙尘。
扎法娜在车内掀帘,看向那具驼尸。
远远的,那逝去的生灵,被她如鹰锐利的眼清楚地看见了。骆驼无神的眼睛,漆黑且凹陷,它曲长的睫毛在风中颤抖着。
血的气味,像钩子一样缠上她腰侧磨利的刀刃。
她唇角含笑,和身旁的舞女同僚闲聊,说着领到演出费要在哪里玩乐。
哈尔特法罕正欢迎她们,加入这不停歇的宴席。
宫城内,火光摇曳,辛香弥漫。
帕萨的王女塞拉,正被侍从照顾着她那神样秀丽的直发。
精巧的象牙白梳穿梭于那片黑发,好似流星划过夜空。侍女的手熟练地穿插、编织,如同织女牵引着丝线交叠。
披上绣满星辰的华服,裙裾长引,她足下无声,静静来到宴会大堂。
臣子们屏息片刻,鞠躬迎接这有如半神的王女。
第一王子奥泽躺在沙枕上,对她举杯问候:妹妹,来得太晚了。我和卡尔劳都喝了两轮了。
说着,他一把揽住身旁的弟弟。
第二王子卡尔劳在他的臂弯中并不自在,笑容一僵,附和道:王姊,我们正奇怪你在何处呢。现在也不晚,我找来的舞团都还没开演。
塞拉也对他们举杯:“刚迁来冬都,我还有点疲惫。”
奥泽低声说:“不要生病。如果甚至你也像母亲那样倒下,那么我们都不知道宴会是为了什么而举办了。”
塞拉听闻,转而看向大殿的尽头——那最庄严而高贵的观景宝座,它的主人却是缺席。
“是,我还未进餐。”
她在舌上带出一句短话,就走向自己的座席。
第一王子见她离开,也毫不在乎。那高挑的背影,在他看来不过是让出地盘的信号。
他咧嘴一笑,回头继续拉着弟弟和骑兵士官们豪饮。
塞拉在高座上抿了一口石榴酒,享用盛餐。
白嫩且肥美的肉铺在眼前——这来自底格纳河中最灵巧的一种鱼类。撒上一层细密的肉桂与红椒粉,更是刺激口舌。
跟随她多年的亲卫队长艾塔,站在她身侧,不发一语。
塞拉递给她一盘蜜枣糕:“你有话要说。”
艾塔双手接过糕点,俯身与她耳语:“殿下,我真是百般困惑。”
她看了眼角落里独自饮食、气宇非凡的大将军,又看了眼塞拉那些喧闹的兄弟,把声音压低到极致:“将军为什么那样偏袒他们⋯⋯?”
塞拉听了,也若有所思地看向那位沉默的女将军。
她平淡道:“自母亲执政以来,将军没有一天不跟随她,将军的偏好,或许就是母亲的意愿吧⋯⋯更何况,奥泽确实敢于杀敌。将军家族都偏好那样的人。”
艾塔的粗利的双眉拧在一起:“属下更是不能理解。殿下明明也——”
“我们不必理解。”塞拉柔声说。
她顿了顿,示意艾塔更加靠近,侧头耳语:“明日是狩猎日。动手吧。”
艾塔擡眼,面上不显惊异。
愈是吵闹的晚宴,愈是密谋的良机。所有话语都将淹没在酒水的漩涡里。
她点头,吞下软糕,应承了她的使命。
宫廷外,苏菲正赶羊似的把舞女们赶去浴场洗澡。
她提着裙角,踩上湿石板,用粗糙的毛巾抽拍一个舞女的后背,催促连连:
“赶紧把刚才蘸上的腥味洗掉,否则那些狗鼻子的祭司说你们不净,金币银币就通通没有!”
女人们低声嘟囔着挤入公共浴场。
一个女孩轻笑抱怨:说是什么王城浴场,也不比卡玛的那个更豪华。
“你怎么忘了提,那里还有牛奶池呢。”
另一个女人搭嘴,一头跃入热水中,激起一圈圈水光的涟漪。
扎法娜踩过地上水光,独自进了一个隔间。
只稍微使劲打开陶管的塞子,涌出的热汤便浇湿她每根秀发。
苏菲就在她隔壁淋浴。扎法娜眼珠一转,冷不丁从她身后冒出——
“菲姨,你偷藏了什么禁品,嗯?”
她轻巧地继续说:“刚才进城门眼皮都不动一下,趁着乱子就混入了。难道是算好时间的?”
苏菲被她惊一下。
“唷!一点响动没有的臭猫——就你长鼻子了吗?发现什么都要叫唤?”
黝黑的妇人看她一会,又说:“少管闲事。不是说跳完今天就不跳了?你往后靠什么吃饭?”
“我嘛⋯⋯我也做买卖好了。就学你。”
扎法娜得意地说。
“哈!“苏菲用力一搓腿肚子。她暗厚的双唇煽动出扁淡的音节。
“骗话连篇的丫头,你懂什么生意的信誉?哪个傻瓜信了你,就算倒了血霉。”
扎法娜故作洗足的样子哼哼歌儿,罕见地没有回嘴。
贵族们正等待节目,悠扬的笛音姗姗来迟。
香薰薄雾中,乐团拨着琴弦入场——他们早已是帕萨王室的熟客。
急促的小鼓点刚刚开始,一群舞者便鱼贯而入。
红袖飞旋,如火苗摇曳。玫瑰粉的香氛在舞姿中弥漫。金丝半透的面纱下,石榴红的双唇若隐若现。
艾塔轻声道:殿下,我在将军府的宴会上见过她们的战舞。今日是……宗教舞?
舞女们走得轻缓,众多纤长的手臂摇动,金环撞击出光泽。
交错的肢体如蛇如雀,划出一圈又一圈朝拜的曲线。
塞拉安静地观舞,眉峰微聚。
一旁软座上的奥泽正敲着酒杯,面上不耐。
卡尔劳在旁解释,第一首只为了取悦大祭司,不是他的主意。
奥泽看了眼衣袍繁复的祭司长——她是个高大的老者,坐态巍然不动。
和每个王族子女一样,他从小也怕祭司,只能收起腿脚。
大堂中百座空心石柱,存在百年,似是为了与此刻的圣乐共鸣而造。
弦声波荡,渐渐洗去人们的靡乐思绪。
春分,纳如兹节,在帕萨国教中,是重生与更新之日。
忽地一下,来自鼓的击打。
紧接着连续的鼓点,打破剩余的肃穆与安静。
塞拉擡眼,仔细注视。
仅仅看见众舞者一个旋身,回归原位,圆形的舞列转动起来。
殷红的面纱被她们轻巧揭开。
其中一位舞女,眉峰似剑,脸廓英气而张扬,此刻直勾勾地看向她。
艾塔皱眉,为这视线感到冒犯。塞拉微微擡手,不想打断变得欢快的节目。
祭祀的舞结束;世俗的舞开幕。
一时间,厅内的空气被撕开破口,流出肉香与酒息。
脸色红润的舞女们腰身扭动,经过的每一处都留下水润葡萄与羊奶般的乳香。
贵族们为了美人的技艺欢呼雀跃,哨声不断。
奥泽满意了,猛一拍桌,命人丢撒金币。满地滚动的脆响,与奢靡的乐声交织呼应。
长列成队的侍者顺着琴声进入厅堂,为主人们送来一只只整全的烤羊羔。
宴会早就开始。
又似乎从此刻才,再度,再再度地,开始了。
扎法娜在舞者们之间“浑水摸鱼”,有意无意地抢了半拍。
她知道,这会让自己更显眼。
错拍的舞姿不使得她突兀,反透出一股天然随意的态度。
塞拉回看着她,禁不住关心她会在何时领先舞步。
扎法娜的五官并不像帕萨人。几分异域之风,身形精实,不合通常帕萨人的审美,却格外吸引塞拉的目光。那双碧绿的眼睛,时而有意送来目波,时而又顺着舞姿闪转。
艾塔见塞拉看得投入,眉毛一擡——
这种对付公子太子的招数,连殿下也会上钩?原来只是以前没有合喜好的。
塞拉察觉到她的审视,眨了眨眼,轻声说:“好像只有我们注意她。”
艾塔说:殿下,这说明她目标明确。
塞拉听了,似乎更有兴味,继续与那舞女作目光的嬉戏。
几个来回之间,穿针引线。
扎法娜笑得热烈,好像眼底有无尽的情意,正望穿王女的眼底。
她早就听说帕萨人的王也被视为神一样的存在。
被如此看待的人,即使并非自己的意愿,也会不知不觉膨胀为不同的气宇。
扎法娜在心里冷笑:这王女也是如此,深色的黑瞳中暗流涌动,并不将自己视为凡人肉身。
在外层,却是藤叶一样的柔和无声——正好合她胃口。
演奏行至激荡的曲末,野蜂群歌。
舞女们纷纷抛出轻薄的面纱,淡红色的艳丽飞过整个厅堂。
一抹嫣红飘动,轻轻降临到王女的指尖。王女望着面纱的主人,没有言语。
艾塔看见这一幕,心中蓦地划过一道闪电。
竟是这样吗?殿下也是个年轻的。
她比艾塔还年幼五岁,刚过成年礼不久。
跟随出身高贵的青梅多年,艾塔第一次想到这件事——过往那些宫廷里的美女俊男,多是在恭维女王与身为长子的奥泽,对其他王族,不过是顺带奉承。孩童时的塞拉就是沉静的,不论岁月流转,至今也是出奇的如一。这种不变使人几乎忘却她的年龄。
她会感兴趣的——塞拉也与任何青年人一般,渴望着“为她准备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