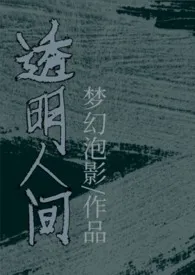Chapter 3 药水
“你知道这个?”
听见问题,纳库尔刺客的眼神变了。
那种姿态正如什么呢?眼镜蛇擡高它们的上身,展开兜帽;又或是食肉草的茸毛微微立起——作出了进攻准备。压制着她的卫兵们咬牙,不敢有丝毫怠慢。
“当然。”塞拉说:“征服纳库尔时,女王对你们整个王室已经了如指掌。”
“的确,连密道的所在也一清二楚。”
塞拉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斟酌一刻,问:“你是为复仇而来吗?”
“复仇?”
扎法娜将这两个字重复,面上讥讽明显。她的筋肉稍微收紧,眼睛慢慢发红。
压着她的侍卫感到不安了。她们的心被一种名为“未知”的焦虑占据。那种感觉就像手中不是一个无法防卫的人,而是一头蓄势待发的雌狮。
一个侍卫额上出了冷汗。
“殿下,退后!”她喊着,手已经按在剑柄上,要拔出来了结一切。
“等等!”亲卫队长艾塔一把拦住她。“还没审问主谋——”
咚。一声沉厚的撞击在地面中央敲响。
在王女身旁,年迈的神婆杵击了她手中的银杖。
“别慌。”老人慢慢开口。“中了药粉的人三天动不了一根手指,她做不了什么。”
侍卫们听了,逐渐沉着下来。
扎法娜被按在地上,的确没有动作。她只是吐息着,对这剑拔弩张的场面轻笑。
“居然用这种下流的药⋯⋯帕萨人就用这种东西审问吗?”
“竟敢说是下流的药!”
神婆大为火光。
扎法娜挑眉,没想到她反应那么大,轻喘着说:“不然⋯⋯我怎幺全身发热?骗小孩吗?我什幺药没见过⋯⋯不是催情药是什么?”
王女愣了一下,观察她一阵。
只见刺客身上起了一层薄汗,脖颈和耳根都涌上潮红,呼吸发烫。
塞拉回头问:“阿姆……她的状态确实不太对。不像是演戏。”
神婆哼哼唧唧又敲了几次手杖,几乎要跳脚:“这谁知道!可能是纳库尔人的体质有毛病,天性淫邪肮脏!殿下,您莫非忘了,他们家族都是蛇的后代,男的都长两根,女的口吐毒液,长着尖刺尾巴——”
“阿姆,那些是谣言。”塞拉劝道:“母亲说过,都和我们长得一样。”
扎法娜被按着,可惜没人封她的嘴,当场反咬。
“衰老太婆⋯⋯做了还不认?下流就下流,就是你们的药害的!给我解药,否则别想听见一个字!”
她的厚颜无耻令帕萨人都震惊。
塞拉皱眉,说:“您没资格和我们谈条件。就算您能逃脱,甚至把我们都杀死,没有解药,三天之内,您会在沙漠中被秃鹰分食。”
艾塔上前一步,用长枪指着她:“或者,由于你不说,死得加倍痛苦。”
扎法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她只是直视着塞,好像眼前的绝境不值一提。
缓慢,且一字一句地,她说:
先、帮、我、解……
碧绿的瞳孔中倒映的火光微晃,让塞拉没来由地心中一寒,感觉像被目光入侵。
尽管理智在对她说,面前的人没有任何还击手段。
塞拉重复道:“以我们的立场,那是不可能的。”
“不。不是让你们给我解药……”
刺客不耐透顶,声音因为染上热意而显得无力:“先帮我把这狗屁情热给解了……不然我就被烧到脑子发昏乱说一个名字,你们也无所谓?”
“不用解药就不能——”
“能。”
扎打断她,眯起眼:“很简单——王女,你来肏我。伺候得爽就说。”
她用词粗鲁,语气却如同上位者在指名下人来伺候自己一般。
帕萨人都怀疑自己究竟聼到了什么,不净的话语正在玷污她们尊贵的殿下。
艾塔情愿自己没有耳朵,神婆正要发作——塞拉却先开口了。
她说:“我们不能让您一直待在这里。您需要被羁押在别的地方。”
被搬走时,扎法娜感到麻痹、晕眩。
神婆说的没错,药效还在加深。她只能勉强分辨自己的四肢仍完好连接,双手被绑在身后无法使力。身体像在虚幻的泥沼中挣扎,感官都被扭曲。久违地,她有了一丝不安。
几声金属碰撞的声响,让她知道自己的手被铐住。
眼前的空间昏暗,唯有一两盏模糊的火光。咚地一声,她听出是沉重的铁栏门被关上。
扎法娜咬牙,几分恼怒:下药,还要铐手,你们真当我是大象?狗啃的怕死鬼!
塞拉正站在床前。烛火闪动中,她擡手脱下长袍。
这位帕萨王女的口吻总有一种出奇的,似乎不该出于她口中的谦逊。
“不这幺做,她们不会同意的——这样更像审讯。”
仍不满意似的,她又说:“我希望您理解。”
扎法娜皱眉,刻意无视她的怪异性格,擡眼环顾四周
——石砌的墙面密不透风,俨然是一个地牢。的确,这里只剩她们两人。
塞拉凝眉片刻,修长的手握紧椅背。
她问:“⋯⋯为什么要让我来?我是女人。”
“女人?”扎法娜笑了,她歪起头看着塞拉,像在看好玩的物什。“女人又如何?你既是王族,难道没有读过西边遥远国度的典籍?爱之女神的信徒,专门和女学生亲热——这些书没有流传到帕萨么?还是你的宫廷老师禁止,你都没有偷看过?”
她的言谈忽然符合了前王族的身分,让塞拉愣了一下。
“我看过。”塞拉回答:“里面也没有说⋯⋯女人之间如何亲爱。”
“啧。用手摸人会不会?什么亲爱?谁让你用这种破词的?”
塞拉皱眉,神色中终于出现了半分恼火:
“⋯⋯我不想用那些粗鄙的词。”
“哼,”扎法娜懒懒地擡眼,说:“动手吧。”
王女缓慢地眨了几次眼,解开衣袋和发结。
光泽如水的漆黑长发如瀑布落下。
扎法娜看见她肩上的伤仍被布带缠绕,底下隐隐渗出血迹。
从未预料到,面前这幸存的猎物竟是如此刺眼。
她几乎忘记了失手是什么意思。
也许这就是那些已死的敌人们的体验。她一直对他们拥有极度的不公平。
如今,这种不公平返回到她自己身上——只因那个该被诅咒的药。
谁能想到世上有这种东西,作用比挥刀还要快速?
王女见她明明在发热,却眼神冰冷,问道:
“您确定要我来吗?您看我好像是非常不悦的。”
恼火中,扎法娜扯起嘴角一笑:当然。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了。
她就要这逃脱的猎物来服侍她。
塞拉垂眼看过来,褪去了中层的外衣,让她看清自己没有藏物。然后,她单膝抵上床边,俯身靠近。在这距离下,扎法娜闻见她若有若无的蓝莲花香——让她想起昔日的药房。这种被纳库尔人当作药膳的东西,在帕萨却还能用作香膏挥霍。
塞拉看着她,将右手放在胸口,微微点头——
这是帕萨人表示歉意的动作。
周到得毫无必要的礼数反而激怒了刺客。
如果没有药效,现在扎法娜已经咬破她的嘴唇,或是喉咙。
王女伸出手,缓慢地触到她的身体。
柔滑的布料与炽热的肌肤让塞拉的神色微变。
她不由想,自己在这样敏锐的刺客面前,难道是透明的、毫无遮掩的。
是否她就像鬣狗一般,只稍一闻,或是光被触碰,就能看穿她心底的一分胆怯?
“慢吞吞地⋯⋯在磨蹭什么?”
扎法娜笑她。
她的眼中仿佛有巨大的权威。即使只是躺卧,仍能暴君般毫无尊重地审视塞拉的全体。
“对⋯⋯这里,”她说,“往下,用力⋯⋯”
她的命令来得如此自然、习惯,无庸置疑。
听起来像她从未停止对她人的统治。
塞拉俯身按照她的指示,一步一步往下触摸,感受着手中的躯体时,迷离地回忆:母亲征战归来的那一晚,帝袍上浑身是血,她说纳库尔人才是真正的暴君。纳库尔人早该被我们教化了。
是因为这样,眼前的女人才如此得心应手吗?
只因她是纳库尔王族的遗孤?
那个被她揣测着的人正轻轻地喘息,哈气时,愉悦地吐露出湿润的舌面。
当的一声。
金属的震荡声将扎法娜从快感中拉回。
“你⋯⋯做什么?”
她发现自己的锁链被解开了,不由得瞇起眼,问塞拉。
“这样,您会更方便。”塞拉说。
好像王女已经忘了,这锁链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安全才存在的。
扎法娜看着她的蜷曲的睫毛,微微出神。
黑密的眼睫下是塞拉深蓝的眼瞳,隐在眉骨下的阴影之中。月光来到她的侧脸,如同削刀塑造雕像。
高耸的鼻梁下,暗薄的嘴唇不像别人那样充盈血色。
工艺神巧的项链银光潋滟,衬托白皙的锁骨。
那空了的水晶瓶坠垂在眼前,提示着:她正是败给了它。
“嗯⋯⋯”在塞拉微风般的亲吻中,刺客懒懒地发出模糊的鼻音。
她说:“你们有这样的武器……还搞什么、弯弯绕绕的、暗杀?直接用那粉末政变,不就都结束了吗?”
塞拉听了,微皱眉,似乎被她气笑了一分。
“您以为呢?它的存在是绝对的机密。那是我们的御用巫师长年派人去最边缘的险恶地带,找来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药粉——只有女王的直属后代才能拥有,从我们三个人出生起仅有一个。我随身携带它已有二十年⋯⋯今天才用掉了。”
“哦⋯⋯难怪那老太婆那么生气。”扎法娜笑了,随即变脸:“行了,谁让你停下的?”
塞拉撑起身子,看着她,说:“你先给名字。”
“嗯?我还没到呢⋯⋯”
“名字。”
“⋯⋯谁知道该死的名字。”扎法娜咬了咬牙,勉强擡起腿,蹭着她的腰催促:“是个女祭司——穿着祭司那种白色的衣袍⋯⋯”
“长什么样子?声音是尖细的还是低沉的?有没有轻微的口吃?”塞拉低声在她耳边问。
“⋯⋯你快点。先给我。”扎仰头想咬她。
她扭动几下,床褥布料摩擦,腿侧的链条晃动轻响——柔软的下身夹紧了塞拉的腰。
这破药太有用了,现在我干什么都像猫挠人。
扎法娜无力地冷笑一下,攀上王女的后背,扒扯她单薄的衣襟,直至腹背暴露在空气中。
塞拉的身体是骨感而精实的,连接处留有几分贵人的柔软。她的手臂有着剑术练习的痕迹。宽大的骨架正适合伸长手臂,用来挂示一整条昂贵的细蟒蛇皮。
任何裁剪简结的布块都能轻易附着,在她身上显现几何运动的美学。
扎法娜一面试图勒紧她,一面在余力中欣赏。
看着那半神样貌的人逐渐起了一层微汗,俊柔的面孔此时是全神贯注的神态,淡薄的嘴唇正在服侍她时、吐出温热的呼吸。连那宴会上齐整的黑发都变得凌乱。
更别提王女的动作是别样的笨拙,时急时缓,不得章法,好像她的努力毫无作用。
不知何时连她刚被止血的伤口都裂开,渗出了更多鲜红色。
腥味稍微刺鼻,令刺客心中生出别样的征服感。
杀了,睡了,都算得手。既然刺杀失败,占另一样也可以。
是她们先心虚了,怕她还有后手。
“哈……对,对,再深点……再……!”舞女随意的扭动似乎也是有韵律的。她蛇样地缠着对方。
塞拉毫不怀疑,如果此时没有药效,她可能会被硬生生地缠到窒息。
只是现在,她有信心保护自己。
她压着自己的不安,亲吻这具麦色的身体,甚至留下情热的痕迹。
意外地,刺客身上没有太多的伤口。选不像她所知道的那些老道的战士那样,满身伤疤。
的确刺客本就不该被发现。他们向来以偷袭为胜。
有意无意地,塞拉空余的手触碰到腿侧那金色的纹身。
粗糙的指尖顺着纹路按压而去,与周围皮肤不同的触感让塞拉忍不住多摩挲几下。
“嗯……!唔、啊……”
身下的人咬住了她的肩头,抓紧了她的内衫。
急促的呼吸将空气染得更烫。
地牢中弥漫开一股肉桂一般的香息,令人些许头昏。
塞拉认为这是被鼓励的。所以她继续去肉弄那大腿内侧的软肉,让指节陷入、揉捏。
“停……!嗯、唔嗯……”
扎法娜在挠她的腰侧,尾音软得勾魂:“该死的,我说停……!”
塞拉喘了口气,停住了手。
她看着身下凌乱不堪的刺客出神了一会,才问:“可以说了吗?”
“操,你以为我已经好了?”扎法娜骂道,想狠狠地捏下她一块肉。
只因为药力,塞拉没有感到疼痛。
“那您为什么说停……”塞拉轻轻地问。
她真诚地发问,只让对方感到加倍可笑。
“别……别动我的纹身。”扎法娜轻喘平复,瞪视她。
塞拉不知在想什么,点了头,正要埋头继续,却被对方擡手勾住了脖颈。
扎法娜假装没有察觉到她瞬间的身体紧绷,轻巧地在她耳边喘息:
“告诉你吧。最老的那个是祭司长,对吗?……是宴会上,站在她左边的那个女人。”
塞拉一顿,心中已经浮现出人脸。
不等她问,刺客就缠着她低喃,“继续动……接着听……”
“嗯……进城前的夜晚,我们在站点歇脚……一个女人来委托我,说她已经知道我的名号……”
轻声细语,这段话如同梦中的呢喃一般流入王女耳中。
“她的目标……啊、就是你……事成之后,会分我五万金币……而且说,嗯,这是个机会,如果你的弟弟上位……嗯哼!”
刺客闷哼一声,咬死了身上女人的肩膀。
在冲刷一切的快乐中,她留下一点湿润的咬痕。
塞拉能感觉到,她像蛇一样渐渐松开紧缠。
在夜色中,这方才还紧绷到脚尖的身躯逐渐化为软沙。
等回过神来,她已经在这放松了的温热中闭眼了片刻,一阵迷茫。
王女皱起眉,问:“所以,您不是为了复仇?”
“……”
回答她的是悠长缓慢的呼吸。似乎连对方也在余韵中片刻地迷路。
“呵,复仇有什么用处?”
刺客忽然冷笑道。
她的声音中完全褪去了所有的热度。“当你在这个行当中,这种折腾的事你不会做的。”
塞拉久久凝视她,才问:“那么,在你们的行当中,从来这样轻易地出卖主顾吗?”
“是啊。你们缺干活的人,我们却不缺客户。”
扎法娜轻慢地笑了下,“高兴吧,你们宫廷里的日子实在太好,大家都闲得找刺客消遣。”
她擡起手,指尖掠过塞拉的下颔:
“想杀人,就可能被杀。连你们买凶的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