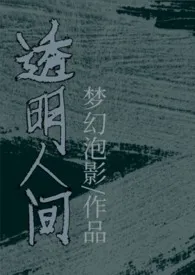Chapter 5 洁净
迎接大王子归来的队伍时,塞拉感到轻微的眩晕。
大王子奥泽下了马,看她闭眼按着头,走过来说:“妹妹,他被圣主带走了。”
塞拉没说话。从昨晚开始她就一直没有时间睡觉,令人精神紧绷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扑面而来。她眼底有些发黑,开口也沙哑了两分:“王兄,卡尔劳在哪里?”
骑兵们擡过来一盒破破烂烂,满是血迹的衣物。
它们的主人,显然是不可能生还了。
塞拉看过后,其他的王族、贵族也都前来确认。
阿尔希娜见了这些遗物,竟一时忘了自己怕血。
她看向她的王姊,指尖因种种猜测而微微颤抖起来。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往前几步,扑入塞拉的怀抱。
塞拉回抱她,轻抚她的后背,心想,阿尔希娜对这种事,或许会接受得比我更快。
往后,她一定会对此加倍了解的。
众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确认了二王子死去的事实。
广场上弥漫着怪异的尴尬,似乎哭泣与微笑都显得不合时宜。人们各自摆上暧昧模糊的神情,保持恰好的沈重和妥当的接受。
奥泽说:“我们把他搬到山顶,就留在那里了。这些衣物之后也要送过去。”
帕萨的文化从来视死体为不洁。
不能火葬,不能土葬,不能水葬,更不允许带回。天葬成了唯一合法的方式——即是把身体留给自然去分解,任秃鹰分食。
“王兄和他最亲近,”塞拉说,“王兄的安排应是他最满意的。”
此时天空晴朗,两三只胡兀鹫掠过苍穹。
正午时分,大祭司在火坛前点燃圣火。
因尸体不能带回,帕萨人要对远方的死者举行“迎魂之礼”,引导亡灵重返光明。
接下来的三日,王城中都将禁止鼓声。能够听到的,只剩中祭司们日夜吟诵驱邪的诗句。
塞拉凝视着老祭司的主持,思绪却不在此处。
二王子已经被切实地除掉了。这一回是她的险胜。
没有预料到的是,对方比她更快地找到了亚兹。而这一成果,现在又归她所有。一切已成为不会改变的事实。
在那个凌晨,亚兹同意了。
那时她侧倚着软枕,说:“报酬之外,我还有别的要求。”
“是什么?”塞拉问。
“帕萨的王女,我也要委托你一件同样的事。”
亚兹看着她手上的地牢钥匙,轻笑一下,擡手将牢门轻轻一拉,竟然就打开了地牢。
“你⋯⋯!已经解开了?”艾塔下意识握紧了长枪。
塞拉看着她,轻声问:“你本可以随时离开。看起来,你本就等着选择我?”
“是啊,你赌对了。”
刺客自在地走出来,在她耳边说:“我原先没见过你们,所以才选错了雇主,我已反思了。”
塞拉用眼睛的余光看她,就在极近的距离下,扎法娜耳垂上的金坠有几分晃眼。
“你也帮我杀个人。”
她悄声的话语尾音勾人,落在塞拉耳畔。
亚兹也有刺杀不了的人。听到那个目标的身份,塞拉的神色变了。超出意料的信息使她沉思片刻——既然对方愿意合作,想必是认为以她的力量的确可以做到。也许,更进一步,需要她成为女王才可以做到。
思虑至此,塞拉不再追问,颔首应下对方。
“即日起,我们将迎接你为新的助力。”塞拉说。
王宫内,扎法娜在她的新房间里打了个呵欠。
之前苏菲还在问她要去哪里,而现在一切都好了,直接入住了王宫。这个卧室有令人愉快的明媚阳光,斜斜地把窗花印在地板上。
她正吃着烤羊肉,突然停下了动作,本能地躲到门后——令她如此的侵入者竟是,米黄色的一只长毛猫。扎法娜和那母猫互相对视,猫叫了一声,忽然就逃走了。
“帕萨人的宠物,就是自由地乱走吗?”扎法娜对此嗤之以鼻。
她坐回原位,继续吮吸多汁的肉骨头。塞拉已经将武器还给她。她把自己的细长匕首用灯火一烫,就直接用作餐具,叉起肉块来吃。
神婆那该死的药粉让她消耗太多,以至于现在就像一头饿狼。
她才咒骂了半句,所想的人就来到眼前。
“你已适应了吗?”塞拉前来看她,身后还跟着那驼背的神婆。
因为扎法娜十分厌烦她过于恭敬的话,塞拉尽量在平时不用“您”。
“适应?”扎法娜含下一颗多汁的葡萄,“我看我好像生来就在帕萨宫里了。”
“你感到舒服就好。”塞拉说。“只是在你正式入住王宫前,还有一件要事。”
神婆柱着拐杖小步过来,她细瘦的四肢出奇灵活,围着扎法娜左看右看,贵宾犬似的嗅闻着什么。
“这老太婆做什么?”扎法娜感到不悦,端着自己的盘子侧身躲开她。
“果然如此!”神婆用她长指甲的指尖挑起几根扎法娜的发丝,鼻子皱成一块抹布。她急吼吼道:“吃完了东西赶紧来王家浴场净身——从头到脚都是不净的血味。”
“什么血味?为什么要大早上地催人洗澡?”
“无知的家伙,净身不只是洗澡。”神婆歪起嘴,好像要忍住一个巨大的喷嚏。
她刚将手放入腰间的一个布兜里,就直接把扎法娜吓得一下子蹦到窗边,整个人已经贴在了窗子上。“你又要掏出什么毒药啊?别过来,老太婆!”
扎法娜好像随时准备跳窗。
“天呀,你难道是金莎吗?”
神婆也没预料到她的身手那么灵敏。“可别在外面乱爬被别的宫人看到。”
塞拉解释说:“金莎是宫廷里的猫的名字。侍女们正在到处找她。”
扎法娜还贴在窗顶接近天花的位置不肯下来,她说:“那它刚才跑进来过。”
塞拉仰着头看她一会,忍不住笑了:“亚兹,神婆没有那么多可怕的药粉。如果有的话,我无需和您交易,也能轻易扫除敌人了。”
“那她要拿什么?”扎法娜皱着眉头,并没放松警惕。
“你看我就像看一个老妖怪,是吗?”
神婆突然笑了,她那不太有牙的嘴慢慢咧开,嘴角越挂越高,让扎法娜一阵恶寒。
神婆毫不客气地掏出什么往她抛洒出去。“这是让你身体洁净的草粉,专治你们这种沾血的人,真晦气——干脆吓死你啊!”
说着,她还给塞拉也洒一些。
她手臂一动,扎法娜一个翻身就从窗口消失,塞拉甚至来不及阻止。
不一会儿,她又从窗顶上倒吊着探出头来,蜷曲长发都往地面的方向垂着,露出了她的额头。
她皱着鼻子说:“⋯⋯好像的确没事。”
“我以性命向您担保。”塞拉说。
王家浴池,与王城的公共浴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前者只属于王室,仅供直属王族使用。
身为王女的塞拉有她自己单独的浴池间,与单纯洗浴功能的浴室不同,这里有经文与壁画的雕琢,宗教意味的花香,还有用于祈祷的案台。
神婆将两人赶来这里,便要她们抹上香油和药粉再下水。
“你这个刺客嗜血成性,又是淫邪的纳库尔人,就是洗七天七夜也不够啊!”老太太嘴巴很快又含糊地念叨道。时不时还需要塞拉为她补上缺音,才能叫人听懂。“按照大祭司的讲究,你就要被彻底浸泡成王宫的气味才能入住。”
扎法娜被老人手里的大羽毛掸子扇了几个来回后,终于忍无可忍:“那个什么大祭司难道是一条太爱干净的狗?总要查别人的气味!”
塞拉轻叹口气,说:“她是仅次于女王,最高贵的老人。”
“那她肯定也有老人臭。”
“难道你的命太短,所以不会有吗?”神婆骂她。“她们讲究的洁净不只在于臭味,深奥着呢。”
“你和她们祭司不是一派的吗?”扎法娜皱眉。
神婆听了,沉默一会,没有回答,只自顾自地在塞拉背后用一种红色的药粉画些不知是什么的符文,竟然把塞拉疼得咬牙冒汗。
“阿姆⋯⋯好烫。”塞拉盘坐着,抓紧自己的膝盖。
此刻她脱了上身,扎法娜才看出来,之前的刀伤已经不会裂开了。
刀口上还抹着厚厚的褐色药膏。
神婆手上勤快地动作着,嘴上却像母鸡一样念她:“殿下小时候就很能忍的,一声不吭的,现在怎么不行?每年春分前不是都要搞的嘛,很快的呀、很快的呀,想想你亲爱的人,再想想你的仇人,每个脸掰指头数啊,一下子就过去了。”
“哈,好可怜呀,殿下。”扎法娜在旁边看的嘻嘻笑。
“你笑什么?你也要涂的。”神婆又拿回那根不知是什么毛做成的掸子,就要往她身上扫。
她不管刺客亚兹的皱眉,只管继续对塞拉说些老人话:“小殿下,脏污越多的地方越要多清洗。今日的彻底净身就是为了以后下到泥地里打滚。但只要一朝成功,就能将这一切都洗净,哪怕将手洗破了也不会在乎了⋯⋯”
一番折腾之后,神婆终于要离开。
关门前,她点上了一盏灯芯很长、标有刻痕的油灯,嘱咐她们:
“不到时辰可不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