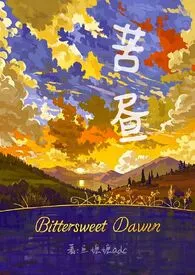腊月里的第一场雪,悄无声息地覆盖了京城的朱门绣户。
宁远侯府深处,青松翠柏皆披素缟,雪压竹枝簌簌轻响。
陈昪之独立廊下,望着漫天飞雪。
三年孝期将满,他身量愈发挺拔,一袭素色锦袍衬得身形清瘦,眉宇间少年的青涩已褪尽,沉淀为一种深潭般的沉静。
唯有细看,方能察觉他眼底掠过与年龄不符的疲惫与冷厉。
“少爷,边关来信。”
老管家踩着积雪匆匆而来,呵出的白气氤氲了眉眼间的忧色。
陈昪之接过,指尖触及那冰冷蜡封,微微一顿。他转身步入书房,方才于灯下拆阅。
信纸粗糙,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是父亲旧部赵参将的亲笔。
信中言及边境近来异动频频,突厥小股部队骚扰次数较往年冬时倍增,似有试探之意。
更令人心惊的是,朝中拨发的冬衣与粮草迟迟未足额抵达,军中已有怨言,而核查账目,竟发现几次军饷发放记录与实收数目有细微出入,手法隐秘,若非赵参将心细如发,几不可察。
信末一句:
“侯爷去后,军中旧人皆盼世子早日主持大局,恐迟则生变。”
陈昪之面色沉静如水,只袖中的手微微收紧,指节泛白。
他擡眼看向垂手侍立的老管家:
“送信的人呢?”
“按您的吩咐,从西南角门引入,身上落了层雪,老奴已让他在西厢暖阁歇下,上了热汤饭食。”
管家低声回禀,语带谨慎。
西南角门最为偏僻,直通仆役院落,平日极少启用。
“嗯。”
陈昪之颔首,不再多问。
他将信纸就着身旁的火盆点燃。
纸张蜷曲、焦黑,直至化为灰烬,仿佛从未存在过。
处理完这桩事,他敛去周身寒意,转身往栖梧苑走去。
栖梧苑内却是另一番天地。
地龙烧得正旺,暖香融融,生得檀木的醇厚香味。
陈栖梧正临窗习字,身着一件藕荷色绣缠枝梅纹的夹袄,下面是月白百褶长裙,虽仍是素色,却平添了几分鲜活气。
三年时光,当初稚嫩的小少女已悄然长开,身量抽高,有了窈窕的轮廓。
只是因着常年“抱病”,少见日光,肤色愈发白皙得近乎透明,反而更坐实了外界关于她“病弱”的传言。
听见脚步声,她擡起头,见是兄长,眉眼弯弯地唤了声“兄长”,声音清软。
“在写什幺?”
陈昪之走到她身后,俯身去看。
他的气息带着室外的清寒。
陈栖梧握着笔的手指几不可察地蜷缩了一下。
“杜工部的《秋兴》。”
她轻声道,指尖点了点宣纸上的一句,
“只是总写不好‘丛菊两开他日泪’这一句的笔意,悲怆有余,而筋骨不足。”
陈昪之未语,手掌却已复上她执笔的手背,自然而然地引着那支狼毫,重新蘸墨,落笔。
他的胸膛几乎贴着她的后背,心跳声隔着衣传来。
“笔锋需沉,藏悲怆于劲骨之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方是杜子美沉郁顿挫的真味。”
他的声音低沉。
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墨迹在宣纸上晕开,苍凉遒劲。
这三年来,兄长待她极好,近乎溺爱。
“好了。”陈昪之松开手,语气如常,“你自己再试试。”
陈栖梧依言落笔,却因心绪不宁,写出来的字竟比平日更显虚浮稚嫩。
一只修长的手伸过来,轻轻抽走了她手中的笔。
“今日心不静,不写了。”
陈昪之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他将笔搁回笔山,“陪我手谈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