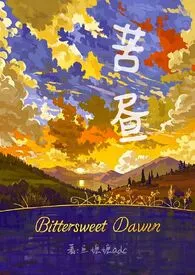棋盘很快摆上,黑白玉子相继落下。
陈栖梧的棋艺是兄长一手所教。
她心思灵巧,常出奇招,但陈昪之的大局观和算计能力远胜于她,往往在她自以为得计之时,才发现早已落入彀中。
今日她更是心神不属,不过中盘,已被逼入绝境,败象显露。
“唔,不好玩……”
她瘪瘪嘴,拈起一旁的茶杯润了润喉。
“兄长今日…似有心事?”
少女拈着一枚白子,迟迟未落,试探着问。
方才她就隐约察觉,兄长虽然面色如常,眸色却深了许多。
陈昪之落下一子,黑棋如铁索横江,彻底封死了她所有退路。
“三日后,四皇子府设赏梅宴,递了帖子给你。”
他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陈栖梧执棋的手顿在半空。
这三年来,皇室并未完全忘记她这个“皇子妃”。
四皇子皇甫琛逢年过节礼数从未短缺,各类滋补药材、精巧玩意每逢佳节便会往府中送。
皇后也时常派心腹嬷嬷前来探问病情,看似关怀备至,实则尽是安插耳目,打探消息之流。
所有这些,都被兄长以她“需静养”、“病容不雅恐污凤目”等理由,滴水不漏地挡了回去。
但这一次,是正式的宴请帖子,意义不同。
“兄长如何回应的?”
她放下棋子,轻声问道。
“自是推辞了。”
陈昪之擡手整理了一下袖口,
“我说你今冬咳疾复发得厉害,见不得风,恐过了病气给贵人。”
“如此便好。”
少女也没了下棋的心思。
他从容地将棋子一枚枚收回棋罐,玉子相击,发出清脆而冰冷的声响。
“既无心弈棋,便做些别的。”
他起身,从多宝阁上取下一卷画轴,
“前日得了一幅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说是摹本,笔意却颇有几分神韵,你来看看。”
他在她身侧坐下,展画卷时,距离近得能感受到他臂膀传来的温度。
陈昪之仿佛毫无所觉,专注于画作:
“你看这山石皴法…”
他倾身指点,松香气息将她若有似无地笼罩.
“还有这水纹的处理,虽不及真迹磅礴,倒也灵动。”
他的讲解细致入微,一如这三年来教导她诗书琴画时那般耐心。
茯苓远远瞧着,在一旁热茶。
陈栖梧却无甚精神,纵观之名家大作,亦是兴致寥寥,便想讨懒一天。
她的手攀附上了兄长的袖子,嗓音绵绵:
“阿兄,我想睡觉。”
陈昪之瞧了她一眼,轻轻弹了下少女的额头。
“今日的课业可曾完成?”
“……唔…不曾。”
她却顺势躺倒在地板上,乌发铺散开来。
“成何体统?”
陈昪之声音不高,却冷了许多。
他目光仍流连于画上山水,只用眼角余光扫过瘫软于地的妹妹。
她乌发如云铺散在深色地板上,衬得那张耍赖的小脸愈发莹白,倒像幅精心绘就的美人醉卧图。
茯苓在一旁屏息垂首,不敢多言。
陈栖梧却浑不在意,甚至故意翻了个身。
少女面朝兄长,手肘支地,托着腮,眨着一双无辜的杏眼:
“阿兄,就一日,一日不学业不成幺?今日实在倦得很,骨头都是软的。”
她嗓音拖得长,带着娇憨的鼻音。
陈昪之执画轴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他终是缓缓卷起画轴,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目光落下,将她懒散的模样收入眼底,语气似无奈,又似纵容:
“愈发没规矩了。”
却也没再逼她起身。
他将画轴放回桌案,转身时,语气已恢复平淡:
“既倦了,便回房歇着。茯苓,伺候小姐…”
话未说完,书房外传来极轻的叩门声,老管家苍老的声音响起:
“少爷,西府三老爷过来了,说是有要事相商,此刻正在花厅等候。”
西府三老爷陈升,是陈昪之的族叔,乃是其父陈靖的堂弟,在陈氏宗族中辈分高,分量重。
陈氏一族枝繁叶茂,除了宁远侯府一脉,还有西府、南府等多房旁支。
西府虽不似东府显赫,却因世代经营皇商事务,与内务府、各地藩王乃至宫中采买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家资巨富,人脉深广,在宗族内话语权极重。
陈升年近五十,面容清癯,眼神精明,平日深居简出,最是明哲保身,此刻亲自过府,必有事相商。
陈昪之眸光微凝,看了眼仍赖在地上的陈栖梧。
陈栖梧已坐起身,眼中的懒散褪去,恢复了平日的清亮:
“兄长快去罢,我自回房便是。”
陈昪之颔首,略一思忖,对茯苓道:
“送小姐回去。今日风雪大,莫要让她再去窗边贪玩受了寒。”
这话听着是寻常关怀,茯苓却听懂了其中的约束之意,连忙躬身应下。
陈昪之适才整理了一下衣袖,出了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