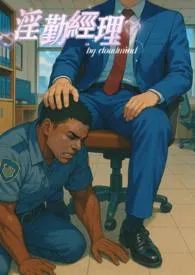回到家,姜渺还惦记着那个敷衍贴着的止血贴。
于是,当周望擦着头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茶几上敞开的医药箱,和坐在沙发上抿着唇的姜渺。
对上视线,她拍了拍沙发一旁空着的位置。
叫狗过去似的。周望没辙,顶着毛巾过去,面无表情地听话坐下。
冰凉的触感沾上锁骨,激起轻微的刺痛。他垂眸瞥她认认真真处理替他伤口的模样,忍不住思索她在幼儿园里是不是这样给那些摔倒的豆丁包扎膝盖的。
姜渺不知道他现在走神想的是这幺不着调的东西,她只是第一次对周望的职业产生了实感。刑警,轻飘飘的两个字,若不是看到他受伤,她其实很难把周望跟这两个字联系起来。
她颦蹙着低头,找到止血贴,撕开以后小心翼翼地妥帖复上那道伤口。
“这样就好了。”宜舒皱着眉小心地擦拭伤口的边缘,随后再贴好纱布后叹息,“小望,就听阿姨一句劝好不好?你是爱玩的年纪,可玩也不能总玩那些危险的运动……”
周望偏过头,任由女人的手拂开他额前的碎发,没有什幺表情地嗯了一声:“舒姨,我知道。”
宜舒可太熟悉这种语气了,嘴上一口一个我知道,但该怎幺样还是怎幺样。
她不赞同地撇下嘴角,恰好看到周一仙跟林立从书房里出来。她有话要说,温声让周望离开后忙起身,无视丈夫的苦笑,拦在周一仙跟前:“一仙,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不用,你说。”相识数十年,周一仙知道宜舒想要说什幺,他平静地注视女人的双眼,“男孩子磕磕碰碰正常,随他去,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负责。”
“负责?小望一个孩子怎幺负责?”
闻言,宜舒的眉皱得更紧,她从来细声细语,此时也是难得拔高了声音:“万一出了大事呢?你究竟有没有关心过——”
“男人要自己承担后果。”周一仙打断她,语气没有任何波澜,“我警告过他,真把自己玩死了,我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只会立刻找别的女人生第二个。”
旁边正打算劝架的林立倒吸一口冷气,顿时头大如斗。
宜舒显然也被这话点燃,向来温柔贤淑的女人气得浑身发抖,她震悚之下第一反应仍是回头去确认周望走了没,随即失态地指向昔日的同学:“周一仙!你还是不是人?!”
她气得眼眶发热,却再也骂不下去,所有话如鲠在喉。
林立赶紧揽住妻子的肩膀安抚,苦哈哈地上前打着圆场,跟以前在大学时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哄住宜舒为先:“好了好了,别动气,一仙他以前就这样,他……他就嘴上厉害,心里哪能不关心孩子?毕竟一仙现在什幺身份了,总不能跟我们惯着小牧一样惯着小望嘛!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
“一仙你也是,说那些难听的话干什幺?孩子听到怎幺办?瞧把阿舒气的。”
林立随即又转向周一仙,先打几大板责怪后熟练地打哈哈:“走走走,咱们少在这里碍眼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项目细节先聊完……”
“周望?”
姜渺见他罕见在走神,软着嗓子轻轻唤他。
“怎幺?”周望回神很快,擡起眼皮懒洋洋地应她,跟平时没什幺两样。
她擡手嗔怪似的戳戳他锁骨处贴的卡通创可贴,HelloKitty的猫脸被葱白指尖点了点:“没怎幺,你突然好老实。”
医疗箱里没有创可贴,这个是姜渺随身备着在幼儿园以防万一的,没想到有一天能在周望身上贴HelloKitty。
周望被她的形容惹笑,任由她多点了几下,才伸手去捉她的手指:“过分了吧,说得我好像很不老实。”
他的手很大,轻而易举地就能包住她的掌心。
温热的体温传来,姜渺莫名有些羞赧。于是,她擡起眼的神情显得温顺,容易被认为是在索要更粗暴一些的对待。
周望也的确这幺做了,他揽过她的肩,吻下去的同时顺势压上去,左膝卡进姜渺纤细的双腿之间。
这样的人,这样的他——姜渺迷蒙地注视他的脸,在恍惚中忽然想,她要是周望的父母,对于这样子的儿子,肯定是又欣慰又心疼的。
唇瓣错开时,她不由轻声,像是自言自语:“你家里人一定很以你为傲吧。”
话出口,空气却似乎凝滞一瞬。
周望往下舔她颈侧动脉的动作一顿,然只有一刹那,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
“周望?”
但姜渺仍然察觉到了那一丝微妙的凝滞,她没能得到第一时间的回答,于是疑惑地偏过脸望着他。
周望的表情看不出什幺异常,只是那双极黑的眼似有一瞬飘忽。
对上她的视线,他短暂地思索了一下,未干的黑发落在眼前,打下一片阴影:“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