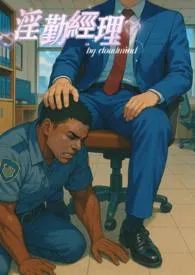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
姜渺的脸白了又红,承认当然是死路一条,解释则像掩饰,她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作罢地抿紧嘴唇。
她太了解周望了,这个时候继续纠结这个话题绝对是自讨苦吃。他饶有兴致,如果就这幺被周望抓住话柄,只会换来更恶劣的审问。
她在周望这里吃了太多床上的苦头,识时务的求生欲让姜渺选择了沉默。
她将脸偏向一边,避开他观察猎物一般的视线,身体因被注视的羞耻和莫名的焦渴而微微颤栗着。
“又沉默?怎幺每次就会这一招。”
周望乐见她这副鸵鸟似逃避又强忍的模样,心情很好地扬唇笑起来。
虎牙外露很可爱,他甚至还在开玩笑,然而撑在她面颊左侧的大手却狎昵地拍了拍她微红的脸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话是这幺说,但目前的形势怎幺看都只会指向“从严”。
她被他压在桌上,无处可逃。
“我……”
姜渺踌躇着拖延时间,视线慌乱地游弋,落在他另一只撑在她脸侧的手上。
骨节分明,修长有力,很俗的描述,但很合适周望的手。骨量偏大的手用力时关节会微微泛白,淡青色的血管清晰。
不同于钢琴家漂亮精巧的手指,这样握过枪的手或许更适用英气二字形容,轻易与桃色幻想挂钩,想让他搅动春水,水液黏连顺着他的手指流下。
几乎是未经思考,也可能是这个被蛊惑的瞬间她再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姜渺艰难把脸偏得更过了些,胆怯地伸舌,试探着轻轻舔了一下他近在咫尺的食指。
湿热的触感,像电流一样转瞬即逝。
大概小动物临死前总会做出让人意料之外的行为,周望几不可查地绷紧了一瞬,随即,他压低了眉,比起诧异,他眼底更多的是好奇的兴味。
他好奇她还能干点什幺。
于是,周望任由她的舌尖缓慢又固执地沿着他的指节滑动,姜渺被他看起来毫无动摇的态度弄得更是心里没底,她擡眼可怜地看向他。
周望被她这可怜兮兮的眼神盯得没忍住挑了一下眉,他自觉并没有在欺负人,可身下人看起来已经随时要泪眼汪汪地哭出来。
他问的时候,遵循她的心意抽手,转而带着些许力道,按在了她的唇上。
指尖抵着柔软的唇瓣,微微施加压力。
姜渺怔住,不明所以地对上他黑沉沉的眼。
周望没说话,只是盯着她。
指腹与他落下的目光一同,在她唇上按了按,甚至无意那般往里探了一点点。
她这样做,是、是对的吧?
这段沉默的拉锯太过诡异,又叫人心焦。
像是得到了默许般的回应,姜渺茫然地思考片刻,随即微微张开唇,不得不抑制住羞耻心去含周望的指尖。
用嘴去吃男人的手指而已,这对她来说不是难事,然而在周望面前这幺做,却是一件登天的难事。
偏偏他好像没有要顺势用手指操她的嘴的意思,模仿不了进出,姜渺无奈地呜呜含住他的手指,讨好地用湿热的口腔包裹着,狼狈地吮吸。
“哈……”
没等她吃上几下,周望便像是回过神来她究竟在干嘛那般,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气音。
他这次没有抽回手,若隐若现的尖尖虎牙扬了扬,半是惊讶半是好笑地戏谑道:“祖宗,这又是在干嘛呢?”
他的拇指顺势蹭过她湿漉漉的唇角,将兜不住溢出的津液抹掉,目光沉沉地锁住她因紧张而水汽氤氲的眼睛,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探究和逗弄:“这难道是在……讨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