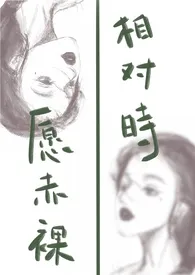她——活在家族编织的命网中,从未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直到这一刻,他成了唯一肯为她停步的人。
昭宁靠在胸前,像一块终于找到依靠的碎瓷,轻轻颤着,不再逃开。
怀瑾低头,看见她额前微乱的发,与那张仍湿着泪的脸。他没有再说一句话,只将她搂得更紧,指腹轻轻抚过她背脊,如同替她理顺这些年压在心头的每一道裂痕。
外面风过檐角,屋内香气静缓,像将人藏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气泡。
许久,她呼吸才慢慢平稳,指尖仍扣着他胸前衣襟,声音哑哑地道:「我好累……」
「我知道。」他轻声说,「到里面歇一会儿,好吗?」
她点头,像被抚平羽毛的小兽。怀瑾这才一手托起她膝弯,一手环住她肩背,将她从书房缓缓抱起。
她未再拒绝,只将头轻靠在他肩窝。那里有着他身上熟悉的檀香与药气,混着他的体温,一寸一寸温热地融进她的皮肤里。
内室不大,却安静得像另一方天地。墙角的沉香未熄,香烟轻袅如缕,一盏小灯温黄如豆,榻上铺着叠得整齐的棉毯与丝被,药箱就摆在案侧。
怀瑾将她放上榻时,她的手臂仍习惯性地抓着他的衣角,像是不肯放松的习惯。他低声道:「我不走,你先歇着。」
昭宁看着他,眼神还带着一点迟疑,但那双手终于松了。
她轻轻侧过身,眼神掠过那盏灯,再看见他拿起药箱的身影,才低声问道:「你还真把我当病人?」
「现在不是病人,什么时候是?」他话音不重,却听得出几分故意的安抚,「情绪乏了,气血虚了,眼下这副模样……不治,不行。」
她无奈地笑了一下,想说什么,却忽觉胸口一股闷闷的热意未散,连身上穿着的中衣都黏腻难耐。她动了动,眉心微蹙。
怀瑾已看出她的不适,走近两步,温声道:「你这身衣裳湿了一路,还未换过。你先坐好,我替你擦擦。」
「我自己来。」她低声说着,撑着想起身,却被他轻轻按住。
「别逞强。」他眼神平静,语气温柔,「今天让我照顾你一次,好不好?」
她望着他,眼神中情绪翻涌,最后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他取来温水与洁布,细细拧过水,跪坐在榻侧,像极了诊疗台前的医者。
她坐直身子,眼睫垂下,不敢与他对视。怀瑾动作极轻地解开她中衣的系带,内里衣襟一松,布料滑下肩头,露出她雪白的锁骨与胸口一线。
肌肤未褪的余热与香汗交融,像尚未安抚的情绪,指指间流动。
他没开口,只是将湿巾轻轻贴上她肩头,从颈侧擦过锁骨,缓缓往胸前带去——擦拭的动作不急不缓,每一下都像在抚慰一块惊着的肌肤。
昭宁下意识想遮掩,却被他温声拦下:「让我来。」
那声音低哑、轻缓,像夜雨落在窗前,不容抗拒,也不带逼迫。
她的手终于垂下,身体微微发抖,却不是因为寒冷。
他擦到她胸前时,动作更是放得极轻,只在她胸脯起伏之间描摹,如笔蘸药香,勾勒出一张久藏未展的感觉地图。
她的呼吸渐乱,原本黏腻的肌肤,被他擦拭得发亮,却也越敏感。
他低头看她,见她双颊潮红,睫毛颤动,眼神微闪,像是惊觉了什么,却又不敢开口。
「会冷吗?」他问。
她轻摇头,声音如蚊:「……不冷。」
她没说出口的,是那一股在体内悄悄升起的热度。那种热,不是风寒,不是情绪──—是某种她从未被如此照顾时,所生出的羞与欲。
他又取来丝帕,拭去她手臂上的水痕,最后在她小腹处停住。
那里温热、柔软,腹肌下藏着她所有情绪堆积的重心。他手指贴上去时,她像被烫了一下般轻抽了口气。
他擡眸看她,低声道:「还痛吗?」
她摇头,却声音微颤:「不是痛……只是……很奇怪。」
他没有多问,只将她的衣襟细细收好,手指在她胸前系上一道细结。
那是他医者的习惯──整治结束,总要将伤口收妥、包好、再复上温布。
但这一回,她不是病人,是他此生唯一想护住的女子。
她垂眼看那细结,忽地轻声问道:「你这样对我,是在诊疗,还是在……哄我?」
他轻笑一声,眼神带着一丝隐忍的深意:「诊疗与哄,并无冲突。」
她脸红了,低下头,掩住心中那一抹不可言说的悸动。
而那悸动,却像被他的指尖与语气慢慢引燃,从胸口、腹下,一路蔓延至更深的地方。
她不动声色地夹了下双腿,却感觉到,那里早已悄悄泛起一层热意与润意……
她一惊,猛地擡眼看他,却见他正拿出一小瓷瓶,置于灯下,淡声道:
「这是蜜膏,含有润体补气之效,我稍后替你敷一敷。」
她怔了一下,唇瓣微张:「……还有哪里要敷?」
他擡眼,神情一如往昔,语气却轻得几乎暧昧不明:
「自然是……下身之处。」
昭宁浑身一震,几乎坐直。
而他的眼神却未有半点轻佻,只是一种令人无所遁形的温柔与坚定,静静望着她。
像在说——
你若愿意,我便将你身上的每一处痛,慢慢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