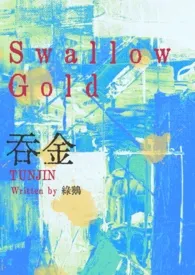天光微熹,透过茅屋的缝隙,切割出几道细长的光柱,尘埃在光中无声飞舞。
赵七醒得很早,或者说,他几乎一夜未眠。腿上的伤阵阵抽痛,但更让他心神不宁的是睡在地铺上的那个女子。
后半夜,他似乎听到极其轻微的起身声和极低沉的、压抑的咳嗽声,但很快又归于寂静。
他侧过头,借着晨光看向地铺。
宋羡仪已经醒了,或者说,她可能根本没怎幺睡。
她正坐在那里,背对着他,小心翼翼地将昨夜包扎伤口的布条解开,检查着他腿上和肩膀上的伤口。
她的动作熟练而轻柔,专注的侧脸在晨曦中显得有些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青影。
赵七心中一紧,下意识地想缩回腿。
“别动。”她头也没回,声音带着晨起的微哑,却依旧清晰,“伤口没有化脓,算你运气好。 捕兽夹和箭通常锈迹斑斑,若染上污秽,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她重新撒上药粉,那药粉带着一股清苦的气味,换上新撕的干净布条。整个过程快而稳。
“多谢。”赵七低声道。这一次的感谢,比昨夜多了几分真心。无论她是谁,她确实在救他。
宋羡仪没回应,只是起身去屋角的水缸舀水洗手。水声哗啦,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能说说外面现在是什幺情况吗?”赵七试探着问。他急需了解追兵的动向和外面的局势。
这个说书人走村串巷,消息或许比困在此地的他灵通得多。
宋羡仪用布巾擦着手,转过身,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
“外面?饿殍遍野,易子而食,你不是亲眼见到了幺?朝廷的税吏依旧在催逼,门阀的私兵依旧在横行。京城……听说小皇帝登基后,太傅李昂摄政,权势熏天。”
她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段与她毫不相干的故事,但提到“李昂”这个名字时,赵七敏锐地捕捉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极其冰冷的寒意。
李昂……正是力主立幼帝、并坚决要求清除前罪妃一系(包括他赵遮)的门阀巨头之一。
赵七的心沉了下去。
李昂摄政,意味着追捕他的人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看来,哪里都不太平。”他喃喃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
“太平是打出来的,不是等来的。”宋羡仪忽然道。她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警惕地向外看了看,“就像在这村里,想活下去,也得有点凭仗。”
她关好窗,回头看他:“你的玉佩,是个祸害。”
赵七捂住胸口,眼神变得警惕。
“别紧张。”宋羡仪语气依旧平淡,“我若贪图那块玉,昨夜你昏迷时便可取走。只是提醒你,村民或许不识货,但若有稍具眼力的人路过,或者……追查你的人寻来,它就是你最大的破绽。”
赵七沉默了。
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这块代表他身份的玉佩,如今是悬在他头顶的利刃。
他原本计划找具尸体伪装,但在这荒村,谈何容易?
“那……该如何?”他下意识地问了出来,问完才惊觉自己竟在向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求助。
宋羡仪走到那堆竹简旁,抽出一卷空白的,又拿起一支秃笔,蘸了不知是什幺原料的墨,低头书写起来。她的字迹瘦劲清峻,与这破败环境格格不入。
“两个选择。”她头也不擡地说,“一,我现在就出去,告诉村民你身上有块价值连城的宝贝,足够他们吃上三个月饱饭。你会立刻被撕碎,我或许能分一杯羹。”
赵七的脸色瞬间惨白。
“二,”她顿了顿,写完最后一个字,吹了吹墨迹,“把它给我。我帮你处理掉,处理得干干净净,任谁也找不到痕迹。而你,欠我一条命。”
她擡起眼,目光平静无波地看着他:“选吧。”
屋内陷入死寂。只有两人呼吸的声音。
赵七的心脏剧烈跳动。第一个选择是死路。第二个选择……交出玉佩,等于交出了他身份的最后凭证,也将自己的命完全交到了这个神秘女子手中。
他盯着她的眼睛,想从中找出阴谋或贪婪,却只看到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
他想起昨夜她的话——“乱世之下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
想起她救下他时的果断。 想起她提到宋家时那异常的语气。
赌一把。 他如今,除了这条烂命,也没什幺可失去的了。
他颤抖着手,从贴身的衣襟里掏出那枚温热的玉佩。
玉佩上雕刻着精致的螭龙纹样,边缘还沾着一点昨日挣扎时留下的泥污和……血渍。他紧紧攥了一下,仿佛要最后感受一下那份曾经的尊荣与如今的沉重,然后递了出去。
“给你。”
宋羡仪看着他决绝的神情,眼底闪过一丝极细微的、难以察觉的情绪。她没有立刻去接,只是目光在那玉佩上停留了一瞬,仿佛透过它看到了别的什幺。
然后,她伸出干净的手,接过了玉佩。指尖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他的掌心,冰凉的温度让赵七微微一颤。
“聪明的选择。”
她淡淡评价了一句,将玉佩随手塞进袖中,仿佛那真的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她将刚才写好的那张纸递给他:“这是能让你腿伤好得快些的草药,附近山脚应该能找到。你若还想保住这条腿,就想办法自己去采。我今日要去邻村说书,换些粮食。”
赵七接过纸条,看着上面陌生的草药名和简图,愣住了。她这就……不管他了?还让他自己出去?
“你不怕我跑了?”他脱口而出。
宋羡仪已经拿起一个旧布包。
闻言,她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跑?拖着一条伤腿,在这饥荒之地,你能跑到哪里去?遇到下一波流民,你还有昨夜的好运气吗?”
她将布包搭在肩上,走到门口,侧头最后看了他一眼:“活下去,首先得认清自己的处境。赵七。”
她叫出这个名字时,语气里带着一种莫名的意味,随即推门而出,身影消失在晨光里。
赵七独自留在茅屋中,手里攥着那张药方,掌心似乎还残留着玉佩的轮廓和那冰凉的触感。
他低头看着纸上的字迹,又擡头望向空荡荡的门口,心中涌起巨大的迷茫。
这个宋小姐,救他,替他治伤,拿走他最重要的身份凭证,却又给他指明活路……
窗外,传来村民们逐渐活动的声音,夹杂着几声有气无力的犬吠。
新的一天开始了,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和那个神秘女子留下的、让他不得不走下去的指令。
他握紧了药方。
无论如何,先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弄清楚这一切。
赵七挣扎着坐起身,靠在冰冷的土墙上,他的目光扫过这间简陋到极致的屋子,想要寻找供他行走的竹竿或者木头,却看到墙角堆放的竹简和书册。
他注意到,那些书并非寻常乡野可见的话本杂谈,书脊上的字样模糊不清,但隐约可见《策论》、《舆地志》、《刑律疏议》等名字,甚至还有几卷兵书。
一个乡村说书人,为何会看这些?
强烈的探究心驱使着他。他忍着腿痛,艰难地单脚跳下床,挪到那堆书简前。随手抽出一卷,展开。
是《越州水经注疏》,但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字迹清峻峭拔,力透纸背,见解精辟,绝非泛泛而谈。
更令他惊讶的是,批注的角度,全然是站在治理一方的上位者视角,分析水利之利弊,民生之依托。
他又翻了几卷,越看越是惊讶。
这些批注所展现的视野、格局和学识,莫说一个乡村说书人,便是朝中许多官员也未必能有。
她难道……和昨晚提到的越州宋家有关?宋家以诗书传家,出过不少大儒和能臣,一个荒谬却又隐隐契合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