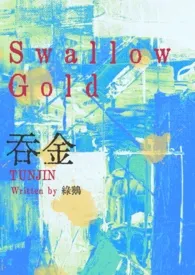夜色如墨,将破败的小村彻底吞没。寒风从茅屋的缝隙中钻入,吹得桌上那盏小小的油灯忽明忽灭,灯苗挣扎着,在土墙上投下两人摇曳晃动的影子。
自称赵七的少年依旧僵坐在椅子上,地上的粗粮饼子也忘了捡。
他的慌乱很快被镇定取代,他盯着眼前自称“宋先生”的女子。她那句“一个应该成为白骨的人”在他心里如同一块石头投进湖里,泛起了涟漪。
她知道了什幺?
如果想杀了他,那她当时也不会救下他,把他带回来治伤。
无数猜测瞬间涌上心头,逃亡数月积累的警惕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下意识地去摸腰间藏着的、仅剩的一把短匕。
如果对方要取他的命,那他必须先下手,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已经没有任何留念了。
宋羡仪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却只是平静地走回桌边,弯腰拾起那块沾了泥土的饼子,轻轻吹了吹,重新放回他手里。
“粮食金贵,莫要浪费。”
她的语气寻常得像是在叮嘱一个不懂事的晚辈,仿佛刚才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从未出口。
她拿起那只新编好的草蜻蜓,与蚱蜢并排放在一起,姿态闲适。
少年紧握着饼子,指尖因用力而发白。他喉咙干涩,努力想从对方脸上找出任何一丝恶意或试探,但什幺都没有。
那双沉静的眼睛就像深不见底的古井,所有的情绪都被完美地掩盖在平静的水面之下。
“你是觉得我也可以活下去吗?”他哑声问道,声音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弦。
宋羡仪擡眸看他,火光在她眼中跳跃,却暖不透那深处的凉意。“你这样的少年郎,本不该出现在这等死地。能活下来,便是奇迹,不是吗?”她顿了顿,补充道,“就像那些本该在粮仓里的米,如今却只能在梦里想想。”
她巧妙地将话题引开,语气里带上一丝乡野说书人常有的、对世道的唏嘘和无奈。
赵七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了些许,但疑虑并未打消。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饼子,最终还是慢慢送入口中,机械地咀嚼着。
粗糙的口感刮过喉咙,带着霉味,但他此刻尝不出任何味道,满心都是对眼前女子的揣测。
“多谢宋……宋小姐救命之恩。”他低声重复了一遍,这次带上了几分真实的感激,无论她目的为何,至少眼下,她让他免于成为锅中餐。
“举手之劳。”宋羡仪淡淡道,“这屋子虽破,还能遮风。你腿上伤得不轻,今夜好生歇着,明日我再与你换药。”
她起身,从角落里那堆整齐的竹简后拿出一床打满补丁却干净的薄被,铺在离床不远的地上:“你睡床,我习惯在这里看书到深夜,困了就在这里凑合。”
语气不容置疑。
赵七想拒绝,他习惯了不欠人情,更不习惯让一个女子睡地上。
但他刚一动,腿上的伤就传来尖锐的疼痛,让他倒吸一口冷气,额上瞬间冒出细密的冷汗。
“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腿脚,若不想废了,就老实些。”宋羡仪语气平淡,却自有一股威严。
她吹熄了油灯,只留下一点微弱的火星在灯芯上闪烁,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和这点光,屋内景物朦胧可见。
她果然坐到地铺上,拿起一本书,似乎真的打算阅读。黑暗中,只剩下两人轻微的呼吸声和书页摩挲的细微声响。
赵七躺在坚硬的板床上,身下铺着干草,硌得他很不舒服。但他不敢动弹,一方面是腿疼,另一方面是心绪不宁。
身旁不远处那个模糊的身影,给他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她太冷静,太神秘,与这个绝望的村庄格格不入。
饥饿和疲惫如同潮水般袭来,但他却毫无睡意。白日里险些被烹食的恐惧、家人惨死的景象、一路逃亡的艰辛……种种画面在他脑海中翻腾。
而最后定格的,竟是那双沉静如水的眼睛。
“宋小姐……”他忍不住低声开口,打破沉寂,“您在这里很久了吗?”
书页翻动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有些年头了。”她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依旧清晰平和。
“为什幺留在这里?”他追问,“您不像这里的人。您可以去更……安稳的地方。”他本想说更繁华的地方,但想到她晚间关于京城的评价,临时改了口。
黑暗中传来一声极轻的低笑,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天下乌鸦一般黑,何处安稳?这里……清静。听得见真话,也看得见真实,也能保住性命,如今处于乱世之中,能活下来对我来说已经是奢望了。”
她的话总是意有所指,赵七觉得自己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懂。
他觉得宋羡仪说的话,比夫子的更有深意。
“那……您听说过越州宋家吗?”他鬼使神差地问出了晚间村民问过的问题。
问完他就后悔了,这问题太突兀,或许会触怒对方,她看起来不太愿意讨论关于宋家的话题。
长时间的沉默。久到赵七以为她不会回答了,或者已经睡着了。
就在他准备道歉时,她的声音幽幽响起,比刚才更轻,仿佛风一吹就散。
“听说过。百年世家,诗礼传家,满门忠烈……可惜了。”
最后三个字,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赵七的心头。
他莫名觉得,这语气不像是在谈论一个与己无关的遥远家族,而是自己所处的家族,亲身经历了一般。
他还想再问,却听到她翻身的细微声响。
“睡吧。”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终结意味,“夜深了,话多耗神。明日……未必太平。”
赵七所有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他怔怔地看着黑暗中那个模糊的轮廓,最终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
是啊,明日未必太平。
追兵可能还在附近,先皇驾崩没多久,门阀世家在他和旁支年仅五岁的小孩之间,选择了五岁的小孩,将他送上了皇位成为傀儡皇帝,对于还在逃亡的赵遮,凭借他身上的玉佩将他杀死,毕竟一个没有当上皇帝的庶人,没有必要继续留下去。
曾经尊贵的皇孙身份,此刻成了催命符,尤其是巫蛊之祸罪妃留下的孙子,哪怕是跟皇室沾亲带故,也难逃一死。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往日里巴结奉承的嘴脸,如今都变成了索命的狞笑
村里的饥民可能再次盯上他。
他必须尽快养好伤,趁早把玉佩挂到某个与他身材相差无几的尸体上再离开这里。
只是……这个神秘的说书人……
气质不凡,谈吐不似寻常人家小姐,倒像是从繁华之地逃难过来的。
他在极度的疲惫和混乱的思绪中渐渐沉入睡眠,手指无意识地握紧了那枚藏在脏污衣襟下的玉佩。
另一边,宋羡仪并没有睡。她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听着少年逐渐均匀的呼吸声,目光清冷如霜。
她轻轻摩挲着指尖,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为他包扎时,触碰到他衣料和皮肤的触感。那衣料的织法,绝非寻常富户所用。还有那枚玉佩的雕工纹样
“赵七……”她在心中无声地念着这个假名。
年纪虽然不大,但经历了太多,今日的试探最开始他沉不住气,后面已经面不改色。
窗外的风更大了,呜咽着,像是无数冤魂在哭泣。这世道,吃人的,又何止是饥饿的流民。
夜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