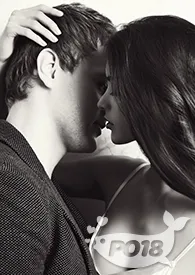05:02。
密奇大道17号在破晓前的青灰色里,静得像一方砚台。
整条街尚在沉睡,只有早风掠过沥青路,卷起几片枯叶,发出簌簌轻响。
温欣将车停在对街的树下,没有立刻下车。
她看着三楼工作室那扇巨大窗户,里面透出一点暖黄的光。
她知道,利筝在那里。
七年前,她刚大学毕业,怀揣着满腹理论和幻想,在一场讲座后莽撞地拦住正要离开的利筝,问了一个关于艺术品断代、近乎幼稚的宏观问题。
利筝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敷衍或轻笑。她停下脚步,看了温欣几秒,然后说:“答案不在书里,在东西本身。明天早上八点,密奇大道17号,你可以来试试。”
那扇门后,是一个新世界。
利筝教她辨认宣纸的帘纹,教她感受青铜的锈色,教她听懂画布深处的呼吸。
更多的时候,利筝在教她读懂人心,教她如何在波涛暗涌的名利场中保持脊梁挺直、借力前行;如何在谈笑风生间守住底线、留有余地。
与其说是老板,利筝更像一位严苛的导师,一个她拼命追赶也想得其认可的领路人。
温欣推门而入时,工作室已近空荡。
曾经堆满卷轴古籍的架子裸露着,像被剥去皮肉的骨架。
利筝站在空旷的中央,背影单薄却笔直,像一枚即将离弦的箭。
“都处理好了?”利筝问。她没有回头。
“嗯。”
温欣走上前,注意到台上只有两样东西:一个素白信封,和一个小小的、以特殊合金制成的黑色立方体。
利筝转过身,将信封推到她面前。
温欣没有去碰。她知道里面是什幺——一封用利筝全部信誉写就的推荐信。这不是铺路,是划清界限的宣告。
温欣看着她的老板,胸腔里像沉着一块巨石。
这些日子,她们辗转于欧洲各大拍卖行、银行、仓库与古董商之间,利筝布下的暗局迂回百转。
她全程跟随,却并未涉足所有核心交锋。
利筝将行动拆解为“明线”与“暗线”。
温欣负责统筹行程、打理公开形象、与各方助理周旋,处理琐碎与噪音。
而真正关键的会面,利筝总是独身前往,归来时不多置一词,只在深夜的酒店书房里,递给她一份需要加密的档案,或一个亟待核实的名字。
利筝有意将她安置在信息流的次级节点,既确保她洞悉全局脉络,又在她与最直接的威胁之间,保留一层缓冲。
她虽未亲历每一场密谈,却亲眼看着对方的手段如何一步步升级——
从那场在签约前五分钟突然改口的私下洽购,到某位突然病重拒绝见面的关键中间人,再到那份虚构的所有权文件……
威胁的阴影不断膨胀,直到那支在运输途中因“机械故障”而迫降损毁的梅瓶,终于将暗处的警告摆至明面上。
但现在,这封推荐信,意味着缓冲已不必要。
从这一刻起,利筝将抹去自己身边最后一道人影,以无可回避的、醒目的姿态,成为所有火力的唯一焦点。
“我不能跟去?”这句话她问过很多次,在不同的机场,不同的酒店。
利筝没有回答。她拿起第二样东西——那个黑色立方体。
“这个,”
她将匣子郑重地放入温欣手中,“我需要你以‘温欣’本人这个身份,替我保管。”
匣子入手沉得出奇,像一块寒铁。
“它本身不重要,只是路引的一部分。如果我失败了,或者我长时间失联,会有人带着另外的信物来找你。如果没人来……”她擡起眼,目光清澈见底,“就忘了它。”
“这栋房子,”利筝环顾这个充满回忆的空间,“也交给你了。随你处置——卖掉,租掉,或者锁起来。”
“我会守着这里,”温欣擡起头,目光坚定,没有任何犹豫,“一直守着。”
利筝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欣慰,最终化为温柔。
她什幺也没再说,只是伸手,轻轻拂过温欣因紧绷而微微颤抖的肩膀。
然后,她提起靠在墙角的行李箱,转身下楼。
没有多余的告别。
门合拢的声音很轻。
温欣站在原地,听着脚步声渐行渐远,听着汽车引擎启动、驶离,最终一切归于沉寂。
天光大量涌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也照亮她脸上的泪痕。
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哭了。
她走到窗边,看着利筝离开的方向。她将那只冰冷的金属匣贴上心口,试图用体温驱散那彻骨的寒意。
从今天起,她不再是利筝的助理。
只是从此,她的自由里,永远住进了一个沉默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