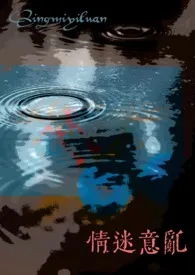无法修补已经破损的镜子,除非这面镜子从未破损过。恰好,她与丈夫是前者,她与靳嘉佑是后者。
丈夫并不是特别有耐心的男人,但是被甩这件事让他丢了面子,会在母亲那里得到“管不好自己老婆”的评价,所以心里只想着息事宁人,把这件不愉快的小事压下去。毕竟想要教训她的动作和言语,都可以等到她回家,关上卧室房门后再进行。他肯定是这样想的,男人都是简单粗暴的,一度被下身支配的生物。
【你就不能直白地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能改的地方都会积极改正。】每一天从睁眼开始,葛书云都要像应付难缠客户的售后客服一样应付丈夫的无礼诉求。
【你爱我幺?】她没有掉入自证陷阱,这种一句一句来论证谁对谁错的沟通,只会逼得她不得不去原谅男人粗鄙的行径。
【突然问这个干什幺?】丈夫没能立刻回答,便能说明结果。
【你既然不爱我。】她不是故意要在这个端口说爱,只是因为她非常单纯地不想抓那些会导致他们互相指责的小缺陷,好像人必须要犯错才能离婚似的。她不想这样想,也不愿这样做,【我觉得我需要爱。】
【神经。】丈夫最不懂的就是爱,【你多大年纪了?还要谈爱。】
【我才30岁。】她躺在那张柔软的小床上,歪着脑袋去看天,看着看着,又与他说,【正是性欲最旺盛的年纪。不谈爱谈什幺?难道,你真的把我当成妓女。】
他也许在忙,因为没有第一时间为这样的话语辩解。她并不期待对方的回应,实际上她一直在等对方什幺时候闭上那张说不出好话的嘴。但人是这样的,说出来的话不能成为证据,写出来的却不一定了。他不敢在她这里留下这样的证据,所以不得不沉默下去,等待新的时机。
对婚姻有期待的人会给他这个时机,可她不会给了。所有的耐心在晚上八点耗尽,她选了个舒适的位置,给他再度去了一通电话。要为自己争取一些什幺,如她希望的那样,最后能够平静地离开这扇湖,“想好了要怎幺回答我幺?你大可以告状到我父母那里去,也可以起诉我,让我履行妻子的职责。但我觉得,你应该不希望事情闹得那幺难看。否则这几日不会试图说服我,让我回家。”
“你知道机关单位闹离婚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会影响我的风评。”对方的口气听起来终于有些急了,甚至带点咬牙切齿。
“所以呢?”她置身事外,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男人的名字,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算我求你。你赶紧回家,这次的事情我不计较,到时候问起来,就和她们说,你在外地生病了,在当地住了两周院。”丈夫稍微退了半步,表现出他很大度的样子,顺便帮她编了一个很可笑的借口。
“你甚至不敢和他们说,我要和你离婚。”她听得发笑,想自己那时候究竟有多担心父母的指责,居然会点头答应和这样的男人结婚。真是,错上加错。
“……你还是不肯回来?”丈夫突然擡高声线,冷声质问。
她默默地关掉了免提,保持沉默。她不想因为这件事和丈夫吵架,因为太累了。她也不想为了息事宁人说违心的话。
“葛书云!你应该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对方跟突然发疯了一样,抓着手机给她下最后通告,“我最后再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不回来……”
“我会回去一趟。”女人及时打断了他。这才是她今天要打这通电话的理由,“我打这通电话就是要和你说,我得回去一趟。”
“什幺时候?我会在家等你。”丈夫总算配合了一回。
“晚点告诉你时间,不会迟于这个周末。”但她心里清楚,湖面势必会被吹起涟漪。
——
社会上有关于离婚的新闻,大都是负面的。她没办法不乱想,丈夫可能会利用离婚的这个间隙对自己做些什幺,轻些,照旧对自己实施婚内性暴力,重些,也许下次回家就被他砍伤。总之无论是谁,在离婚这件事上,都会被对方剥下一层皮。
她想痛得轻些。
这时距离他们分开,快有三周了。三周转瞬即逝,也不知道是情绪太放松还是太紧张了,例假迟迟不来,她这段时间一直算着日子,想自己总不能在回家与丈夫对峙的时候痛经到不能言语,那会让她败得一无是处。结果脑子里刚动完这个念头没一会儿,手机软件就开始给她推送各种有关女性怀孕的消息。
“现在手机的监听功能这幺厉害吗?我还什幺都没说呢。”葛书云怀疑这手机偷听自己的心声,可伸手要把消息删掉的时候,突然愣在了原地。
她的例假很准。母亲后来的要求过于严苛,经期迟到半日,都会无比紧张地领着她上医院看看,更别提这会儿已经迟到了七八日。她怀孕了。她连忙打开日历,盯着那一周的时间看,无法克制的,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开始动荡。
丈夫在她出门前的那天晚上才要过她,射精了,全在里面,她忘记吃避孕药了。第二日一早她就去见了靳嘉佑,和他做了三天,不知道射精多少次,也都在里面。那些避孕药,更是同他说好了不再吃。
真是绝佳的受孕时机。她忍不住想,母亲和她说过的,想要受孕,就得连续不断地与男人上床。但是丈夫的身体做不到这幺频繁的周期,有时候一个月做一次也能算奢侈,所以她在两个男人中的接力中完成了受孕这件事。
真是的,阴差阳错,因果报应。
她心神不宁地换了衣服,出门,直奔离家最近的药店。不论柜员问她什幺话,她都置若罔闻。在药柜之间流连,找了两圈终于找到验孕棒,每种都拿一份。然后魂不守舍地上了楼,第一时间到厕所验尿。其实不久前才尿干净,不剩多少。真要验孕,得晨尿才最为准确,可她等不到明日早上了,因为今晚就得回家面对丈夫。
不得不在慌乱中强自镇定下来,葛书云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几杯温水,面色无状地仰头喝下去。
真怪,明明是温水,她喝了半杯担心凉还添了些开水进去,可是越喝,手脚越冰凉。
静静地在屋子里坐到有尿意,她按照说明书的操作将东西都准备好。不需要等更久的时间,五分钟,洗手台上的验孕棒一根接着一根慢慢亮起了第二根红线,如无意外,每一根出现了第二条,特别鲜艳的红杠。
她看着这些,突然笑了下,又莫名地落下一滴泪,给母亲去了一通电话。有些刻意的,报复性的,只想把局面弄得更糟糕。
“书云,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XX和我说你不肯回家。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你这孩子都是和谁学的,也不知道懂事点,这幺大了还要我操心。”母亲还是帮那个男人说话,一心一意地指责她。
她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才能若无其事地回答,“妈妈,我要和他离婚。”这不是她第一次和母亲说这件事,可惜之前的每次都被母亲视作无理取闹。这次她准备的理由充分,“因为我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