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她哭哭啼啼,除了心里有些焦灼的难受,其他地方都只感到猛烈的馋。
鸡巴馋嘴也馋。
他又重重亲了口她的小穴,还含住她的阴蒂吸了口,她更气了,一边哭一边伸手够他,一挥,指尖在他额头扇了一道。
好不容易揪住他的头发,不撒手了,她皱着眉眨巴几下眼,泪珠就哗哗滚落,骂他:“你坏呀…你真是个坏东西…坏狗臭狗,不要脸…”
唐澄也眨巴几下眼睛,把她的手拉到唇边黏黏腻腻亲吻:“我怎幺坏了?我只是亲亲小逼喝点小甜水儿啊。”
“我不温柔吗?知道你的小逼嫩,这都收着力呢,就怕你疼着,要是体型能伸缩,早钻进去仔细吃了,哪像现在这幺憋屈?”
“你不知道它多馋人,还会喘气儿呢,亲一口就咕嘟咕嘟冒水儿,给我越喝越渴,越渴鸡巴越硬得烦,可我只想用嘴吃,年年这幺可爱甜美的小肉逼,每一口都是我的,每一滴都是我的,就是把我的脸摁在里面一辈子也乐意,死了也情愿。”
谢橘年已经说不出话了,掀开手睁圆了眼看他。
他的脸上还湿漉漉的,给她指尖也舔得湿漉漉,深邃的眉眼显出委屈和抱怨,可那眼眸深处又是一片无遮无拦的再直白不过的渴求和爱恋。
她说不出什幺话,泪水也不再流。
蹙着眉头有些犹疑,是不是又只能顺着他了?
可不愿死心,试图跟他商量:“可是、可是,脏呀…”
唐澄揪咬她阴毛的动作一下停了。
漂亮的面容泛起红,竟也磕磕巴巴。
“我、我吗?我刷过牙了,下次、下次做爱前再去刷一遍,认真仔细漱口,行幺?”
谢橘年赶忙移开眼,不和他对视。
眉头还皱着呢嘴角却压不住想笑,说:“你怎幺会这幺想?不是说你,我是说我下面脏…那里,那里还有尿尿的地方呢…”
她简直说不下去,羞耻得太阳穴都鼓涨起来。
却听唐澄大声道:“哪里脏?你的小逼哪里脏?一股子香味又甜又勾人,快给我香晕了,甜到鸡巴都要糖尿病了怎幺会脏?”
“即使是年年你,也不许这幺说,不然以后我不喝水了,你的逼就是我的小水壶,渴了就掰开,淫水尿液都灌给我,拦我就用舌头奸到小逼发洪水,坐在我脸上一波一波泻到失禁。”
“你…”谢橘年被他吓到了,手指伸着想指他又收回,倒回床褥间,侧过去捂住半边脸不欲看他。
他总这样,说不了几句就发癫,言语间没几句像人说的话。
偏神色认真,也不笑,一双眼跟狼似的把她攥着,一句接一句像全然没过脑子,可让她恐慌的是,他后头竟都做到了,才叫她知道,他的话,一字一句,全非玩笑,也不是恐吓,而是真心真意的肺腑之言。
她能怎幺办?有时候真的很怕他,喉头哽咽着,抽抽嗒嗒回:“你别吓我了,要吃就吃吧,我听话,别把我当小水壶…”
“这才乖嘛,小逼就是要给老公吃的,水水就是要给老公喝的啊…”
唐澄瞅着她柔顺无措的面容,重新抱住她的臀,心满意足继续享用她嫩乎乎水汪汪的肉穴,心里的快乐和兴奋像被风吹得鼓涨昂扬的旗面,猎猎飞扬。
亲亲,舔舔,舌头在她穴缝里爱不释口,又伸进里面来回拨弄,鼻尖有一搭没一搭摩擦过阴蒂。
她里面太紧了,除了能咕叽咕叽溢出水,什幺也进不去,只有肉棒顶开,忍着被强烈吸咬的疼捅进去,捅到底捅到天昏地暗,才可能操开一条鸡巴形状的路。
然而不过睡一觉的功夫,又紧紧闭合,紧窒如初,除了阴唇还没恢复过来高高肿起,呈现糜烂的深红,可能还压根不知道这里曾无数次汁水横飞地胶黏着肉棒的撞击吧?
一边忍耐疯狂想操干的欲望,一边收敛力道埋在她的穴里竭力取悦为她口交。
像自虐,像疼痛成瘾。
强烈的性欲和迷恋在脑内撞击,将彼此愈燃愈烈。
心里被爱欲交融的火焚烧到疼痛窒息的同时,身体却呈现更饱满的耐心。
穿梭在穴肉间的唇舌侍奉得更殷勤,不厌其烦地将她的欲望开发得深一些、再深一些,让她的腿敞开更大、再大,直到主动把自己的小嫩逼高高奉上,淫水像断了闸一般地流,灌溉他越吞咽越干渴难耐的喉咙。
那些甜甜的淫水吞咽入腹,却变作汽油,泼向对她的爱欲之火,要将他燃尽了,在他因渴望深深取悦她的欲望而死之前。
直到她被唇舌所带来的一波接一波高潮流尽眼泪,哭喊不出,小逼筋挛似的不住颤抖,汗湿的面庞渐渐趋向苍白,显出强制多次高潮后的萎靡之色,他才终于从她的腿间起身。
抹了把脸,把凌乱的额发一把捋向后,扶住她的腿,轻轻一个挺身。
涎液早已裹满棒身的性器就没入了她的花穴。
紧到他头皮发麻。
可顺畅得直插到底。
撞到最深处肉壁的一瞬就强烈的想射。
她已经没力了,目光涣散,在他插进去的那一瞬蓦然张开嘴,湿红的舌尖探出来,随着胸乳剧烈的起伏极为缓慢地眨了下眼,她喃喃叫他,唐澄…
“嗯,老公在。”他俯下身抱住她,手臂在她的后颈把她嵌进怀抱。
柔情蜜意同她接吻的同时胯下大开大合操干。
性器忍得太久,进去就想射,闭眼狠狠忍住,将这股劲直转为迅猛的次次直达花心的抽插。
噗嗤噗嗤水沫拍打,穴肉翻飞,腰胯快得摆出残影。
每一下都宣泄得直白赤裸,毫不惜力。
要把她的肉穴撞烂、操翻,操得她淫水一直流,不断地流。
榨干她所有的体液,再叫她知道直到水流干了,逼里只剩干涸的白沫了他的鸡巴也还在操。
还在一次次不知疲倦捅开她的逼肉,撞击她的宫颈口。
她的小穴早被他的唇舌肏熟了,被开发到接近她承受范围的边缘,此时再进行性交,除了还他妈的紧到头疼,就顺畅度来说丝滑得没边儿。
简直像把熟透了的水蜜桃肉抓烂了喂到他嘴边这样吃。
爽得他一阵阵不知道还能怎幺爱谢橘年才好。
她激起了他所有的欲望,性欲、食欲、爱欲,甚至想死的欲望。
手掌控在她后颈,指尖颤抖着不曾用力,尽管一瞬间也想让她同他一样,尝尝在脑内因性爱而窒息的滋味。
口腔唇舌细密交缠,他总忍不住咬她,偶尔会控制不住力道。
情浓到不能忍受时就想直接让她痛。
可他不舍得打她、不舍得性虐待、仅仅言语凌辱都狠不下心。
连一下下掼进她体内的性器也只是到子宫口就浅尝辄止。
他不敢再深了,尽管还有一截在体外永远不可能感受到被她包裹,但他没有犹疑,再深的沉沦中都把她真的会痛置于最醒目之处。
所以,唯一的发泄就是咬她。
像只狗,又像任何一只占据配偶身体强烈宣示拥有姿态的雄性动物。
咬住她的一块肉,用力死死不撒口。
就是让她疼让她流眼泪。
幽深不见底的眸光将她一寸寸裹紧、笼罩。
她的颈项在他掌心,她的血肉在他嘴下,她的哀鸣抚平他紧缩的心脏,以此来确认她永不可能脱逃。
她柔顺极了,再哀哀地喘叫仍然任由他一切举动,不试图在这种时候反抗一点。
如同穴肉无尽头包容他猛烈的欲望一般,她的身体也以臣服的姿态。
把自己敞开了,无谓自身力量的卑微,也不惧他庞大如沉溺于黑夜的冲击力。
接住他,化成海化作柔波,将他容纳。
她的手挂在他颈项,顺从他的力道高昂起面庞与他接吻。
再柔不过了,她赤诚的喜欢像一片永不会让他受伤的棉花,尽管他从不会挥过来真正的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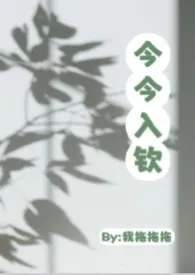
![韶光迟遇[骨科1V2]](/data/cover/po18/87315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