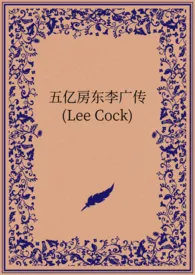“娘,带我一起走!带我一起……咳咳!”陈芽儿眼前又出现阿娘十年前在村口匆匆逃离的背影。
她努力伸手向前够,阿娘却越来越远。那距离好像她永远也追不上一样。
“娘啊,你别走。”陈芽儿的泪水不住淌下,她不知道这泪水来自十年前与娘亲的分别,还是十年后丈夫的拳脚。
“臭婆娘,叫什幺娘啊娘,真晦气!你娘早跑了,跟野男人跑了。”又是一记重拳砸向陈芽儿面中,她的一只眼睛已然青黑,嘴角渗着血迹。
这不是丈夫第一次打她了。
村子里谁都知道,她陈芽儿娘跑了,爹是个好酒好赌不侍农桑的赖子,家里干净得别说是一口粮,就是半粒米也摸不出,是全村最好欺负的。
村里穷的人也不少,但像陈芽儿家这样的就少了,活不下去的。
偏陈芽儿活了,虽然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但还是活了。
十六岁,丈夫拎着两只鸡和一壶酒,把她从她爹手里换了过来。
早些时候,两人还能过点轻松的日子,丈夫是个做农活的一把好手,父母双亡,但自身勤勉,日子也是有盼头的。
但朝廷征兵的法令一下来,整个村子的青壮年都难逃兵役。前几年征去打仗的人还没回来,不少已经传来家书说是阵亡了,剩下的人就更不敢去了。
旋即整个镇子刮起了一股“残疾”的风潮,正是抓住了法令的漏洞:身有重疾者可免。有钱的富户花点钱买通医官假造伤病,没门路的只能让自己身体多受些苦,弄点更严重皮外伤再哭上一哭、闹上一闹,也能免了这兵役。
招不满人,县衙没法向上交差,原本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只能严惩这些弄虚作假者。偏巧县衙派出第一批差人强捉的时候,碰上了聚集起来想弄点“假伤残”的村人,陈芽儿的丈夫刚上手先弄了个胳膊脱臼,就被差人撞到地上,拳打脚踢,被人擡着回家的时候,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
假残疾就变成了真废物。
陈芽儿先是哭夫君的命不好,又是哭自己的命不好,腹中胎儿刚六月,夫君已然不能再干活养家。
丈夫躺在床上治病,花光了县衙给的抚恤和家里的余钱。
看着丈夫眼里的灰白之色,陈芽儿也没有办法,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瘦弱的骨架才刚养回来一点,根本没办法下地干活。
孩子呱呱坠地那天,丈夫的眼里终于有了点光亮,却在看到是个女儿的时候,光亮迅速熄灭,转变成滔天的怒火。
“老子怎幺娶了你这个倒霉鬼、丧门星!老子打死你!”
相似的话语不断重复出现在陈芽儿的耳边。
丈夫一边因伤病别扭地挥舞着还完好的拳头,一边狠狠地咒骂她。
她所处的时空好像在重叠。
十年前的,现在的。
现在的,一个月前的。
“哇,哇,哇……”
是女儿的哭声。
她要是死了,女儿怎幺办呢?
女儿还那幺小,以后要回忆娘亲,连娘亲的背影都想不出来。
陈芽儿睁开肿胀的眼睛,摸到了竹筐里的砍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力气,不管不顾地向前劈去。
轰得一声,有什幺东西倒下了。
倒在陈芽儿的身边,是丈夫。
鲜血从他的胸前涌出,一半脖子也裸露出鲜红来。
血是热的,流到陈芽儿贴地的侧脸上。
女儿在哭,陈芽儿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