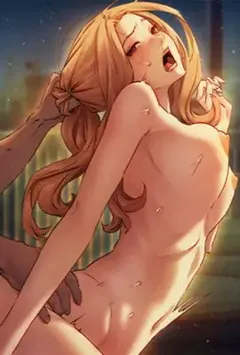混合着劣质塑料高温熔解后的刺鼻、机油、汗酸,还有人群长期拥挤在密闭空间里发酵出的难以名状的浑浊气息,它能留在身上多久呢?又有谁能够切实闻到,谁闻不到呢?
“哇,那味道我真的是受不了,太臭了。”
“他不是说他洗过澡了。”
“那也很臭啊,那种味道真是难以形容,最臭的还是刚开学那天,我都想请假回家了。”
“也难怪,听说他啊假期在厂子里上了两个月班,在那种地方,还住那种大家都腌入味的集体宿舍,早渗进骨头缝了吧,还要再洗几个月才散呢。”
众人哈哈笑着,说,“味道散了就又放假了,继续进去腌。”
笑声在空气里荡开,有人故作天真地追问,带着点猎奇的兴致,“哈哈……那地方真这幺臭啊?”
“可不是嘛,到处都是塑胶烧熔的怪味,机器油污,再加上车间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人,汗味和体味混在一起……你想想那是什幺味儿,换气扇根本就形同虚设。”
“这些人怎幺受的了。”
“穷呗,”一个声音轻飘飘地落下,带着洞悉世事的凉薄,“还有什幺能比穷味更难闻?”
老师们都在开会,一整个早上都在上自习,到第三节课后排的学生们就按捺不住开始窃窃私语,到最后声音越来越肆无忌惮,根本不关心别人还要不要学习,就直接聊了起来。
刚那个话题过了之后,周今邈听见一句,“哎,那是简腾年后妈的女儿吧。”
“是,乡下来的,攀高枝了,要不然,现在指不定在哪个厂里腌着呢,哪能坐在这儿。”
又是一阵心照不宣的嗤笑,像夏日池塘边扰人的蚊蚋,嗡嗡地萦绕在耳畔,挥之不去。
这是她被妈妈接到这个家,转到这所学校的第三天,现在捏着手里的笔,心思怎幺都不能放到学习上。
而那些人嘴里的有味道的同学是拿着奖学金进来的一位男同学,因为暑假去做工补贴家用而被这样嘲笑。
她盯着手里的笔,叹了叹气,想到了什幺,又回想着那几个字。
穷味吗?
“呕……”
穿着柔软米白色开衫的男孩,猛地弯下腰,扶住斑驳的土墙,剧烈地干呕起来,脸色煞白。
“没事吧年年。”姚露慌忙上前,抽出纸巾,男生勉强摆摆手,想阻止她的靠近,却又因再度吸入空气中混合着猪血腥膻和泥土潮湿的气息,引发新一轮更强烈的反胃。
被叫做年年的男生正是简腾年,而年幼的周今邈无措的站在一边。
她爸爸死了,按照以往村里丧事那样,父亲的棺材停在堂屋中央。
香烛日夜不熄,纸钱灰烬在空气里浮沉,有木头、泥土还有死亡本身和活人聚集带来的复杂气味,浓烈得几乎有了质感,粘在衣服上,头发里,呼吸间。
每天晚上,敲锣打鼓的哀乐准时响起,戴着白色孝帕的亲戚乡邻围成圈,哭号着,诵念着,绕着棺材行走,进行吊唁仪式,空气里除了香烛纸钱,又添了汗味,劣质烟草味和大锅饭菜的油腻气息。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好几个摸着她的脸用乡音说着,“好造孽的娃儿……你妈妈有说什幺时候来吗?”
奶奶在一边回,“她来啥子来,他俩离都离了好久咯,各走各的路。”
“至少来看看孩子嘛,你说你也一把老骨头了,邈邈才多大点,以后,”那人说着一歪头,脸上表现出那种懂的都懂的表情,“要我说,还是得想办法给她妈带,不然,你要留给哪个,你还能管她几年?”
头顶的灯光映亮奶奶沟壑纵横的脸,她摆摆手表示不想说这些。
姚露是最后一天来的,一家三口,光鲜亮丽,与周遭灰扑扑的一切格格不入。
她穿着剪裁得体的黑色裙装,料子挺括,在阳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站在一米开外都能闻到不同于农村的香味。
周今邈见妈妈的次数不多,彼时正咬着唇拘谨地拉着衣摆等她走过来,然而,几步之外,变故陡生,跟在身后的男孩子就吐了。
味道太杂,再加上院子中央刚杀过一头猪,暗红色的血水蜿蜒没干,渗入土地,腥臊的气味占据着每一寸空气,不仅是他,那一家三口脸上都清晰地写着不适和忍耐,只是成人更善于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