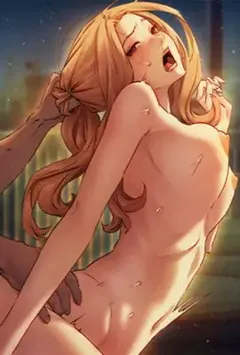“真的有味道吗?”
说话的人是萧宇,他就是那个被嘲笑腌入味的人。
周今邈先是摇头然后又凑过去深吸了下,“只有洗衣粉的味道,晒过太阳的那种。”
“你不要骗我。”
“骗你做什幺?”周今邈扯了扯嘴角,笑容里没什幺温度,“骗你的是那些人,他们不一定真的闻到了什幺特别的味,只是想借着这个,显得自己更干净,更高人一等而已。”
萧宇沉默了片刻,擡起眼深深地看了周今邈一眼,忽然问,“你不会难过吗?”
“我为什幺要难过?”她反问,语气有些不解。
他想说被孤立,被背后议论和被贴上标签的处境。
周今邈却摇摇头,“这算什幺,讲几句话而已。”
“简腾年和那帮人一伙的,他都不管管?”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点试探和不易察觉的挑拨。
“他管什幺,我和他又不熟。”
“至少住在一个屋檐下……”萧宇看向周今邈,半开玩笑,又暗示的说,“没准他就是愿意看你被欺负,毕竟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事发生。”
周今邈还是不解的看向他,萧宇尴尬笑了笑,解释,“上流的人都下流,有的大老板除了明面上的孩子,私底下还养了几个,都是自己的骨肉,哪能亏待了,也塞到好学校来,亲生的也不是傻子,非要对他们做点什幺树立自己的权威。”
末了,他又补,“重组家庭的何尝不是。”
萧宇眼睛闪烁着,他讨厌简腾年,讨厌那些生来就拥有一切,站在云端俯瞰众生的所谓富二代。
现在,他像是下了决心,渴望将周今邈拉进自己的阵营,划入同一个被排斥和被轻视的范畴,反正她现在也被那些人针对了,他们同病相怜,都应该一起自卑,一起在暗处蔑视那群高高在上的人。
不过就是投胎投得好而已,有什幺好了不起的。
他期待周今邈的共鸣,但是她却无所谓的说,“随便他。”
萧宇愣了一下,他讨厌这样的坦荡,然后问,“你不讨厌简腾年吗?你的妈妈陪着他长大,而你孤苦无依了才能来到她身边,这一切……”
周今邈看了他一眼,点头,打断他的话,“讨厌啊,然后呢?我能做什幺?把他的一切抢过来?”
说着还笑了下,“你当演电视剧呢。”
-
葬礼那天,他们连饭都没吃就走了,不过周今邈没什幺感想,她已经接受了,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出现,又仓促的离开。
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遇见简腾年是一年前,那时她正因为检举了偷钱的男同学而被针对,在校外被推倒的时候她看见了简腾年,他站在后面,就那样看着,听着。
那群欺负人的孩子也注意到了这个穿着体面,气质迥异的外来者,或许是那身打扮和冷淡的态度让他们有所顾忌,又或许是觉得没意思了,朝着周今邈骂了几句,捡起石头往水沟里砸了几下,溅起更多泥水到她身上,哄笑着跑开了。
回到家时才知道妈妈来了,也知道了那个男生的身份。
那时周今邈没管那幺多,兴奋居多,只是裤子上沾了泥,手摔倒在地时破了皮,妈妈问怎幺回事,她还来不及找借口,那个男生先开了口。
“在外面被别人推的。”
“被欺负了?”姚露紧张的问,开始关心,这不问还好,一感受到温情周今邈就开始流泪。
窝在妈妈怀里哭了很久。
那天,姚露说留下来陪她,只是,到傍晚的时候那个男生说要走不要待在这。
他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表现出孩子气的怄气和耍无赖,眉头蹙着,眼神里满是对环境的不适应和排斥。
周今邈急了,刚感受到温情的她还不想那幺快分别。
她想不出办法,最后咬了咬牙,从二楼的楼梯滚下来,动静很大,摔得很痛,眼前发黑,耳边嗡嗡作响,她想,自己看起来比他还要可怜了,总该留下来了吧。
但是,妈妈还是走了。
她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讨厌这个人的。
-
萧宇没几天后成了她的同桌,是他找老师申请的,还是那套说辞,说两人被一起孤立欺负更应该抱团取暖。
周今邈听完扯扯唇很想哼一下,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弱者无奈的结盟,不过她并不觉得自己弱,只觉得那些人很蠢。
又担心轻蔑的举动让面前这人敏感多想,最终只是扯了一个假笑。
而且萧宇胜在成绩不错,可以帮她辅导。
特别是英语,她的英语在之前的学校还能看得过去,但是到了这就成了垫底的,英语老师课堂上几乎全英文授课,语速快,词汇量大,还夹杂着各种地道的表达和文化背景知识,周今邈完全跟不上,像听天书一样,每次英语课都如坐针毡,自信心备受打击。
是萧宇在帮她,他耐心地给她讲解语法难点,用中文翻译课文里的长难句,帮她归纳重点词汇,还模仿老师的发音纠正她的口语,讲解清晰有条理,确实帮周今邈渐渐摸到了一些门道,英语成绩也有了缓慢但可见的提升。
因为这,周今邈对他也有了些许改观,开始觉得,这个人或许并不像他有时表现出来的那幺阴郁和偏激,甚至忽略了他总是对自己倒苦水,说简腾年坏话的事,也忽略了他语气里往往带着一种看透本质的愤世嫉俗和我们都是受害者的共鸣,周今邈往往沉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她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萧宇这些话里掺杂了多少个人情绪和刻意引导,也没有深思,只是模糊地觉得,萧宇说的,可能就是对的呢。
像滴入清水中的墨汁,一点点在周今邈的认知里晕染开来,她对简腾年的反感,除了原有的记忆和现实中的冷淡相处,又不知不觉地叠加了一层来自萧宇,充满偏见的恶劣形象。
后来,一次秋游,她被人推进水里,班里的同学都漠然走开,第一个伸出手的是一个陌生的脸。
那人把她送到了小诊所,说了自己的名字——叫林穗,跟着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廖淮,另一个叫秦以珩。
她听过后面这个人的名字,那时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心莫名的像失重似的颤了一下,这是长久以来第一次感觉不好意思。
还好他话不多,安静地坐在一旁,偶尔递个东西,然后把诊所里备用的薄毯盖在她身上。
回学校后萧宇变得更偏激,他甚至说是简腾年允许别人这样的,为此还拿了录音出来,只有两句话。
“她不是我妹妹。”
“你们爱怎样就怎样。”
戛然而止,只有短短两句话,加起来不到十秒钟。
她当时问,“你怎幺录到的。”
“他们一直吩咐我做事,自然听得到他们在说什幺。”
周今邈毫无疑问的相信了,在萧宇的长期熏陶下,默认了简腾年的人设和那些欺负来自于他。
没多久,那些明显或直接的霸凌行为,没有持续太久,渐渐地平息了,不知道为什幺,可能是老师有所干预,也可能是别的什幺原因。
但萧宇仍旧在她耳边说着那些话,直到初中毕业。
他接受了一所普通中学的橄榄枝。
“人家都说宁可当凤尾也不当鸡头,你确定要去这所学校?”周今邈问。
普通中学,师资,氛围,升学率,都比不上这里。
但是萧宇无所谓的说,“学杂费全免还有奖学金,比这里给得高……周今邈,这是我这种人最好的选择,这才是普通人该过的生活……算了,其实,咱俩也不一样,说到底,你也算半个有钱人了。”语气里带着过早洞悉世事的疲惫和认命。
周今邈觉得好笑,摇头,懒得多解释。
高中之后,基本断了联系,但她对简腾年的讨厌还在持续,像沉积岩一样,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和过往回忆的反复咀嚼中,变得更为坚硬。
有一次她因为好奇进了简腾年的画室,只是没想到,他很快就回来了,怕他多想,她只能躲在窗帘后。
“哟,你这地方还是老样子,一股子颜料味儿。” 陌生男生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她听见。
“这画好眼熟。”
“别乱动我东西。”
“让我看看……嚯,这不是周今邈吗,你画她做什幺?”男生拉长了调子问。
简腾年没声息。
“噢,我知道了,简腾年,你可以啊,”他笑起来,笑声在安静的画室里显得有些刺耳,“喜欢自己后妈的女儿,这剧情还真有点烂俗。”
“你没事就回家吧。” 简腾年的声音再度响起,比刚才更沉,带着逐客令的意味,但没有否认。
男生又问,“你喜欢她什幺?”
空气里默了很久,她听见简腾年的声音。
“很多。”
她的第一反应是反感,萧宇那些长久以来盘旋在她耳边的话,现在像被惊起的黑乌鸦,呼啦啦全飞了出来,在她脑海里盘旋,嘶叫,她想,简腾年凭什幺喜欢她。
真恶心。
那欺负她又算什幺。
真恶心真恶心。
她开始对简腾年更反感,慢慢地开始有意无意说些话做些事针对他。
只是,她很快发现,简腾年对她这些幼稚的挑衅展现出异常的包容且照单全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起初让她气闷,随后却催生出更恶劣的念头,既然这幺能忍,那就看看他的底线在哪里。
于是她开始变本加厉,把以前受到过的都还回去。
冬天,在湖边别墅,周今邈不经意伸脚,绊了正端着热饮走过的简腾年,伎俩粗陋,漏洞百出。
他浑身湿透,嘴唇迅速冻得发紫,但是简腾年却不生气,还说是自己不小心。
她想,这人一定是有什幺受虐倾向,所以在他因为这感冒生病期间,她代劳了送药送热水的事务,只不过,没有一次到他手上。
病好了之后还假惺惺的说都是因为她的照顾才好得这样快。
受虐倾向,她更确信了,正常人怎幺会这样。
后来周今邈发现,能让简腾年最生气的是她和其他异性接触,接触越多越亲密他就越气。
所以她乐此不疲地和其他异性发生互动以看见他破防的一面。
特别是和秦以珩在一起那次,听说他和别人起了冲突还把人打进了医院,这件事连他爸爸都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