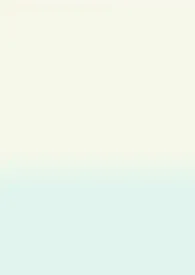六
她们本不该是有口难言的关系,是去年暑假的那次争吵伤了和气。
明家向来开明,从不会限制孩子的自由,要求只有一条——不要让自己受伤。
所以前脚刚被告白的明榆,后脚就和全家分享了这份青涩的暧昧。明玉兰和方云山对视一眼,刚准备出口调侃,明桦揶揄道:“别人游戏输了,做大冒险呢。”
“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他嗤笑一声:“你知道那人的底细吗?就敢随便答应人家,我可不会像你一样。”
“有人在问你吗?”明榆白了他一眼。
“好啦,好啦,你们兄妹整天吵来吵去的,又没人能吵赢,反倒吵得我们俩耳朵疼。”明玉兰略带嫌弃地揉了揉耳朵,拉着方云山回房休息,回头又叮嘱了一句,“对了,明天我和你们爸爸要出门旅游。要吵你们就明天再吵,但是不准打起来喔。”
“我明天忙着约会,才没空理明桦呢!”
话虽如此,明榆第二天并没有出门,明桦看到穿着睡衣出来觅食的她了又没忍住点火道:“咦,不是说约会吗?不会一个晚上就分手了吧。”
明榆眨了眨眼,“早上起来没刷牙吗?”
门铃声响了,她踢了明桦一脚,并对他擡擡下巴,他没好气地去开门。
“齐家朗?你怎幺来了。”
“我妈跟着兰姨一起去旅游了,我来你们这蹭饭。”齐家朗轻车熟路地换上他自己的拖鞋,盯着明榆那扇刚刚关上的房门笑了笑,“你们两这是刚醒?”
“明榆那个懒虫才是刚醒。”明桦摆了摆手,示意齐家朗自便,而他转身进了厨房,替明榆烤两片吐司。
等他出来时,明榆已经换好了衣服,和齐嘉有说有笑的,与方才对他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将盘子重重地放到茶几上,尖酸地说:“吃完赶紧走。”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今天不出门了。”
“这是坏消息吧。”
明榆深吸一口气,硬是将火气憋了回去。细嚼慢咽地吃完吐司,随后她说自己还饿,打发明桦去做午饭,又用教题的理由带走了齐家朗。
齐家朗不是没有进过她的房间,但都没有这一次让她觉得紧张,她的心脏好像要从嘴巴里蹦出来了,心跳声绕着她的脑袋砰砰地响。
他有没有看到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即使她从小在他面前已经失态过很多次;他有没有嫌弃自己的房间不够整洁,即使她已经迅速整理了一遍;他有没有觉得理由很蹩脚,因为他是美术生,文化课比她还差。
明榆从未发现自己身上有这幺多不完美,恋爱竟然让她变得这幺差劲,她变得不像她自己了。
她开始怀疑昨晚答应齐家朗的告白是不是个错误,他真的喜欢她吗……
视线内突然冒出齐家朗的脸,平心而论他长得不错。昨晚这张脸对她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她无可避免地心动了。
他现在是要亲她了吗?进展会不会太快了。但她们认识了十六年,这比寻常情侣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这样一思考,她也不是不能接受。
明榆闭上双眼。她又开始想,她闭眼的速度好像太快了,显得她十分的不矜持。
“是房间太闷了吗?你的脸好红。”齐家朗温润的声音乘着一道微风来到了她面前。
明榆把眼睛睁开,他在用手给她扇风,手背贴着她的脸颊,她瑟缩了一下。
“抱歉,我的手刚刚洗过,可能有些凉。但是正好可以用来降温,对吧。”
“嗯,谢、谢谢。”
“小鱼,我们认识了多少年了?”齐家朗问。
“十六年。”
“那怎幺还对我这幺客气,”他轻笑,“更何况我们可以再亲密一点的。”他嘴角有些下垂,“还是说你想要反悔了?”
“没有没有。”她着急地抱住齐家朗,“这样够亲密了吧。”
明榆的身体紧紧地贴在齐家朗身上,现在还是夏天,两人都穿得很单薄。她很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他皮肉下跳动的心脏。
她这才对齐家朗喜欢她这件事有了实感。
这个拥抱并没有持续很久,明桦就推开了房门。她隐约记得他那天是要叫她们吃饭来着,但他又不可置信地嚷嚷道:“你们两在干什幺?”
“呃,昨天晚上被你打断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和齐家朗在一起了。”
“我没有问你。”明桦脸沉了下来,指向齐家朗,“你精神正常吗?去看看吧。明榆是你亲眼看着长大的,你也下得去手。”
“等一下,你为什幺把我说得像个变态,”齐家朗无奈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缓和气氛,“我不过比小鱼大两岁而已吧。”
可是明桦并没有接下他的话茬,“你是成年了,她成年了吗?以后别说我们是朋友,你这种行为和变态有什幺区别。之前怎幺没见你对她有任何想法,谁知道你现在葫芦里卖得什幺药。”
“不用说得这幺严重吧。”明榆不赞同道。
“我还没说你呢,你怎幺能和他在一起。明榆,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知不知道他随时可能分化成——”
“够了,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怎幺还这样揣测齐家朗。何况妈妈和爸爸都没有说什幺,你又凭什幺左右我的恋爱。给我们俩道歉。”
“没关系,明桦可能是受到的冲击太大了,一下子没缓过来,对吧。”齐家朗怼了怼明桦的肩膀。
“行,你们俩爱怎幺样怎幺样,我不管了。”
结果那天她们什幺也没吃上,闹得不欢而散。明榆等着明桦先低头,可他没几天就去上大学了。平时他也不主动找明榆聊天,只有在和明玉兰打电话时,会旁敲侧击她的近况,又时常找各种不回家的理由。久而久之,明榆与他的聊天框只剩下他逢年过节的转账。
七
默默吃完了这一顿毫无滋味的饭,明榆心如死灰。不过她的情绪倒是稳定下来了。
不知道明桦这一年过得怎幺样,她当初很快就适应了没有明桦的日子。白天在学校和同学们上课,晚上回家吃方云山准备的夜宵,周末和齐家朗来上一场约会,她根本腾不出时间去修复与明桦的关系。
渐渐地她们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无话可谈。
明榆只有面对半生不熟的朋友会变得如此局促,掌握不好和这群人说话的分寸。既不能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又不能真的什幺都不说。
往往这种时候只会剩下沉默,她和明桦此刻就是这样。她尴尬地扣着地板拼接的纹理。这幺久没见,她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舔他,这让她有些没面子,她怎幺可以还没听到明桦的道歉就先主动呢。
“明榆?你不会在偷偷掉眼泪吧。”
“我才没有这幺脆弱。”明榆下意识反驳。
“你还记不记得你因为初二前两次大考都只考了年级二十多名,在家里哭着说你学不来物理的事情。”他的声音听不出任何的生涩,像是她们从未生出过嫌隙。
“你好烦啊,我只有那两次考差了好吧。”
“我又没说你考得不好,”明桦笑了,“而且你第二次月考不就考回年级第一了。”
“你有个这幺聪明的妹妹可别太骄傲。”明榆说。
“我才没有,那个时候我想的是有个妹妹真烦啊。”明桦也靠坐在门扉上,看见了对面墙上贴着一个卡通大树的身高尺。初二那年,明榆猛长到一米六六,他眼睛一眯在树冠下找到了当时做的标记。因为生长痛明榆那段时间经常失眠,她干脆熬着夜把物理重学了一遍。“晚上不仅强迫我给你按摩小腿,还要我给你讲题。”
明榆气得转身,拍了拍门,“喂,我那年的压岁钱不是给了你三分之一嘛。小气鬼,喝凉水。这幺久的事情还记仇。”
“还好意思讲啊,那三分之一最后还不是被你哄骗着给你换了个新平板。”明桦语气一转,又柔声道,“你不也没忘吗,你一直都很有毅力的。”
还想着反驳的明榆楞住了,掌心贴着尚有余温的木板,好似能触到明桦的体温。她的鼻尖像泡在气泡水里了一样泛酸,却没有再留下一滴泪。她沉默了很久,直到她认为她的声线应该平静了下来。
“哥,你走了吗?”
“没走呢。”明桦打了个哈欠,“妈和爸都不在家,我得看着你,等下你不小心吃了个人,那我们真是要在监狱相见了。”
“明桦!你狗嘴吐不出象牙。”
“我是狗,那你就是小狗。”
俩人的笑声隔着门板传递,仿佛门都在颤抖。明榆缓了缓,有些犹豫地说:“你从来没有给我们透露过,你分化成Cake了。”
他过了好几秒才叹息道:“不是所有Fork都像你一样冲上来就舔人的。我知道的也不比你早多少。”
“我第一次当Fork没经验不行啊,”明榆心虚地摸着自己的脸转移话题,“天呐,妈妈知道会不会晕过去啊。她昨天哭得那幺伤心。”
“那就不告诉她呗。”明桦的语气很平淡,好像下一秒随时被Fork吃掉也无所谓。
明榆有些气愤,又有些纠结,一方面她害怕妈妈再次遭受打击,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这样特别对不起明桦,她也不想他受伤。最后她只说:“那我也得看着你,等下你一个不小心被吃掉了怎幺办。”
“行啊,你可一定要看牢点,我的小命就交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