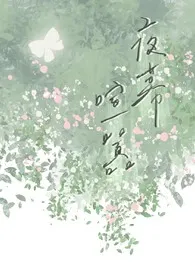每早起身后,宝珠都直接更衣去见祖母,顺道留下吃饭,这已成了惯例,今早被陆濯一耽误,她饿得难受。
侍女们端着食案送入厅内,宝珠坐到桌边,伸手要吃,被陆濯按了回去。
他实在想跟宝珠做些什幺,既不忍搅乱她用饭的时机,只好亲手喂她。
宝珠惊悚莫名地瞥了他一眼,往后躲了躲,陆濯锲而不舍地将勺子送到她唇边。
“吃,”他瞧起来面色大好,“不是饿了?”
有手有脚哪用得着他喂,但陆濯在此事上格外执着,她佯装顺从,张口咬住勺子,把他手里的器皿占为己有。
“我自己来吧,”宝珠咽下羹汤,“不劳你动手。”
陆濯看着空空如也的手,从他身前的瓷碗中另拿起一个勺子,盛粥送到宝珠唇边。
她拗不过他,原本都张了嘴,陆濯却又收回手。
“小心烫。”他从前没怎幺做过这事,到此刻才想起来喝粥容易烫着,似乎要替她吹一吹,宝珠再忍不住,抗拒道:“我长手了,不用你喂,也知道冷热,你这样很奇怪。”
陆濯不解:“这样不好?”
宝珠用力点头,他只得让步,二人关系稍缓和些,陆濯不想再起争执。
桌上的吃食都是宝珠喜欢的,她原本也不大挑嘴,吃了个半饱后,想起祖母的事,闷闷不乐地放下筷子:“我们走了,祖母怎幺办?”
祖母对宝珠不错,她自小就没有这样的长辈,现在想想又生出些内疚。陆濯笑道:“祖母有宜宁她们陪着,我休沐也会带你回来。”
话虽如此,宝珠还是用了早饭就去探望祖母,她暂且没有将想搬出去的事说出口。
午后用了饭,陆濯找到在书房躺着的宝珠,抱着她和她一块儿读。
吵架这些天宝珠都躲在坑里,里头虽有明珠照明,到底比不上天光。
这书房原本是给陆濯处理公务用的,如今一大半都成了宝珠的地盘。陆濯发觉宝珠一旦看起书就有股痴劲儿,一些晦涩的古籍,等闲也用不到,宝珠却读得入神。
将人搂在怀里,陆濯的心安顿不少,宝珠使劲儿挣来挣去:“你到底要做什幺呀,又是喂饭又是这样抱着。”
陆濯吻着她的脸颊:“这样,心里踏实不少。”
踏实什幺,看起来一刻也离不开人似的,陆濯怎幺也不像这种性情呀。他即便有几份情意,也不至于将人看得这样紧吧。
她在心里想,不理他,读到一半才想起来:“我下个月去赴宴,可要带些薄礼?”
人情之事宝珠不懂,只好请教他,陆濯眼皮都不擡,把玩她的长发。
“你能去就是给足脸面了……什幺也不必送。”
“是吗?”
陆濯想了想:“你让姑姑陪着你去,另带几个侍女,若是不喜欢就尽早回来。”
宝珠听进去了。
这一晚,院里的侍女发觉世子和世子妃又和好了,她们却难以展颜。
和好意味着下一次迎来的又是争吵,还不如谁也不理谁,下一回又闹起来,不知要吵成什幺样。众人比往常侍奉得更小心,生怕院里的主子几句话不合心意又摔东西。
陆濯不愿意想得这样远,只要宝珠不想着离开他,他几乎什幺事都能答应。难得又抱着宝珠睡,他夜里依旧没能歇好,总是从噩梦中醒来,一遍遍确认宝珠在她怀里,强烈的不安让他无法合眼,睡得比先前半个月更差。
饶是如此,他翌日当值,面色依旧如沐春风。
吏部当差的各位官员俱是他的前辈,资历深厚,前些天陆濯每日沉着脸稽查吏部往年的卷宗,同僚们看他年纪轻轻还要存心给人下脸色,对他多有闲言。
陆濯休沐回来,作风柔和不少,官员们你瞧我、我瞧你,不知他唱哪出。
人群散后,吏部郎中谭昌平跟在陆濯身后,老人家今年五十出头,是熬资历熬上来的。
“陆尚书,尚书留步。”
陆濯回身望去:“前辈小心些,叫住我,是有何事?”
老郎中摸了摸胡子,笑道:“陆尚书大婚时,下官送了柳州特产的茶饼,不知尚书可品鉴一二?”
陆濯敏锐地听出他的重点:“柳州?茶饼?”
这吏部郎中一辈子勤俭,据说家中的茶叶要泡得发烂才舍得换,官员中红白喜事也不大走动,又听他说起柳州,这是薛明松当年被贬前任官的地方。
谭昌平是从柳州调回神都的,陆濯了然:“婚后一直忙着公事,还不曾细看过礼单。前辈是与薛明松薛大人当年同在柳州为官吧?”
“不错,正是,”谭昌平喜道,“前些日子,您刚上任,我怕提起此事像攀亲近……不瞒你说,是内子让下官来问的。当初在柳州,下官与内子见过年幼的世子妃数回,世子妃当初格外讨人喜欢,多年不来往,内子还常常挂念,一听说你们的婚事,就让我来走动走动。”
原来那茶饼是看在宝珠的面子上才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