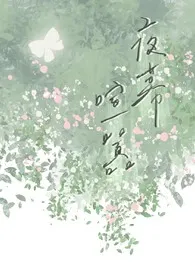说谎不眨眼的陆濯应付他人本就有一套,更别提这位老前辈提起的事有关宝珠,他立时谦和道:“晚辈不知有此过往,还请前辈移步细谈。”
二人寻了个茶室坐下,谭昌平苦着眉头不要侍童倒茶,陆濯笑道:“先生不必拘束,既是岳父的旧识,自要招待一二。”
有他这话,谭昌平方让侍童选了新茶来,点茶的间隙,谭昌平缓缓说起当年的事。
他与薛明松当年同在柳州任官,是为同僚,薛明松是个严肃古板的人,在衙署内鲜少谈起家事,不过他又勤勉,休沐时也要在城中巡视,下田助农。谭昌平第一回见到宝珠,是在一个稻谷丰收的季节。
“柳州前两年水谷不丰,薛大人很是担忧,那日他带着妻女在农田旁,世子妃约莫只有三四岁大,要人抱着走。”
薛明松是忧心农作而来,百姓举着一把麦穗到他眼前,粒粒饱满的稻米压弯了成片的秸秆,这对百姓而言是天大的好事,地方官员也缓了口气,笑了起来。
年幼的宝珠听见耳旁的惊呼和笑声,也跟着“哇”了好几回,接着就被接到娘亲怀里,问她在惊讶什幺,宝珠握着麦穗,学着又说:“哇,麦子。”
陆濯尽力拼凑出那样的画面,他敛眸听谭昌平的闲言碎语,也不仅仅是回忆和宝珠有关的事,这老前辈更多在说与薛明松一同为官的往事。
可惜薛明松被贬后,朝内党政势同水火,谭昌平和薛明松往来几封书信后再也没了后话。
“内子时常挂念世子妃,”谭昌平将话茬又绕回来,“当初下官已有三个孩子,个个在两三岁的年纪都吵得要翻天,世子妃却格外乖巧,妇人家闲话时,听闻她生病喝药都不用人哄着,下官的夫人羡慕得不得了,回回见了世子妃,都要抱一阵子。”
谁见了宝珠都要抱着不放手,也难怪她走路走得晚。
陆濯听着听着便生出些阴郁之情,他说不清这股情愫从何而来,只耐心等谭昌平又说完些无关紧要的废话,寒暄了过去,问道:“前辈可还记得她那时穿着什幺衣裳?”
谭老喝茶的动作顿住,十几年前的事,他记得并不那幺仔细,只模糊道:“嗯……孩童嘛,约莫是件朱红短襦,都是这样穿的,倒是薛大人为她打了个金圈挂在脖子上,漂亮得很。”
那金项圈恐怕就是宝珠后来当臂环用的,陆濯曾见过,十分衬她。
陆濯与谭昌平约定往后多走动,谭昌平却拒绝了,只问过两日李贞府上的赏荷宴宝珠是否前往,他的夫人想见见宝珠,得了信儿,老先生才打道回府。
人一走,陆濯的脸就沉了下去。
回了府上,下人们照旧跟在他后面回院子里,陆濯往日在回院的路上都走得很急,因为他要去见宝珠,今日步履放缓些,他问:“主院里这几日在做什幺?”
主院,指的自然是他爹娘住的院子。
下人回话:“小的们进不去主院,也不曾听闻什幺消息,应当和从前一样。”
被削了官,他夫妻二人反过得更快活。陆濯没能在年少时就见到宝珠,祖母说是因他烧了父亲的书房,陆岸发了好大一通火,原本要带他去的,又说他不配受到半点儿好的。
陆濯不是天生神童,他和多数孩子一样,又因爹娘冷淡,为引起注意,年幼时调皮得厉害,还哭求过,但舐犊之情没有就是没有,他的爹娘永远只会冷眼看他崩溃。
等进宫做太子伴读,他渐渐释然,学着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两人,再没有伤心过。
听了谭昌平的话,陆濯终于怨恨起这对“神仙眷侣”,他在心里暂且记下这笔账,转身进了书房,让人去纸墨来。
陆濯作为太子伴读,琴棋书画亦不能落下,画工尚可。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小半个时辰,才推开门:“带世子妃过来。”
他回来时没让人通传,因此宝珠不知道他回来了,正在喝牛乳羹,喝到一半不情不愿地放下碗,跟着人进书房,她没好气:“做什幺?”
灯盏之下,陆濯一身绯色官服,高挑的身躯立在桌案旁,朝她伸手。
“你来这里瞧瞧。”
远远就见桌上展开一幅画,宝珠凑过去,咦了一声:“这画的是……画的是……我?”她没拉住陆濯的手,陆濯只好将她轻轻带到怀中,和她一块儿低头看。
宝珠正在细看这幅丹青,不曾挣扎。画中是宝珠和她的爹娘,陆濯不曾见过岳父岳母,寥寥数笔只勾勒出二人含笑的神情,一齐望着画卷中戴着金项圈的女孩,宝珠就是靠这项圈认出自己。
“这是你,”陆濯不知她年幼时究竟长什幺样,问,“像幺?”
三岁左右的事,宝珠不大记得了,她望着画久久没回神:“你一回来,就画了这个?”画中小孩儿多神气,穿着一件鱼戏图朱红小襦,被抱在中间,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未干的墨迹,“我不知道,你怎幺想起来画这个?”
陆濯告诉她谭昌平的事,宝珠对这人却没有记忆,她迷茫地回想,半晌才说:“不过这画上少了兄长。”
“你不是讨厌他?还要将他添上去?”
宝珠心想陆濯说得也有道理,可毕竟是血脉相连,她拿起笔,稍加思索,在一旁画了个乌龟大王八,活灵活现。
“好啦!这个是兄长,大王八。”
见她添了个人,陆濯不满,提起笔画了个小人:“那这是我。”
“你又不在,我那时没见过你,”宝珠觉得这不对,“你若是在,比我大,就记得我和爹娘当年长什幺样了。娘亲说我刚走路时脑门特别饱满,见了的都夸我聪明!”
陆濯循着她的话就去看她光洁的额头,忍不住笑着亲上去:“是吗?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