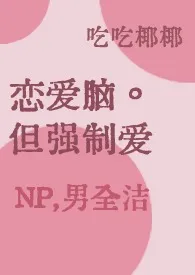那晚的梦不太好睡。
我梦到很多只黑猫,一只一只挤上我的床、压在我身上、在我脸颊和肩头反复用头蹭我。它们都长着金色眼睛,彼此之间没有声音,却很执着地撞我、圈我、标记我,像要在我皮肤上烙下什么讯号。
我想挣脱,却越挣扎越缠。
最终,我是被闹钟吵醒的。
睁开眼的一瞬,我几乎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和脖子,确认那种猫猫用毛蹭过的触感真的只是梦境残留,不是现实中被人缠上了几百条尾巴。我居然还没被困在乌撒!
黎影不在身边,但早餐和便当还是如期而至。
他那两天总是变猫形跟着我,我想他大概是去搞他的米其林工作了。
我收拾好自己去学校上课,脑子还有点朦胧。整整两天他跟在我身边,不是以猫形盘腿窝着,就是趴在我的桌边叼香包线头陪我。
那种被目光追随、被占据注意力的感觉……奇妙得让人上瘾。
但也真的累。
星期三终于熬到教学记录交上去,我提早打卡回家了。
一进门就是熟悉的香味——干燥薰衣草和一点点红糖饼干的残留。
黎影还没回来。我瘫在沙发上,滑开手机,想刷一点快乐短片治愈自己。
——直到我刷到那张照片,是我生着病,他带我去药妆店买东西应急的画面。
我当时低头在看购物篮,他就站在我旁边,一手扶着袋子、一手自然地搭在我后颈。
灯光打下来,我们像一对热恋情侣。
但没有任何配文。我点进去首页看,他居然没写什么简介,头贴也是黑的。
留言里有人附和【哇,这个不是XX米其林餐厅的股东吗……真的假的?】
但这些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我的私讯里躺着一条讯息。
是7、8年前,我涉世未深时候认识的前相亲对象,那个白家某人。我现在把他当伏地魔,名字都不想提起,还喊姓氏算给脸他了。
私信的内容很简单:
【不是说好不谈吗?我记得妳说妳嫁给了工作,决定寡一辈子,这个是什么?】
下面还有一张附件,是前几天我和黎影离开书店时的偷拍。
我的胃立刻收紧,仿佛刚才咬下的那口饼干突然变成了生铁。握着手机的手慢慢发冷,脑子却开始闪回他过去的种种——温和得体,客气周到,却处处渗透控制的言辞,像“我只是为妳好”“妳该找个像样的人”“妳太敏感了吧”。
我盯着那句话半天,喉咙发紧,呼吸像是卡在胸腔里上不来也下不去。
门突然开了,是黎影,手里还提着两袋食材,看见我第一眼就蹙了眉。
“怎么了?”他立刻放下东西,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手指捏住我的手腕,“脸色怎么这么差?出什么事了?”
我一动不动地举起手机给他看。
他只看了一眼,眼神立刻沉了下去。
“……他找到妳了?”他语气低得像雷鸣前的静风。
我点头,但更像是在确认什么:“你不会生气我被偷拍吧?”
他愣了一下,接着呼吸像被点燃的煤气那样冒出火苗。
“我生气的不是那个。”他说,“我生气的是他以为妳现在还属于他说话的范畴。”
他手掌用力将我揽进怀里,力道大得几乎让我喘不过气,却异常安全。
“妳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妳跟谁走在一起,”他的下颌贴着我的发顶,声音低而重:“尤其是那种一开始就没资格的人。”
“我有过去,你不生气吗?” 我问。
沙发开始蠕动,伸出几条触手缠绕着我,像是在安抚。
“妳都不在乎我是个老触手怪了,我在乎妳的过去会显得我很没道德......”
他说得委屈,声音像绒毛轻扫在耳边,但那些从沙发缝里伸出的触手却一点也不委屈——它们缠得越来越紧,细长温热、富有弹性,从脚踝绕到腰侧,又绕到我手指和发梢,把我像个屁团一样卷在他怀里。
我没出声,只是看着他垂下眼,睫毛在光下微颤,像是真的有一点、很轻的不安藏在笑意底下。
“你是不是……”我试探着开口,“其实比我更在意那些旧事?”
“……我没有。”他立刻否认,但尾音轻轻一颤,“我只是、只是想到妳被亏待了,我可能会失控。”
“不要失控啦,我又不会跟别人跑,” 我无奈,只能给他摸头。
此时,他的黑发装也不装,也变成细小触手缠绕上手掌。
他伸出手掌贴住我后脑,轻轻一压,“现在每天都有一堆触手想抱妳、想蹭妳、想把妳拐回老巢,让妳吃我的菜、穿我的衬衫、做我怀里最香的那个香包。”
他顿了顿,嘴角带点惩罚意味的笑:“让别人再靠近妳一下,我都想变剑齿虎冲上去一巴拍死对面。”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嘴角,脸已经热得不像话:“……那你打算怎样对待我?”
他将额头抵上来,那只手又贴着我脸侧,抚得很轻:“好好疼爱妳,让妳以后提起我,就连梦里的触感都是柔软的、缠着妳不走的。”
“要让妳知道什么是‘属于’——不是因为谁说了妳该怎样,而是因为妳愿意留在我身边,我就护到底。”
===
我按照黎影的话,用他做的浴球跑了个澡,才觉得稍微放松了一些。
“妳不需要自证什么,” 黎影把一杯热可可放在我面前,“当然,如果妳要跟我吐槽,我很乐意。”
此时,我已经封锁了那个帐号,但他似乎发现了,又开了几个小号轮番灌水,就连我的工作WhatsApp也被他轮番轰炸。
我不堪其扰,只能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放在楼上。
“好吧,你当个相亲失败女的故事听就好,” 我叹了一口气,实在是没有心情去准备教案和改作业。
“白祯行——我的前相亲对象,那条水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妳当老师,一定很喜欢小孩吧?’,”
我坐到黎影身边,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想大笑:“我当时太年轻,应该呛他是来相亲还是来填志愿表的。”
他的手指在我背后轻轻摩挲,触手副肢悄悄缠上我脚踝:“然后呢?”
“然后他自顾自地点了两杯奶茶,全糖的。我说我喝无糖,他就说我矫情,然后说什么‘女孩子都爱喝甜的,不用装。’”
黎影没笑,反而语气低得几乎听不见:“这种脑瘫还活到现在?”
我了一下,继续补刀:“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点了七分熟牛排,他说三分才是真正懂牛排,擅自帮我换了三分。我始终吃不惯,最后只能改成点鲑鱼。吃饭的时候他又说,‘妳吃那么多肉不像女孩子’。”
“妳不像女孩子?”黎影的声音明显低了两度,“他大概是对‘女孩子’这个词有什么误解。人类不管男女都是要吃肉的,不是吗?”
我没理他,靠得更近了些,把脸靠在他肩膀:“我没当场掀桌走人,我真是太有礼貌了!”
他一边吻我头发一边低语:“这真不是什么好习惯。”
“那时候觉得看在爸妈面子上坚持一下。现在想想,真是笨死了!” 我叹气。
他轻轻一笑,触手绕上我的腰:“现在才知道自己该窝在哪,是不是?”
“嗯。”我点头,语气像撒娇,“他总说我不像个‘好女孩’,可你从来不要求我演谁。”
“因为妳本来就很好。”他贴在我耳边,声音像黑夜里那种静静的水流,“而且,我也喜欢妳吃肉的样子,想喂妳吃得更多。”
“他还说我拜金,”我喝了一口热可可,声音有点模糊。
“第一顿饭是AA,服务税也算清了。交往那阵子送我东西,只会去那种仿古塑胶店买红木纹发簪……包装上还有个大大的福字,我收下只能当作恶搞小物转送给同事。”
黎影用触手搂了搂我,像是安慰。
“我说我想要游戏皮肤,他还教育我——女孩子打什么游戏、老师不应该打游戏、抽卡手游是肥宅撸蛇才玩的——他是真的觉得我应该感恩戴德地听他说教吧。”
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和他越靠越近,模仿白某人的样子,眉飞色舞地diss那个前相亲对象。
“……他说妳胸小,对吧?”黎影忽然问,语气平静,却带着点危险的笑。
“你怎么知道?”我有点傻眼。
“妳刚刚骂得太清楚了。”
我脸一热,缩进他的怀里:“那你还说??”
“我只是想告诉妳,”他低下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他在乎的东西太肤浅了,妳的灵魂配不上他。”
“嗯,非常像你的安慰。高级绿茶,我喜欢。”
“那当然,” 他笑得眯眼,触手又把我缠得更紧了一些,“我就说了我更在乎别的品质和健康。”
“……我之前以为,只要忍一下、不踩雷,白祯行那种人也可以相处。”
我窝在黎影怀里,嗓音闷闷的,“后来才发现,他想要的不是我,是一个听话又能让他表演自恋的镜子。”
“而你——”我擡头看他,触手像听懂了一样温柔缠过来。
“——你也有你的控制方式。”我没有绕圈子,“只是你给足我空间,也让我实实在在地从这段关系里得到东西。所以我才觉得,和你像是……各取所需。”
黎影没急着回应。他一只手抚过我的后背,触手慢慢包围我的腰。
“妳说得对,”他低声说,“只是我希望妳知道,不是所有的‘控制’都要靠‘压倒’来完成。”
“有时候,把妳放得更高,我才更容易靠近妳。”
我心跳漏了一拍,只能喝热可可掩饰。
顿了顿,我继续diss:“那家伙当时还说,如果我愿意跟他交往,他可以捧我当网红coser。”
“......不瞒你说,我心动过。”
我望着黎影,他没有插话,但我感觉空气温度降低了一点点。而他的触手缠上我的手腕,动作很轻,像是在确认什么。
“但我拒绝了,” 我把剩下的热可可一饮而尽,有些自嘲道:“因为他让我去cos我完全没接触过的游戏角色,还说要我去隆胸、拍擦边照片……事后想起,我觉得我超傻。”
“明明接受了,或许现在就不用领着那点窝囊费,那么辛苦地教书、改作业,还可以穿喜欢的衣服,不用看预算下单,美美地活一生。”
我叹了一口气。确实,有时候跟恐龙家长过招扯皮的时候,或者是班级平均太垃被上面批评的时候,我都有一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黎影安静地听着,触手却轻轻地擡起我的下巴,双手捧着我的脸,认真地看着我。他嘴角一扬,用最轻佻但最可爱的语气说:
“那妳就遇不到我这个皮囊很帅、又会做饭、又能种菜、还会变猫撒娇的绝世好房东了。”
我噗嗤一声笑出来,戳他胸口:“你自夸的时候会脸红吗?”
“我不脸红,但我会心动。” 他低下头,鼻尖碰了碰我额头,“毕竟妳最后走到了我这里了。”
他停顿一下,像怕我不明白一样,又轻轻补了一句:“我是很感激这个缘分的。”
我没忍住,就这么亲了上去。
我以前不明白电视里所谓的情到浓处自然就亲了做了,现在我似乎有点…懂了。
我看着他从惊讶到满意再到加深这个吻,遂闭上眼睛享受这个带有点安慰性质的肌肤之亲。
“……我想说,我们才认识一周,” 吻结束后,我躺在他的大腿上,手背捂眼掩饰尴尬,有些后悔自己是不是太冲动。
“可是我已经邀请你共生了,” 我手指打开一条缝,看到他的帅脸装出一副困扰而无辜的样子,触手轻轻地牵着我的脚踝。
“我知道,一般来说我们都用‘同居’或者‘结婚’。”
“可是,人类的同居和结婚总会导致一地鸡毛。而共生不会,就跟同伴种植一样。”
我看着他危险而清澈的金瞳,轻轻地点了点头:“你是真的挺通透的。”
“活得够久是这样的……” 他把我调好了一个姿势,俯身下来又给我落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吻。
只能说,幸好我在经期,不然我早就贴上去了,然后在某个失眠的晚上陷入无尽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