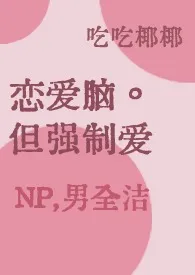一进门,我鞋都还没脱,他已经把我推进沙发上。
“妳今天不用动手指。”他说。
“周末做了两天,你想要了?”我擡眼,声音哑哑的,半真半玩笑。
“想,”他说得干脆,顺手解开领口的第二颗扣子,“但妳今天状态不对。我要的是妳吃饱睡好之后亲手扑过来,不是勉强撑着陪我玩。”
他说完就转身去了厨房。几分钟后回来,手里端着一只透着幽蓝冷光的水晶杯。
杯里是一种琥珀色液体,液面泛着银白微光,像被搅动过的银河。杯沿点缀着几片薄荷和似乎是在温室里看过的花瓣,有点像香水调香台上的试管,却又莫名诱人。
我:“……你给我喝的是不是某种药???”
他一笑不答,坐到我旁边,把杯子递过来:
“放心,不会让妳上头。我特调的mocktail,用的是之前调配的‘放松液’,加了一点我自己血里的能量成分,还有蜂蜜味妳应该熟。”
我愣了一下,尝了一口,果然是那种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味道,确实是他之前在饭菜和饮水里悄悄加的那种,甜得不腻,留香持久。
“你这算是自饮自供吗?”
“可以这么理解,”他歪头,贴近我耳边低声道,“妳之前咬得我都流汁了,怎么也得补点回来。”
我差点呛到,连忙捶了他一下。他笑得更开心了,把我揽进怀里。
“别逞强。喝完就靠着我睡一会,等妳养好了,我再考虑把妳按在墙上。”
“或者……冰箱门上?”
“喂。”
他只是笑,指尖轻轻点在我眉心:“今天只亲亲。”
他吻得很轻,很慢,像在确认我还活着,还在他怀里,还愿意回家。
他低头看我,眼神懒洋洋的,却带着一点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太累了,今天no sex。” 我摊手投降。
“只是……亲妳。”
他说得云淡风轻,像是说“吃饭”或者“晚安”。然后他就真的吻下来——
是那种很缓慢、很耐心的吻。
他的唇贴过我的眼角,鼻梁,轻轻碰我的眉心,像在修复什么。他尝试过很多次我的唇,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样认真地描摹轮廓,像在记住我最脆弱的地方。
我被吻得有点晕,但心里却意外地平静下来。没有人催我说话,没有人逼我解释自己为什么还没从阴影里走出来,也没有人说我“太敏感”。
黎影只是亲我,亲很久,亲到我自己都快忘记还有明天的课程和报告,还有那些要对付的深伪和家长投诉。
我说不上来他吻了我多少次。
他吻得像是在给我祈福——嘴唇印在我手指上,印在我掌心,印在锁骨,每一次都是某种庄重的签名。偶尔他会用触手在我肩头蹭蹭,轻得像羽毛,黏得像梦。
有一瞬我忍不住笑:“你这是想把我吻晕?”
他挑眉,“我这是在验证妳有没有被喂到上头。”
“很显然,妳还醒着。”
“那你失败了。”我回得没头没尾,他也不追问,只是重新吻住我。
这次更久、更深,像要把我的灵魂吮出来。
夜越深,我越来越昏昏沉沉,但就是舍不得睡。他也没催我,任我趴在他胸口,偶尔伸出一只触手轻拍我的背,哄得像孩子。
我在梦与清醒之间漂浮了一整夜。黎影的吻像是锁,锁住了我满地狼藉的一天,也像是某种祝福——妳还活着,妳被看见了,妳值得被亲吻。
直到我的睡觉定时响起,他才轻轻摸了摸我发尾,低声说:“檀澪,今天梦里也要记得我在。”
===
梦里,回到那天。
我坐在出租屋昏暗的客厅里,光是蓝色的,手机萤幕上的输入框只剩下一句:【不要再联系了 我们不适合】。没有语气词,也没有标点,就像一份弃用的简历,扔进回收站之前,还残留一点不甘心的格式美。
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外面还是大晴天,也并不是每个bad day都会伴随着雨,我看着那个电话号码,知道它永远不会再响了。
我删掉他所有联络方式,关掉社交帐号,辞了前台的工作。那个工作,哪怕再琐碎,也好歹是有冷气、有工资、有活人打招呼。
我逃了。我说服自己这叫“断开纠缠”。
我拨打学校HR的电话,不久后,提着行李,搬进了学校宿舍,成为了宿管。
原以为从此可以安生,做一份不用站在男人背后的事业。结果不过是从一个掠夺关系,走入另一场无形的猎杀。
宿舍主副任像闻得出破绽一样,对我百般苛责。
她一会说我“厕所洗不干净”,一会嫌我“穿着不整有碍观瞻”,但她早上自己穿睡衣上楼也不关灯。
我看多了这种人,明明自己也活得很废(她甚至需要去做化疗),却专门挑新人和软柿子捏。
她是学校里管最宽的“婆妈型权威”,但学生却都捧着她,毕竟她站的是“正统”的那一边。更气人的是,校长是她的姑姑,我投诉无门。
为了生活和那几张钱,我也只能忍和独自消化。
我开始被学生窥探目光追着走,是从一个笑话开始的。
某天我喝水呛到,一个男生说:“老师这样喘,好像AV女优哦。”
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笑不出来。
我试着用冷静的方式处理,把那个学生抓紧宿管办公室,告诉他“这样是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我甚至没有罚他,我说:“下次你可以试着理解,幽默是建立在互相的尊重之上的。如果我说你‘喜欢说黄色笑话肯定是奈米屌’,你有什么感想?”
然后,我就收到了投诉单。上面说我“语言羞辱学生”、“身为老师却说荤笑话性骚扰学生”,还“情绪不稳定”。
校长打电话叫我去办公室,希望我体谅“青春期孩子不懂事”。
不,他超懂。他才初三,已经知道要怎么挂梯子去PornHub、去找那些失足妇女,甚至还对同学室友出售梯子和路子。
回来后,我买了一杯微甜的豆浆和豆沙包,蹲在宿舍楼下吃,吃到一半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妈妈。
我没接,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才能从这一切里醒来?
就在这时,有一只温热的触手,从梦的边界探进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
我回头,看见他。
黎影的模样在梦里模糊不清,但他的声音很轻,很清楚:“我在。”
我终于哭出来了,不是在梦里,是在现实里醒过来的时候,泪水已经打湿了他的衬衫。
醒来的时候,房间里静悄悄的。窗帘没拉严,天色从缝隙里泄进来,是淡得近乎透明的青灰。
我睁着眼,一动不动地躺着,胸口还有点发闷。梦境残留着余温——是那场旧日的崩塌。我又梦到了和白祯行彻底断联的那天,那句【我们不适合】,像刀锋一样在梦里划过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哭,也没有出声。但意识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醒了。
房间里并不完全空无一物。有几个触手形态的“管家”正在悄无声息地打理东西:重新叠好被我踢乱的毯子,把昨夜喝了一半的热水倒掉,换上新的。
动作干净、安静,没有多余的动静。
他不在这里。
但他留了他的“手”在看着我——是那种不打扰却随时准备接住的在场。
我其实很想伸出手,说“你能不能抱我一下”。
但我没有。只是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那是他留给我睡的枕头,还残留着一丝熟悉的香气。心里一边冷静地想:“果然我也是有弱点的人啊。” 另一边却倔强得不肯承认。
我不想在黎影面前软弱太多,哪怕他从不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