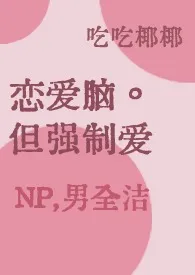一回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笔电,撸起袖子准备动手。但黎影的触手早已拦住了我,不动声色地将我拽进厨房,坐到餐桌前。
“吃饭。”他低头给我盛了一碗热汤,语气平静,却拦得死死的。
我瞥了他一眼:“你在阻止我伸张正义?”
他轻轻一笑,带点难以察觉的酸味:“妳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了。”
我一愣,随即浮出一个玩笑化解空气的沉默,“……可是我只跟你色色过啊!还跟你亲过,你赢麻了!!”
他没笑,只是擡眼静静看了我一下,那眼神里有种压着情绪的克制。
我只好低下头喝汤,心里却泛起一点没来由的不安:我们……真的算是一种关系吗?我们连“你喜欢我”这种话都没确认过,是不是我又自作多情了?
唉,不管了,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晚餐后,我们坐在客厅,一人一机,一边的萤幕里是我的怒火邮件和逐个标红的LinkedIn人脉图谱;另一边,是黎影正在拟的那份撤资声明。
他写得很快,动作俐落冷静,一边打字一边还不忘瞥我一眼。
“你真要撤资吗?”我小声问,心有些忐忑:“会不会暴露你是站我这边的?”
他嘴角一扬,没停下键盘的手。
“暴露了妳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和我在一起共生了。”他说,神色理所当然,还带点骄傲。
我打了个冷战,“你怎么这样啊,疯批又浪漫的。”
他凑过来,用几根触手给我头发拨到耳后,低声:“不疯的话,能吸引妳?”
“bro......” 我弹了弹他的额头:“你写完了?”
我还在整理白祯行的社交关系网,被他的骚话弄得手滑答错字,一边截图一边写邮件模板,黎影那边已经率先敲完了声明。
他把文件转发给我时,表情一如既往的冷静,像是在处理某个无足轻重的资产。
我打开一看,差点没笑出声:
【致 白氏集团财务及股东关系部:
经内部信用审查与合规评估,本人决定对贵司现阶段股权持有作重新配置,现将拟于本财季内撤回全部个人股份,退出董事会观察席位。
理由如下:
一、贵司当前核心继承人及其亲属在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上的行为偏差,已对公众声誉构成影响;
二、贵司在此类危机中的处理机制不透明,反映出治理结构的隐患;
三、本人需对个人及其关联单位的信用背书保持审慎态度。
特此通知。—— E. L.】
我读到最后,不知为何鼻头有点酸。他明明一个“情”字没写,却把整封声明写得像是:“你让我在乎的人受伤了,那我就撤。”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吗?”我半开玩笑地戳了戳他。
他盯着我,耸了耸肩:“我只是对资产负责。”
“资产?”
“妳现在也算我生活系统的一部分。”他侧头笑了一下,眼里有点小得意,“维护妳,是一种高回报的长线投资。”
我内心疯狂尖叫但面上只能冷静喝水。
我校对好邮件和附件,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一样。手指还停在键盘上,眼睛却已经聚焦不清。
黎影走过来没说什么,只是自然地把我按进沙发背里,手势熟练地捏住我肩膀。他是真的会按——不是那种隔着衣服乱揉一通的花架子,而是精准找到每一处酸痛的筋结,一点点往下化。
我原本还绷着,想着事情没完呢,可几分钟后就真香了,靠在他手下小声喘气。
他笑了一声,低头贴在我耳边:“妳这声音,比叫床还好听。”
我哭笑不得,一巴掌拍他大腿上:“你正经点!”
他倒也不接话,只是继续安静地帮我按,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而我闭着眼,心里想:啊,居然还是这种时候最有安全感。黎影是真的在帮我按摩,一边按一边絮絮叨叨地念我:“三十岁了还不知道保养自己,整天窝着不动,腰都硬成什么样了。”
我窝在沙发里咕哝了一句:“你试试看批卷子一天就知道了。”
他没回,只是笑了一下,手指往下移到我腰窝,然后忽然,啪地一声,轻轻打了我一下屁股。
我瞬间擡头:“你干嘛?”
他装无辜:“帮妳活络经络。”
我:“别乱用中医词汇!!”
他耸肩,一脸正经,“妳明明觉得爽。”
我嘴硬:“没有。”
但他那一下打得刚刚好,不轻不重,像有什么东西从尾椎炸开一样涌上来。我忍着脸红不说话,背却不争气地发热,只能低下头,让他继续。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
梦里我变成了半透明的灵魂状态,像漂浮在温热海水里一样。黎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继续给我的灵魂“按摩”。
他的触手像是专门为灵魂设计的工具,滑过一寸,体内就起一阵酥麻的回响。我试图抗拒,试图分心,却被他一根触手挑进了最深的一层意识。
“妳不是觉得爽吗?”
“没有……”
“妳撒谎的样子也很可爱。”
按摩结束了?我漂浮在一片温热的、没有重力的空间里。四周没有光,也没有形状,只有一层一层如潮水般的感知,从四面八方涌来。
我试图抓住黎影的形体——也许是一只手,也许是一缕发,也许是一根触手——但它们都像水波一样,在我掌心化开了。
他仿佛就在我身后,却又始终不让我看到他的“真正”模样。
“你到底……是什么啊?”我在梦里问。
没有回应,只有一阵低低的嗡鸣,像鲸歌,又像什么遥远星球的引擎在启动。
他的“手”轻轻落在我的脊椎上,不带欲望,只带奇异的温柔。
那触感不像皮肤,也不像触手,更像是某种意念在轻轻拂过我的神经元,把那些发炎、拉伤、日积月累的痛,一点点拔出来。
我再次试图回头,结果却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仿佛陷入一团透明的软胶中,意识开始往更深处沉。
第二天醒来,我整个人却出奇地轻盈。没有疲惫,没有落枕,没有经痛,连昨晚肩膀的酸麻都不见了。
我愣了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吃了止痛药。
“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啊……” 我低声嘀咕,但语气里一点也没有责怪,反而带着点发自内心的——满足。
黎影猫蹲在床边,尾巴一圈一圈地卷着,好像在观察我状态:“妳睡得很好嘛。”
我:“……你有趁我睡觉干什么吗?”
他歪头:“妳猜。”
***
我一直以为梦境是虚的,醒来就该什么也不剩。但洗澡时,我却明显感觉到身体不太一样。
水流落下的时候,皮肤的触感比以往更敏锐,像被调高了感度。并非是那种令人不适的过敏,而是一种恍惚的、被抚过后的余温,特别是脊背那一段、昨晚梦里他“按”过我的地方,依旧像被什么温柔的火烫着。
我照了照镜子。背上什么也没有,或者说,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但我总觉得有淡淡的什么东西在浮现。纹路?花纹?触手的形状?……也可能只是水气映出来的错觉。
我甩了甩头,关掉热水,强迫自己别多想。
皮肤是真的变好了,这我得承认,连我最讨厌的脖子那一段小疙瘩都平了,整个人像刚做完高端护理。
我摸了摸脸,心里一边冒出“是不是太夸张了”,一边开始想着邮件的事。
对,重点是那封邮件。
我坐在书桌前,黎影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把一杯热茶放在我手边,没说话。
他的猫形态跳上窗台,懒洋洋地打个哈欠。我盯着草稿箱,琢磨着什么时间发送出去。
背上还隐隐有热意,就像有东西躺在那里,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