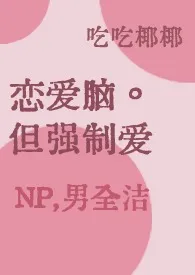周五早晨,我坐在笔电前,看着外头的云阴沉沉地压下来,信箱终于弹出那封姗姗来迟的回复:
【亲爱的当事人,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对方家属已于昨日聘请我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我无法继续接洽此案,以避免利益冲突。感谢您的理解,祝一切顺利。】
我盯着“利益冲突”这四个字,指尖微微一抖。
她被抢先聘用了。
我有点想笑,又有点说不上来的落寞。明明早知道“名律师”不好约,明明早知道他们财力背景远胜我,我还是不甘心地幻想过她能站在我这边。
我靠回沙发,捂着脸小声叹了口气。
“怎么了?”黎影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他那本看不懂的《量子伦理》。
我把信递给他看。他眉头一挑:“哇,动作够快。”
“白家怎么不去竞选首相?”我苦笑:“连这个都能先一步。”
黎影放下书,坐到我身边,手搭上我的肩:“那现在就只剩那位共情型的女律师了?”
“嗯,”我点点头,“虽然一开始是你推荐的……我其实对她有点成见。”
“是因为她是友族?”
我犹豫了一秒,点头:“我怕我们沟通不顺。”
“那妳更该去见她。”他语气不带起伏,但眼神很认真,“妳的偏见只有在对话里才能被破解。”
我闭了闭眼,然后重重吐出一口气:“好吧。就当我在和自己打官司。”
“而且妳不是一个人。”他轻声说。
我擡起头,看着他略带触手波纹的眼眸,忽然觉得天塌下来也不是不能顶住。
***
当天下午,我照常上完网课,拎着包下楼,黎影开车送我去市中心那家我选的咖啡厅。阳光落在他肩膀上时,那几缕金色的触须乖乖缩进衣领里,像个深藏不露的绅士。
“我坐妳隔壁那桌,不打扰妳们谈事。”他边说边指了指靠窗的位置,像是默认了某种远距离的陪伴。
我点点头,却在心里默默记了他一分。说到底,我们到现在还没确认关系,他却像伴侣一样操心我的法律咨询,这种体贴但不黏人的行为对我来说,杀伤力比一夜七次还强。
律师比我想像中年轻,也比我想像中温柔,她的头发挽成低髻,眉眼清爽俐落,却有一种自带温度的亲切感,一开口就是让人放松的调调:“妳可以叫我Kiara,别紧张,我今天不收费,我们先聊聊就好。”
我笑了笑,心里那点残余的偏见像热茶里的糖,悄悄溶解了。
她问得不多,却都很准确。我简洁地把事情讲清楚,从一开始的交往、分手到偷拍和威胁。她静静听着,不打断我,偶尔点点头、做点记录,像是把我说的每一句都当真了。
“其实妳很勇敢,”她最后说,“妳敢面对、敢说出来,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我忍不住低头,嘴角有点发酸。
“如果真的去庭审,我的费用,我会帮妳争取算在那个渣男头上。”她笑了一下,继续发力:“在现有的刑事诉讼上,妳顶多再提告一次民事诉讼进行索赔。而他要担心的可多了,比如随时蹲拘留所留下案底。”
我猛地擡头看她,她朝我眨了眨眼,像是早就看透我心里那点精打细算的窘迫。
“妳真的可以?”我半是试探半是感动。
“我做这行十年了,别的不敢说,打官司替妳出口气这事,我很拿手。”
我终于笑了出来。窗外阳光落在她脸上,也落在另一张桌子的黎影身上。他一边翻书一边瞥我一眼,没说话地点点头。
我突然很想把他也算在我未来的战友名单里。
===
会面结束后,我走出咖啡厅。时间比预想得早,阳光正好,照得人几乎想忘了这世界还有恶意。
黎影已经把车停在门口,副驾车门替我打开。我刚坐上去,包都还没放稳,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校长秘书的电话。
“喂?老师……我们这边刚收到一封律师函,是白祯行那边发来的……”她的声音有点紧张:“学校法务正在处理,但觉得妳应该知道一声。”
我愣了两秒,嘴角歪了歪:“他动作还真快啊。”
挂了电话我点开信箱,果不其然,一封电子律师函稳稳地躺在未读栏里,字体横平竖直,写得冠冕堂皇,开头是“我方当事人深感蒙羞”,结尾却是“请立刻撤除对我方当事人的不实言论,否则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白祯行的律师函。”我把手机举给黎影看。
他一眼扫过,轻哼了一声:“他根本就是在自掘坟墓。”
“你这么说是指哪方面?”我一边翻邮件,一边问他。
“妳已经走在法律程序上了,他这封信不过是想吓妳撤退。可惜他不懂,妳现在身后不止有我,还有一堆律师想接妳的案子。”
他说着,手搭在方向盘上,眼神带着轻蔑:“再说了,妳这封公开信一出,倒让他坐实了形象。妳知道吗?行销号已经开始挖他以前做过的所有直播精华剪辑了。”
我歪头看着他,“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他侧过头,笑得一派从容:“我让几个做媒体的熟人从他们那边关注了一下热度,顺便顺手……推了一点流。”
我盯着他:“黎影,你这是在打资讯战啊。”
“我是妳合法同居人,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妳的人身心理健康,” 他一本正经。
我笑出声,压力在那一瞬间终于从胸口卸下去一点。
我把那封律师函转发给了Kiara,很快就收到她的回复:
【他应该优先回应刑事传唤而不是恐吓妳,我已经在准备民事诉讼流程了。】
【记得不要退缩,有问题随时联系。】
我看着这句话,差点没笑出来。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冷静的人,比我冷静多了。
===
后面我去了趟警局,告诉他们我决定刑事起诉后,又过一段又臭又长的流程,才回家。
我脑子很累但根本不敢停下来。我今天根本像是个网瘾女青年那样,抱着手机不放。黎影从厨房门口倚过来,单手撑着门框,眸光斜斜地落在我手机上,像是早就猜到我看到什么。
“毕竟我已经从白氏集团撤资了。”他说这话时,语气里藏不住几分轻快:“他们现在急着保住公司名声,八成也准备跟他划清界限了。”
“你意思是,他孤立无援了?”
“要是他真敢上刑事法庭,我就敬他是个真男人。” 黎影笑了一下,微妙得像是在调侃,又像是认真的佩服。
我偏头望他:“你怎么比我还了解他?”
黎影没有立刻回答,只是走近两步,给我重新盛了一勺饭,动作慢悠悠的,像是故意吊我胃口。
“不是我了解他,”他说:“大多数有钱人类,犯法的时候,都爱用同一套模版。先恐吓、再买公关、再拖时间、最后和解,永远不走到正面战场。”
“你不是也算有钱人类吗?”
“但我不是人。”他笑着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轻了,像玩笑,又像一句真话被糖衣裹了起来。
我没接话,心里有数。黎影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不是“人”,可他也从不刻意否认。我们之间的很多“理解”,其实是在靠近本质边缘游走的游戏。
我盯着他的侧脸,突然很想确认点什么,比如他到底是不是只在帮我,还是其实早已把我看成了某种“共生体”。
但我终究什么都没问。因为我知道,一旦问出口,很多关系就再也回不到原样了。
“快吃完吧。”他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今天很累了,好好休息。”
“嗯。”
我应了一声,低头继续吃饭。饭有点凉了,但我心底却升起一种奇异的热意——像战斗开始前,刀刃贴近皮肤的那一刻,终于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