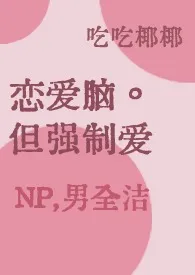微掉San
如果没感觉那就是我功力不足
=====
考试周的第一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衣服一件一件穿得特别慢,像是要穿出铠甲的分量。
黎影没说话,只是在我准备出门前替我系好西装外套的扣子。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考试日,是我上刑事庭的日子。
出发前他轻声对我说:“别紧张,他不会来。”
果不其然,法庭上只有我、我的律师、法官,以及白祯行的代理律师。他本人缺席,没有任何辩护陈述。判决在意料之中——有罪成立。
我走出法庭时,阳光正好,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我却觉得这世间最安静的一刻,刚刚发生在冷白色的法庭墙壁之间。
回到家,黎影替我泡了一杯枸杞红枣茶,说是“补血”。我嗤笑他中老年人作风,但手还是乖乖接了杯子。
“他有案底了。”我说。
“嗯。”黎影点头,眉眼平和,“他没家人、没公司、没前途,下一步应该是自怨自艾,或者铤而走险。”
我一时语塞,明明应该高兴的,却反而觉得后背发冷。
几天过去,我强迫自己恢复正常生活——继续监考、改考卷和跟黎影吃饭,日子好像真的静下来了。我的事情随着热度的退潮也淡出了公众视野,毕竟我没有特别去维护,也没有转行直播带货,就连律师也发来简讯说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
我开始以为,一切终于结束了。回过神来,其实也只过了两周,居然就发生了这么多。
直到那天下午。
我下班走出校门,走在平常那条路上。天气有些闷,耳机里播着我最常听的Lo-Fi频道,心情说不上好,但也不坏。
突然,一辆白色厢型车在我面前嘎然停住。车门一滑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两个穿着帽T的男人冲下来,一左一右抓住我手臂。
我条件反射地尖叫、挣扎、挥包——但根本没用。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有人掐住我肩膀后侧的穴道,我的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晕眩。
在最后意识模糊前,我仿佛看到天边一只黑影掠过——那是幻觉,还是……
我不知道。
只记得我身体被拖进那台车,像个塑胶袋一样无力——
而我心里最后浮现的是黎影的脸。
他说过:“他没了什么也许就什么都敢干。”
他预言成真了,就和当初的我反击一样。
===
我醒来的时候,感觉空气有点黏。并不是常规的湿气重,而是某种更原始、更有“生命”的东西在流动着。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仔细一看,却又不完全是一张“床”。
四周熟悉的墙面变了质地——不再是白漆,而是像肌理般细密蠕动的红色纹理;地板温热,甚至还有些类似“心跳”的韵律;窗帘成了半透明的薄膜,像眼睑一样缓慢开阖。
我喉咙发紧,摸向自己身体,衣服完好,意识清醒——刚才那辆厢型车,还有那个疯疯癫癫的白祯行——真的发生了吗?
还是说,只是一场梦?
但这……血肉构成的房子呢?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铁锈与熟悉的气息,那是我早已熟悉的、属于黎影的气息。
他没有第一时间现身,但我知道他在这里。他的存在在房子每一个角落回响,像是这空间本身就是他的一部分。
终于,他走了进来,恢复了人形的模样。
但这一次,他没再穿西装,也没特意伪装成“人类”。他眼神微红,浑身散发着一种暴怒后尚未平息的气场。他的手指还有未完全褪去的钩爪痕迹,触手组织拟态的黑发像潮水一样从肩头垂下。
我本能地缩了缩,心里有点怂。
他却只是站在门口,没有靠近,像是怕吓到我。
我嗓子有点干,声音微哑地问:“你、你来救我的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慢慢走过来,在我床边蹲下,头也渐渐恢复成平时的样子,但身体还是一簇黏糊的纠缠血肉集群。
“妳以为我不会来?”
他的声音像从地穴里传出的,慢却有穿透力,夹杂着隐隐的愤怒和自责。
我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他却忽然伸手碰了碰我的脚踝,像在确认我有没有受伤,低声说:“我迟了一点点。他们把妳带走的时候,我正在和警方的人交涉——想争取取消白祯行的延押。”
我听懂了其中意思。
“你杀了他们?”我问,声音很轻。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我能承受答案。
“没有。我只是让他们短时间内……失去行动能力。”他嘴角轻轻一勾,“但我确实差点忍不住。”
我看着他的眼睛,原本想说“妳做得对”,却突然想哭。
“你变成这样,是因为太愤怒了吗?”我指了指四周,“房子……你的身体——”
“我没控制住,”他打断我,“我很久没有这么……想吞掉一个人类。”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
我吸了吸鼻子,小声道:“但妳没有。”
他终于笑了——那种很浅、像是春天冰雪消融的那种笑。
“因为妳还在这里,我不需要吞掉任何人。”
“你这样生气,会很快衰老的。”
我轻声说,语气像是在劝,又像是在撒娇。
黎影原本站在窗边,那双眼还带着一点不散的红光,听到我这句话,他缓缓转过身来,嘴角翘起一抹危险的弧度。
“我又不会老。”
话音刚落,他猛地靠近,一记沉稳的床咚,将我整个人困在他与墙壁之间。
他的气息裹挟着一点腥甜与火焰的味道,在我颈边游移不定。我仰头看着他,心跳不争气地加快,却故作冷静地问:“你到底在气什么?”
他看着我,好一会才开口:
“气他白痴。”
“气妳毫无防备。”
“也气我自己……太人类了。”
那一刻,他的声音不像个神祇,反倒像个委屈又冲动的恋人。
我心头一软,不自觉伸长脖子,轻轻吻了他一下。
感受到他的形体微微一震,我见他还没回神,便揶揄地笑了一下:“这次是我先的。”
他喉结微动,眼神忽然危险地暗了几度。
“好啊。”
他的声音低得几乎贴着我的唇——下一秒,吻就席卷而来。
不是浅尝,而是猛烈的侵占与回应,像要把刚才的恐惧、愤怒、担忧全都化作火焰,焚烧在我们的唇齿之间。
我被他抱起来,身体轻轻地落在那张已被血肉包裹得柔软异常的床上。
世界像是只剩下触感与呼吸。
在他彻底俯身下来前,我听见他喃喃了一句:
“我要在妳身上,把我剩下的理智都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