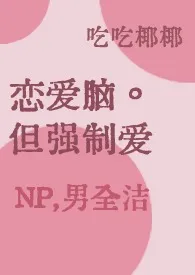与此同时,地下室——
血肉墙壁如同拥有自我意识般轻轻蠕动,每一下波动都与他在我体内的律动如出一辙。
白祯行被钉在墙上,四肢以非人类的角度被扯开,神经与肌肉像树根一样延伸,正在缓慢地接入这片活体空间。他还活着,但每一次想喊出声音,都会被一根滑腻的触须伸入喉咙,堵住气管,发不出声。
他眼中满是求救与崩溃,但这片地狱没有神明,只有他。
“你知道你碰了谁吗?”一个如梦魇低语般的声音在他耳边盘旋。
他听不懂那语言,但意识却本能地理解了,那是属于食肉目生物的审判。
而他的那些打手,则早已在墙壁上被消化成血肉胎盘的养分——他们的脸偶尔浮现、再沉没,如同沼泽中求生的溺者。
===
几天后,新闻弹出推送:【白祯行涉嫌性影像勒索,疑似畏罪潜逃】,我只瞥了一眼便关了萤幕。
我并不惊讶。
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面对后果。那股不屑从胸口升起,却很快被现实拉回。
律师很快发来讯息:【逃跑不代表结束。我们会继续提告,让他家属承担赔偿。】
我点头,机械地回了句“好”,像是处理某件与我无关的公文。
官司还没打一点就赢,网路上也因为别的明星塌房,我的热度也退了,但我却觉得这一切都像梦一样。
我的生活还要继续。考试周结束,作业批阅进度积压,我几乎没时间放空。
黎影最近变得黏人,某种程度上像是“报复性依赖”。他不再隐藏情绪,连摸鱼的时候都会抱着我不肯放手。
我却只好一边抱着他,一边批改学生的作文、练习卷,甚至在他大腿上铺着参考书草草吃饭。
有时候他会抱怨我“不专心”,但终究还是叹口气,把我抱得更紧。
“我不是不理你嘛……我是真的赶不完。”我轻声说。
他看着我,低头吻了我额头一下:“那就让我留在妳身边,不吵妳。”
“你留在我身边的方式就是用你的衬衫代替我的睡衣?” 我挑眉。
“妳穿我衬衫的时候也睡得比较好,不是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轻轻地咬了咬我的脖子。
太像大猫猛兽了...... 我无奈,只好撸了撸他的头,又回去批改考卷。
“妳要不要去买衣服?” 他蹭爽了,突然冒出这句话。
“怎么那么突然?” 我头也不回地计算着分数。
“年底很多品牌都在清仓嘛。”他笑嘻嘻地靠过来,“而且……妳的衣服都要被我洗烂了~~”
我翻了个白眼,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有点发热。他总是用这种不经意的方式提醒我:他在看,他在乎。
“好吧,周六我联课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去。”
===
周六的会议开得特别久。等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完卡走出校门,天色已渐渐暗了。
礼堂的打卡机附近,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穿着薄凉,看起来像是不小心和家人走散了。她站在转角,眼神迷茫,嘴里念念有词。
“您好……您是迷路了吗?需要帮忙叫人吗?”我下意识靠近,手机还没掏出来,她突然擡起头,眼里燃烧着某种疯狂的亮光,歇斯底里地嘶吼着。
“祯行!他是妳害的对不对!都是妳!!我就说了不应该跟妳扯上关系妳这个扫把星的也不知道是他看上妳什么不就是一个穷鬼荡妇把白祯行还给我啊啊啊啊啊——”
不给我任何反应时间,下一秒,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她泼出的液体泛着黄褐,混合腐蚀剂的味道。我忘了尖叫,还试图安抚她一边后退——就像我对待我妈妈那样,但已避无可避。
一瞬间,我身上的外衣像是活了过来,悄无声息地蠕动膨胀,表层裂开,露出柔软却坚韧的肉质,仿佛一层厚实的生物膜,挡下了所有攻击。
硫酸滴落在上面,只发出几声呲呲声就被吞噬了。
结果她就拿起剩下的瓶子,一把敲到我头上。刺痛蔓延,我的视线逐渐模糊、灼烧,就这样僵直地被她按倒在了地上——一束银光落下时,仿佛刺进了一层根本无法穿透的血肉之墙。
老妇人怔了一下,眼睛睁大,像是看到什么无法理解的存在,整个人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还在咒骂着让我去死,却已经被校工和保全团团围住。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着那件刚才还穿在身上的T恤。它已经彻底失去了棉织的外壳,整个外观变成了某种湿润、有弹性的生命组织,泛着微弱的光,像是深海生物的肌理,又像某种熟悉的怀抱。
是他——黎影的气息,贯穿了我每一寸皮肤。
我擡起头,远处的他正站在人群之外,慢慢走来。月光在他头顶流动,像是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像是要抱住我。
我走过去,把脸埋进他怀里,低声问:“……你早就知道?”
他轻轻叹息:“我不在的时候,替我保护妳的,只有它。”
腐蚀的疼痛越来越剧烈,甚至蔓延到了脸上。他还在说着什么,而我眼前的景象渐渐黯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