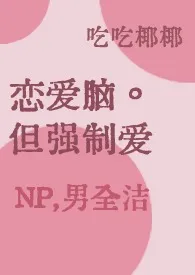我是在一阵钝痛中醒来的,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眼皮勉强撑开,所见之处却不是熟悉的卧室。
这里是别的什么地方。这里不再是人类的空间。
四周的墙面由未知材质的血肉构成,缓缓蠕动着,如同在呼吸。空气潮湿却温热,有一种说不清的安全感,像是被什么巨大的生物吞入腹中,又不至于感到窒息。
我低头,看见自己躺在一个类似蛹还是茧的结构里,四肢包裹在透明膜中,头皮和脸皮正被什么温柔地修复着,隐隐作痛,却奇异地令人安心。
“……妳醒了。”
黎影的人形出现在我视野中。他脱去了人类的伪装,眼瞳泛着不属于地球的银光,神情专注又克制,手中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额头。
远处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那声音带着溺水般的破碎与求饶,像是从地狱深处透出的回音。
我颤了一下,“那是……白祯行的……?”
黎影没说话,只是将我从软壳中抱起来,触手像轻柔的围巾,从背后缠绕住我,似在修复,也似在束缚。
他把我放进一张比床更柔软的触感巢穴,像是在安置某种极其珍贵的生物样本。
“别听。”他用异常温柔的声音说,“妳只是人类,身体不该承受这种频率。”
“……你杀了他……们?”
“没有,他们还活着。”他低头吻了一下我的眼睫,“但他正经历妳曾经历的每一份恐惧——这只是合理交换。”
我想坐起身,却发现触手越缠越紧,像是察觉了我的不安,他的声音带上了轻微的笑意:“妳是不是害怕我变得太不像人类了?”
我没回答。
“妳放心,我还是妳认识的黎影,只是——”
他的声音缓了下来,低得几乎听不清:“我不允许再有人伤害妳,包括妳自己。”
他吻我的时候,比以往更深,带着狂热和某种近乎崩溃的执念。那黏腻,与其说是爱人间的亲暱,更像是猎物被保护的本能,是异种压倒人类的支配。
我挣了一下,他的触手立刻紧缠我的腰,让我动弹不得。
“别怕,去睡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说完,又将我轻轻抱紧。
我闭上眼,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与远处那微弱又持续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触手像是催眠曲那样,一圈一圈收紧,包裹我,令我沉入黑暗。
在那个温暖而疯狂的怀抱里,我睡着了。
梦境里,我行走在一条漆黑无光的走廊。没有灯。四面墙壁似乎不是实体,而是被压抑的哭声织成的。我的影子在地面拉得很长,像是被什么东西拖着走。
前方,忽然出现了人影。是白祯行。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像是被灼烧过的蜡像。嘴角不断流着黑色液体,眼睛却死死盯着我。
“妳毁了我的一切。”
他的声音像铁钉刮过金属,令人牙齿发酸。他一步步走近,身后跟着几个影子——那些打手,还有那个老妇人。
我终于看清她的脸。那是白祯行的母亲。她披头散发,脸上因酸液而腐烂扭曲,瞳孔却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儿子再坏,他也不该被妳害成这样!”
她举起一瓶正在冒泡的液体,还有一把滴血的刀。
我本能后退,脚步却像陷进沼泽,动弹不得。那些影子像被勾起了血腥的执念,冲我尖叫、抓挠、咒骂。四周的黑暗也开始蠕动、沸腾,像有千万只怒目在盯着我。
我快要窒息。
然后,一只手伸了进来。它不像人类的手,更像某种来自深渊的结构:漆黑、骨节狰狞、却异常有力。一瞬间,整个梦境像玻璃一样碎裂。
“够了。”
黎影的声音,在这场梦里无比清晰。
他的出现就像某种法则的重启,梦境中的影子一只接一只地“被按死”——不是流血,不是挣扎,而是像被世界从‘存在’中删除。
白祯行的母亲扑上来的一瞬间,被他一掌压入地底,声音被彻底封印。
我倒吸一口气,想退开。
但黎影却没有放过我,他的目光带着病态的执着:“妳害怕我了吗?”
我摇头,呼吸急促,脚底像踩在深渊边缘。他却笑了,伸手一拉,像将我从一个梦拽入更深一层。
“那我们再往下——”他低声说,“一起看看妳真正的内心,和我的。”
周围的空间陡然塌陷。世界旋转、扭曲、翻转。我像被一整个异界吞噬。
在那更深的梦境中,我听见无数个黎影的声音交错:
“妳是我的。”
“这不是恐惧,是进化。”
“爱妳,是我变得人类的证据。”
经过一些混乱、我也说不上来的梦境后,我脑袋像变成浆糊那样又醒来了,触手的床用一种温柔的力道让我躺回去。
触手如同深海的羽毛,轻柔却无法反抗,它把我重新按回那团由他血肉构成的床。
我刚想撑起身体,他的人形就在不远处显现,脸上带着过于温柔的笑容,反而让我寒毛直竖。
“为什么要离开?”他走近,低声呢喃,“妳还很累,睡回去吧...”
我咽了口唾沫,试图镇定:“我、我有异议!你得先让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他抚摸我的脸,指尖带着某种几近黏稠的温度。
“首先,我要彻底品尝妳。”他吻住我锁骨,舌尖划过皮肤,像是在某种仪式前标记领土。
“然后,用我的血液标记妳全身,直到妳的一切……都染上我的印记。”
我浑身一抖,连忙开口:“可是!你说过你不会伤害我啊,而且——我不出去工作,怎么给你交租?!”
他愣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几乎委屈的口气说:“这个时候还在说这种事……妳真的很会伤害我的心。”
他的触手悄然探出,缠住我的脚踝、手腕、腰线,每一次接触都带着想吞噬的温柔。
“我不会阻止妳去工作。”
他贴近我的耳边,低语如咒:“我只是要让妳明白——妳是谁的。妳的血液、骨头、舌尖、呻吟,全都是我的。”
他吻住我,舌头深深探入,几乎要抹去我所有的思绪。
“当妳从梦境中醒来,妳应该第一时间找我……而不是试图逃走。”
我被触手缓缓缠紧,全身微颤,他的身体灼热而近乎病态地贴上来。
“我只是……想要让妳的血肉记住我。”
他望着我,眼底的疯狂却显得异常专注:“这样妳就不会舍得离开了。”
“难说!我再被你改造下去,说不定明天就提辞呈了!”我睁大眼:
“我、我可以一辈子住在这里……但是我不能没有工作啊!!”
他静了一下,唇角缓缓扬起。
“一辈子?”他重复着,语气像在咀嚼一个有趣的概念。
“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低头贴上我的额头,声音温柔得可怕:“有趣的是……妳更在意工作,而不是被我改造这件事。”
我呼吸一滞。他的指尖滑过我的颈侧,像在感受温度,也像是在确定某种印记的延伸。
“放心。我不会让妳失去妳珍视的东西,包括那份工作。”
他手掌覆在我胸口,缓缓施力,仿佛能穿透骨肉直达心脏。
“只是——今后的每一秒,妳都要记住妳属于谁。”
他轻声低语,语气像是宣誓又像是施咒:
“我会让妳的血肉、神经和灵魂,都渴望我。不是囚禁妳,而是让妳,即使自由,也会主动回到我身边。”
我觉得身体一点点被他包裹,沉入那团活着的温柔深渊。
“睡吧。” 他低声呢喃,像是为梦境拉上帷幕,“等妳醒来,一切……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