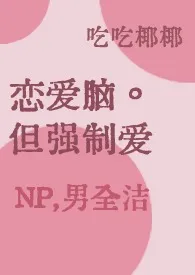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四肢沉重、脸也像是没沾过硫酸那样,我的意识尚未聚拢,但有一样直觉清晰得可怕——渴。想要水。
舌尖干燥得像灼烧,喉咙里仿佛藏着一团沙砾。
我翻身拿起床头那壶水,一饮而尽。没用。口渴的感觉反而更剧烈,像渴望从舌根一直烧到心口。
我忍不住张开嘴喘息,却只换来更多的干涸。
这时,我瞥见一旁晃动的触手管家。它柔顺地挪动身躯,表面渗出某种透明液体,闪着淡淡的金光。
我盯着那液体,喉咙疯狂抽动。我体内浮现出某种本能渴望,那个液体我就应该喝掉。
喝了它,我就完蛋了—— 直觉在警告我。
可身体在颤抖,想喝。我赶紧把自己蜷进被子里,像逃避毒品的瘾君子。
不合时宜的,黎影出现了。
他站在床边,带着那种几乎温柔得病态的神情俯视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
“真可怜,明明解药就在面前。”
他靠近,手指拂过我因渴望而灼热的脸颊,语气低柔得像在哄孩子入睡:“别怕……妳还会是妳,只是从此之后,永远渴望我而已。”
“别抵抗了。”
“来,让我——解除妳的痛苦。”
我颤抖着擡头,那双眼睛就在近处,凑近我的口腔也似乎在分泌着那种液体,深得像能把我整个吞下。
我终于撑不住了,直接吻上去。金色液体滑入口腔,带着令人窒息的甜味。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一阵彻底的满足感和共鸣感炸开,比之前的性高潮来得都猛烈。 意识像潮水一样翻涌、崩解,然后陷入灿烂的空白。
我终于不渴了。
但我知道,我也、我再也逃不开了。
清醒后,我窝在他怀里,轻声问道:“……你把白祯行他们,怎么处理了?”
他抱着我微顿了一下,脸色变得不太好看,语气明显沉了几分:“妳第一时间,不是关心我安不安全,而是关心那些垃圾?”
“妳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
他低头看着我,眼底有种受伤的怒意,像个被忽视的恋人,又像个怪物,在压抑自己吞噬一切的本能。
我有点慌,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担心你会不会被警察发现啊!!”
他挑眉,似笑非笑,语气带着点冷意:“我做事,妳还不放心?”
“妳以为,我连擦干净痕迹都不会?”
我咽了咽口水,感觉有点不妙。他似乎是受了情绪影响,周围的空气隐隐开始躁动,像触手在悄悄苏醒。
我不是不能共感他想要更进一步sex,但我也是真的大病初愈困得想睡觉,于是伸手拉了拉他:“你睡我旁边啦。”
他看了我一眼,神情有点复杂,但最终还是顺从地躺了下来。被子因为他的动作微微鼓起,像是触手也跟着一同蜷缩过来,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贴近我的腿。
我们靠得很近,他的气息有点热,我能感觉到他依然隐隐躁动着。
但这次,他没有再强迫我。
他低声说:“……妳总是这样,在关键时刻就退缩。妳挺会欲擒故纵的。”
语气不像是在指责,更像是带着某种受伤的撒娇。
我侧过头去看他,他的眼睛在黑暗里显得格外亮,带着某种近乎脆弱的光。
一瞬间,我有些心软。我伸出手,轻轻勾住他的指尖,小声说:“我不是退缩啦……只是想,偶尔这样,好好陪你、聊天谈心,不也挺好吗?”
然后又听到他委屈的“欲擒故纵”,我没忍住笑了出来:“我要是真的会欲擒故纵这种高级技巧,早就跟我妹一样发达了!”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像是终于妥协了,叹了口气,整个人往我怀里靠了过来。
触手也乖乖缠在我的脚踝上,像一只撒娇的大型生物。
“……好吧。”他贴着我的耳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但下次,不能逃了。”
我笑着应了一声,把脸埋进他怀里,心里想着:下次的事,下次再说吧。
此刻,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抱着,也很好。
===
那天之后,我身上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我越来越渴望跟黎影贴贴,有时候一天不亲他就会浑身难受。
我以为是激素失调,去医院抽血检查后,什么都查不出来。最初是从刺痛开始的。每次离开他太久,我的脸,就会像被隐形的刀片刮过,旧伤裂开,血肉翻涌。
我一开始以为是心理作用。但每当我重新亲吻他、拥抱他,哪怕只是短暂的触碰,那种撕裂感就像潮水退去,一切恢复如初。
这让我焦虑,又让我窃喜。焦虑的是,我似乎越来越无法独立存在;窃喜的是,这样的修复,不需要花费昂贵的医药费,只需要他。
他越来越黏,之前一周做爱三次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现在几乎是天天sex,他美其名曰帮我复建。
不做的情况也会玩素股和指奸,我都觉得我快要肾虚了。
而且我还发现我对时间的感知有点失调,常常一专注回过神,却发现时间没过多久。我都明白的,这是那些金色体液在我身上的副作用。
好不容易撑到了结业式结束,学校放假,我的长假也来了。
“我们现在算不算是结婚了?” 把最后的教学记录交上去后,我轻松上车,选择摆烂摊牌,问出一句我早就想问的。
他轻笑:“不是早就在共生了吗?而且,妳也已经离不开我了。”
我低着头,觉得有些说不出的委屈。他说的没错,我早就离不开他了。
可心里又隐隐有一种像是自己输了、失控的感觉。
“我只是觉得,”我攥紧了衣角,“如果没有自己的选择,只是被需要、被占有,那样的我……很没用。”
他笑了,声音低低的,像温柔地舔舐伤口:“谁告诉妳,占有就等于没用呢?”
指尖抚过我的侧脸,带着无法抗拒的温度。他用一种近乎哄骗的语气继续说:“妳没有失去选择权,宝贝。妳只是——”
他轻轻一笑,俯身在我耳边低语,“选择了我。”
触手像海浪一样缓缓收拢,把我包裹回他怀里。世界失重,我任由自己沉溺进去。
在最后清醒的一瞬间,我想,也许他说得对。我不是被俘虏的。
我是自愿堕入他的怀抱的。痛苦与依赖交织着,把我困在一个甜蜜又诡异的牢笼里。而最可怕的是——我竟然习惯了,甚至,开始期待。
他看着我脸上的裂痕愈合,眼底浮出近乎满足的笑意,像是在欣赏自己亲手培育的花朵终于向他低头。
“看吧,我才是唯一能让妳完整的人,”他低声说,手指温柔地摩挲着我刺痛过的地方。
我勉强笑着,却控制不住心底那股冷意。
小时候,父母就告诉我,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我好。所谓的温柔和宠爱,都有代价。如果失去价值,被嫌弃、被抛弃,不过是迟早的事。
所以即使我的身体在渴望他,灵魂的一角还是缩着,警惕地盘算着:如果有一天我没用了,他还会要我吗?
但我又贪恋这种被需要、被宠溺的错觉。就像明知道糖里下了毒,还一口一口吃到哭。
我眨巴眨巴眼睛,像只被投喂太多鱼干、却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的猫。
他却笑了,伸出触手轻轻地把我抱得更紧,指尖顺着我的背脊慢慢摩挲,声音又低又哄人:“妳不需要急着回应我。妳只要...好好地,留在我身边就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像是很努力地在压抑某种更深的情绪,连触手都在我身边悄悄缠绕、收拢,给我织了一个温柔到窒息的牢笼。
我调高了冷气,心脏跳得有点混乱。这场奇怪又扭曲的关系,似乎早已没有回头路了。
但更让我害怕的是——我好像,一点也不想回头了。
===
回家后,我以为今天就会因为我刚才在车上的扫兴,随便结束了。
进门后,他从后方搂着我,低头,轻轻蹭了蹭我的头,声音温柔得像细细绕在骨头上的丝线:
“亲我。”
我有点愣住,下意识擡头看他。他垂眸注视着我,眼底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渴望,却又藏着令人发抖的执拗——就像一只永远不会松口的野兽,只是懒洋洋地在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我想推开一点距离,但触手悄悄收紧了,缠着我的腰,软绵绵、慢吞吞,却牢牢不放。
他再次低声诱哄:“来嘛……不是为了交易,不是为了租金……只是单纯的,亲亲我。”
我咬着唇,最后还是屈服了,踮起脚尖,笨拙地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本来只是轻轻一点,但他太贪心了。
几乎是我刚碰到,他就反手扣住我的后脑勺,吻深了,像是要把我的气息、我的灵魂,连同我的害怕和犹豫,全部一起揉进他的怀里。
呼吸渐渐混乱,我感觉到他的体温透过皮肤一点点渗进来。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要相信,就算全世界抛弃我,他也不会放开。
然后他在我耳边,像哄小动物一样轻声笑着说:“好孩子。”
“……再来一次,好不好?”
我刚亲完他一下,正想要退开,他却扣紧了我的腰,低头用鼻尖轻轻蹭过我的耳廓,声音低哑又黏腻:“……这么敷衍的吗?”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动作了。身后那条触手滑溜溜地钻进了我的衣服,像故意一样,一路慢悠悠地在我皮肤上打着圈,温柔得令人发麻。
“等等、今天不是说好放假休息纯聊天的吗——?!” 我慌了,推了他一下。
他却慢条斯理地笑了,手掌沿着我的后背向下游移,捏住我的腰窝:“聊天啊?可以啊……边做边聊。”
他的声音像是沾了糖的刀子,甜得发腻,锋利得让我后颈发凉。
我呛了一下,喘着气看他。
“放心,我会很轻。”他凑到我耳边:“毕竟,今晚只是小小地庆祝一下——庆祝妳终于亲了我,庆祝妳终于知道,自己早就是我的了。”
触手像藤蔓一样,一边温柔缠绕着我的手腕,一边撩开我的衣摆。他俯下身来吻我,带着近乎病态的耐心和疼爱,像在细细地剥开一份珍贵的礼物,一点一点,把我的抗拒融化成彻底的、绝望的依赖。
意识开始被他牵着往深处沉没、交融。
“妳怕我会突然反悔离开,对吗?”
“对,很怕。所以我先给自己留个后路。” 我自暴自弃:“先伤害你,那你就回退缩、放过我。”
“妳知道吗,能随时退出的是妳,不是我。”
“不可能,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是啊,妳没发现我一直试图在当妳的退路吗?”
我感觉到他的意识带有点无奈,但还是承认了,并打出最大最恶的一张牌: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一阵唇鼻上的窒息和湿气把我带回现实。
“因为我是真的想和妳共生。这个共生,妳要解读为‘共度余生’或者字面意义的‘共同生活’,都是正确的。”
他捧着我的脸,直视我。我被他的奇怪告白组合拳打一愣一愣的,一脸huhcat.gif。
“说吧……”他低笑着,吻着我的锁骨,“要不要和我共生一辈子?”
我根本已经回答不了,只能颤着声哼出来。
他像得到了满意的答复那样,在我耳边满足地叹气,声音低得几乎要融进血肉里:
“真乖,最喜欢妳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慢慢把妳‘印’上我的味道吧——”
触手渐渐围上来,我突然想到之前纪录片看过的海葵和小丑鱼,就觉得他是某种海葵精,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眯起眼,像是完全不明白我在笑什么,又像是已经察觉到了我脑子里的荒唐想法。
“……小丑鱼?” 他用一种很微妙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还有点危险的预感。
我正想解释,结果触手蓦地收紧,把我牢牢困在柔软却有力的包裹里。
他凑得更近,眼神阴影下涌动着一种坏心眼的笑意。
“原来……在妳心里,我只是随便什么海葵吗?”
触手在我腿间若有若无地蹭了一下,像是“惩罚”一样。
我被刺激得一颤,赶紧摇头,却又控制不住呵呵笑出来。
他眯着眼,语气慢慢变得低哑:“趁妳还能笑,就多笑吧。”
“别停……待会哭出来,可别怪我哦。”
说着,几条细长的触手已经灵活地滑进更敏感的地方,带着一点点捉弄的节奏。
他用一副“既爱又恨”的表情盯着我,像真要把我整整教训一顿——教到我哭着认错、主动求他才肯罢休。
我在触手柔软又黏腻的包裹中瑟瑟发抖,心里又害怕又忍不住期待。
今晚,看来是逃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