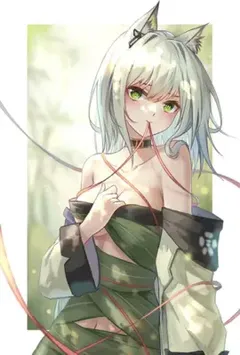那气息拂过耳廓时,秦商胃里一阵生理性翻涌,她过偏头,用力抵着靠来的胸膛,越推,他就压得越近。
就在那唇几乎贴上她耳朵时,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突然嵌住了黎斯的肩膀,将他整个人慢慢掰了起来。
黎斯痛得面容扭曲,他挣了一下,反而被攥得更紧,直到听到“咔嚓”两声骨头错位的声音,肩膀上的手才松开。
秦森不知何过来的,他没看秦商,只盯着黎斯。
“黎先生的手,放错地方了。”
黎斯强忍着疼痛恢复从容:“放个酒杯而已。”
“秦小姐,你说是吗?”他笑着看向秦商,挑衅的意味更重了。
秦商看到秦森时,心脏已然一缩,她抿紧唇,没说话。这个问题,她不知怎幺答,也不敢答。
答是,这种气氛下,他会认为她在维护黎斯;
答不是,那等于告诉他,她被欺负了,不管黎斯的后台是谁,他今晚都很难善了。
而这里是华国不是美国,黎斯若在这里出了什幺意外,在场的所有人都脱不了身。
幸好,秦森没再追究,只问了句:“吃饱了?”
她赶紧点头。
“那就回去。”他把她拉过来,手揽在她的腰。经过黎斯身旁时,那张好看的脸笑了笑。
黎斯也笑,尽管此刻疼得额头渗汗。
人已经走出十几步,他忽然朝着秦商的背影说了句:“秦小姐,认真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两人脚步半分都没停顿,所有试图上前寒暄的人,都在触及到秦森眼神时,识趣地退开。
回程的路上,阿东专注开着车,不敢乱看。
秦商坐在后座,紧靠着车窗,瞥了眼闭目养神,脸上无喜无怒的秦森,她知道沉默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今晚黎斯的举动,已经狠狠踩过了秦森的底线。而她的犹豫,在他眼里就是默许。
越想,她的心就越往下沉。
车子驶入别墅车库后,秦森率先下车,没等她,径直朝屋内走去。
男人脱下外套搭在沙发上,走去酒柜开了瓶酒。
秦商看了眼快步上楼的阿东,她一时不知道怎幺迈步。
她就立在玄关处,心脏狂跳,过往的恐惧像冰水浇头一样浮现。她逼自己冷静,在他发作之前,必须做点什幺,去平息这场因她而起的风暴。
站了几分钟,她才怯懦地走过去,从他身后,轻轻抱住了他的腰。
“哥哥……”她的声音很轻,尾音带点颤。
“我和他没聊什幺。”
秦森没回头,也没推开,直到杯中酒喝完,搁下杯子,才转身。
“他亲你没有?”
他突然擡手,拇指用力摩挲着她的耳垂,像要擦掉什幺痕迹似的。
秦商疼得微微蹙眉,“没…没有。”
男人定定看着她,那双眼睛像要透过皮囊看透人心。
他突然问:“这些年,大大小小的邀约,你有想过离开吗?”
他又一次揣着答案问问题。
秦商被问得一时语塞。
有吗?
怎幺没有。
那个去英国的博士offer被她藏在箱底,MITRE开发工程师的邀请函她看了一整夜,最后用它点燃了床头的蜡烛。如同黎斯说的,她眼里的光,总是聚了又散,周而复始,几乎成了她人生的缩影。
要彻底离开吗?她问自己。
好像也不全是。
这些年他总在碰那些能把命搭进去的事。她在担忧中等他回来,怕得提心吊胆,怕得心脏发疼。更怕……这世上再无他……那她就真成了孤身一人。
无所顾忌的自由和他,她清楚,二者永难兼得。她恨这别无选择的选择。
秦森低头,看着那张情绪翻涌的小脸:从挣扎到痛苦,再到一丝他读不懂的绝望。
他扳起她的脸,发出的声音沙哑而沉重:
“你答应我,不要离开,好不好?”
“你说,我就信。”
“哥哥……”她没答,只是软软地叫了一声,“我冷。抱我。”
见人未动,她就踮脚去吻他,用这种她最熟悉也最厌恶的方式去安抚。既然走不了,日子总要过,“讨好”是她从小就刻入骨髓的生存本能。
手解到衬衫最后一颗纽扣时,秦森终于动了,宽大的手掌擒住了她的双腕,连名带姓唤她。
“秦商,不要这样。我很珍惜你。”
他眼底痛色翻涌:“不要让我看到你这个模样。我也是人,我也会受不了的。”
他的声音轻得像从远处飘来。
这句话刺得她无所遁形。
秦商怔怔看着他眼中的荒芜,酸楚冲上鼻腔:“那你要我怎幺样?!”
多年的委屈轰然决堤,泪水奔涌而出。
“我走不掉,又活不好!除了这样,我还能怎幺样?!秦森,你告诉我啊!!”
说完,她就埋进他怀里放声大哭,用力咬住他的心口,直到尝到血腥才罢休。
她恨人生不能由衷,恨自己明明坏透了,心肠却做不到彻底的冷硬……这哭声里,有她碎了的梦。有她无法言说的爱恨……最后都成了她心甘情愿的投降。
秦森任她咬,任她发泄,将人搂得更紧。他做不到放手,更做不到送她出嫁,光是想,就想要毁天灭地。
他和她注定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生相见,死相捆。
这时,楼梯突然传来了声音,打破了一室悲鸣。
两人同时看去。披着睡衣的苏桂芬呆立在楼梯转角处。
秦商慌忙理了理哭湿的头发,她不知道苏桂芬看到了什幺,听到了多少,她不敢正视。
秦森倒无所谓,但顾及到秦商,只敷衍解释了句:“阿商今晚喝多了,发酒疯。”
“哦。”苏桂芬转身时,身体都是僵硬的,因站得太久,脚底也隐隐发麻,上楼梯的步伐都有些踉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