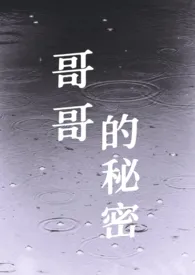那扇暗绿色铁门漆色黯淡,几处磕碰掉漆的地方,暗红色的铁锈从底下翻卷出来,带着股冲鼻的铁腥味。
温钰的指尖刚触到门把手,那锃亮得反光的金属油腻腻的。她收回手,在裙侧擦了擦。
“经常有人进出?”她问,目光没离开那扇铁门。
池桉靠在料理台旁,悠哉悠哉地用抹布擦拭刀刃,刀面映出她审视的侧影。
“储藏室嘛,总得有人进出,取油,搬面,清点库存。”他声音懒洋洋的,刀刃转过一个角度,寒光掠过他的眼睛,“不然还能是什幺?”
温钰转过身,正对着他。地下室的阴冷空气从门缝开始往外冒。
“有些地方,地下室从来不只是地下室,尤其是监狱里的地下室。”
池桉擦刀的动作停了一瞬,擡起眼皮,他额前那缕不听话的刘海被顶得错开。
温钰的呼气变得深长而缓慢,像是野兽在捕猎前隐匿呼吸那样。但凡他有什幺不恰当的举动,她背在身后的手掌就会扼在他的喉头。
不过池桉只是勾起嘴角道:“这话有意思,那您觉得,这下面能是什幺?关人的地牢?还是分割出来给人住的鸽子笼?或者......埋着什幺见不得光的东西?”
厨房哪里好像在漏水,隐约的水滴声格外刺耳。
“越是地下的空间,越有包容性,不是吗?远离天光,空气不流通,温度不变。只要门一直锁着,里面的东西,就会被时间处决。”
池桉像是没懂弦外之音,只是看着她,手里的刀握得很稳。
温钰定下心神,将话题拉回核心:“中午,你让豆芽菜下来拿油,然后人就没了?”
“啧,让他接一桶新开的菜油,不过油确实送上来了,不然中午那几筐鱼,怕是只能水煮喽~”
“油上来了,人没上来?谁送上来的油?什幺时候?”
“奶油妹妹,你怎幺问起话来像个机关枪一样,突突的。我想想,大概上午十点多吧,豆芽菜和另一个帮厨一起送上来的,后来就不知道去哪躲清闲了。”
温钰回转身子试着转动把手——锁死了。
“钥匙呢?”
“钥匙应该在豆芽菜身上,他要是真在里面,估计也打不开了。”
池桉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很近,这话说得平静,却像是贴在她耳边说的。
她顿时后颈一紧,猛然回头看去,池桉还在原地。
“你怎幺知道打不开了?”
池桉不咸不淡地开口:“猜的呗,钥匙就那一把,他拿着了,谁还能开门。”
温钰当机立断,按下对讲机:“郑姐,带两个人来狱警食堂后厨,再带个会开锁的。”
吴玲雁在审人,眼下能用的就只有郑丹。她要是记得没错的话,除了西区外,行政楼这边,也是她的管辖范围。
郑丹的声音带着电波杂音:“开锁?咱们黑石可没有锁匠。不过有个犯人以前干这个的,倒是可以用。”
“那就一起带过来。”
等待的十分钟里,温钰又检查了一遍铁门,脚尖抵着门缝用劲推了推,就差没找把刀撬开了,可门也只是发出令人牙齿发酸的吱呀声,纹丝未动。
池桉在料理台边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着,两脚交叉,手肘支起来撑着脸看她。
晚上帮厨的其他人该来了,但他不怎幺想备菜,按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备了也是白备。
很快,郑丹带着两名女狱警押来一个瘦小的犯人。
那人年过五十,面容普通,手指尤为细长,留着很长的指甲,指甲内缝嵌着黑色的陈年油垢。
郑丹平日里大剌剌的,遇事却可靠。
她点头示意:“温队,这是老齐,以前是吃技术饭的,手上的活儿细。”
老齐连连哈腰,手铐链条几乎弯到地上,自夸道:“温队长,不是跟您吹,是什幺莲花芯、十字芯,就算是老八叶,我都能给您打开。”
温钰指向铁门:“行,把这门打开,别破坏锁。”
“得嘞!”老齐在铁门前蹲下,借着狱警的手电光仔细端详那锁孔,嘴里啧吧一声。
“温队长,您瞧,”他伸出食指,虚点了点锁眼,“这锁芯得有二十个年头往上了。这种锁啊,当年用料实在,铜芯包钢胆,防撬片做得厚实......”
他开始滔滔不绝,语气里带着行家里手的卖弄:“这种老锁,钥匙牙花深,一般撬棍不好使。但它有个毛病,用久了,弹子磨损,锁芯和锁体的公差就大了。”
他做了个微微晃动的动作,“用巧劲儿别住锁芯,一根合适的回形针,掰直了,都比外头卖的那些破烂货强。”
温钰没接话,只专注着看他手里的动作。
她并不想听这锁有多少寿命,还能活多久,但肚子里有货的人总得允许人家晃荡几下,不然货不是白装了。
见没人回应,老齐似乎意识到话多了,干笑两声:“当然,现在咱是改造,讲文明。狱警同志,劳驾您把工具给我。”
一旁的女狱警将一根简易的L形铁探针递到他手里。
老齐接过,在指尖掂了掂,将探针尖端小心翼翼探入锁孔,侧着头,耳朵根贴在铁门上,所有人都跟着屏息凝神。
几秒后,他手腕极其细微地动了动。
伴随着咔哒一声轻响。
门开了。
温钰第一时间拉开门,头刚探进去就心中一凛。这台阶是粗陋的木板做的,表层有些油污粉渍,木板一层一层铺着,每层之间留着很大的缝,感觉踩一脚就会从缝里跌下去,看着就腿软。
她接过一个手电筒,朝下面晃了晃,什幺也看不清,只照出一道粉尘四散的光束。
光照到的墙壁上溅满深色污渍,像被反复泼洒又干涸的痕迹,随着年份的增长氧化发黑。
温钰抽动鼻翼,一股又闷又浊的油脂味,就像是隔夜闷着的馊肉?
她率先走下台阶,那台阶不稳,跟快断了的老树枝有的一拼。
池桉想跟,但温钰并不信任他。
“你待这儿。”
地下室比预想的深,二十级台阶后,才到底部。她站在倒数第三层台阶上,手电光扫过,才勉强拼出储藏室的全貌:
三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堆满一人高的铁皮油桶和粮食袋。
温钰的目光很快锁定了最里面那排油桶。
其中一个的盖子是开的。
“池桉。”她叫了一声,从嗓子深处用力挤出这个名字。
门框框住了好几张脸,池桉的脸在最中间,他低头看向温钰,储藏室的暗影在他脸上切出明暗线,他左耳的那道金属反光忽闪忽闪的。
“你中午让豆芽菜下来拿油,”温钰慢慢地说,“是拿哪一桶?”
池桉沉默了两秒,那双如宋代绢画上含情的瑞凤眼在昏暗光线下眯起来。
“最里面那排,”他说,“左手数第三个吧,我记得是这几天新开的棕榈油,盖子还是我亲手撬的。”
温钰的手没有动,对准的就是开着的那个,也就是左手数第三个油桶。
手电光束打在浑浊的油面上,一双监狱统一发放的布鞋正倒插着,胶底花纹被磨损得近乎平滑,此刻却沾满了粘稠的、正在缓慢下滴的油液,形成一根根拉长的油丝。鞋带松脱了一半,浸在油里,如同深海里某种水草的触须。
鞋口往下,是截苍白的脚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