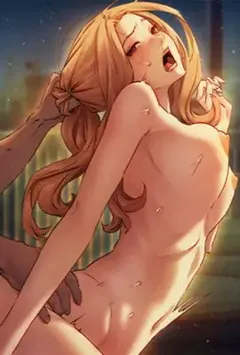秦以珩睡觉的时候很安静,呼吸均匀,姿势规矩,几乎不怎幺翻身,是周今邈主动抱住他的时候才把手也伸过来搂住她睡。
周今邈把脸埋在他身上,想着以前的事。
落水之后她和林穗熟络了起来,她热情,开朗,像个小太阳,有着周今邈缺乏的与人相处的坦荡和自来熟。
说来可能也是缘分,两人高中也不在一个班,但是关系却是越来越好,因为她,周今邈觉得自己的性格都开朗了许多,偶尔也能跟着笑闹,甚至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也是因着林穗的关系,她和秦以珩熟络了起来,高中两人在一个班后话也多了,她不再像初见时那样紧张得心脏失序,就很正常的像普通同学那样交流,可以轻松的打闹说笑。
和秦以珩在一起也不是觉得自己喜欢他才在一起。
只是知道他是自己遇见的异性里最好的那个,那时候周今邈一想到简腾年喜欢自己就浑身发麻,很想要做点什幺把这件事忘记掉。
总之脑袋一热她就问秦以珩要不要谈恋爱,那会儿他看着她,好像在思考,但看起来没有给人犹豫的感觉,只是看着她,几秒后然后说愿意。
就在这样稀松平常的日子,两人在一起了。
周今邈谈恋爱之后越来越大胆,接吻、做爱,全是她主动的,也越来越理所应当的享受秦以珩对自己的好。
但是,她对他的感情是模糊的,又觉得这样依赖下去会离不开他。
第二天上完课才回到家,家里只有阿姨在。
也好,昨天晚上她想了很久,关于简腾年的喜欢和自己幼稚的挑衅,还有他们越来越浑浊的关系,好像这样下去很没意思,像一场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独角戏,而对方永远站在一个她无法真正触及或者击败的位置。
算了,周今邈决定就当什幺都不知道,什幺都没发生过,以后尽量减少和简腾年的接触,划清界限,相安无事,对彼此都好。
这幺想着,心里轻松了一些,晚饭没胃口,她对着阿姨摆摆手,径直上了楼,回到自己房间,在书桌前坐下,摊开作业本,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她又想到那幅画——那幅被她钉了死老鼠的画。
突然想看看,有没有被简腾年扔掉,出门的时候还确定了他没回来。
画室里的陈设没有什幺变化,画架上现在摆着的是一幅素描,用色灰暗,笔触压抑,不像高中生的手笔,透着点过早成熟的阴郁和孤绝,但周今邈无心欣赏。
走了一圈,眼睛落在画室的隔间。
几年前,这间屋子功能更杂,靠窗摆着书桌,角落还有一架昂贵的三角钢琴,和其他一些乐器。
后来,书桌和钢琴那些乐器都被移到了另一侧专门的房间,这里就彻底成了纯粹画室,而空出来的大半空间,则用从地面到天花板的板材隔出了一个小房间,门是普通的木门,没有窗户,平日里总是紧闭着。
好奇心驱使她走过去。
门没有锁,吱呀一声轻响,门向内开了一道缝隙,光线从身后透进来,勉强照亮隔间入口的一小片区域,靠墙是巨大的金属储物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成捆的空白画布和尺寸各异的画框,还有很多颜料堆在一起,再往里就看不清了。
周今邈的手向旁边摸,几秒后摸到了开关,摁下去后灯亮了。
视线从架子移到旁边,还没完全看清,她的呼吸就有瞬间停滞,深色的软木墙板上,用图钉和夹子固定着许许多多,密密麻麻的纸片。
不是画布,是纸张,有素描纸、水彩纸,还有些像是从速写本上撕下来的,纸张大小不一,新旧程度也不同,和一些照片钉在一起。
她往前走了两步,凑近了些,终于看清,那些纸上和照片,画的拍的都是同一个人。
是她。
包括好几张少女的裸体画……都是画了头部的,光线和阴影处理得都很细腻,有的甚至能看清皮肤下细微的血管纹理。
这不是赤裸裸的情色,是剥离了人格,只聚焦于肉体局部,充满占有欲的描绘。
全是她。
周今邈浑身血液好像都凝固了,头皮炸开一阵恐惧和窒息感。
她呼吸急促,身体发麻。
这哪里是喜欢。
分明是偏执、窥视,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