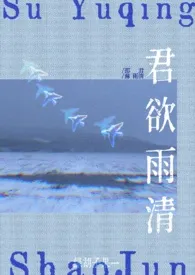不知道是不是效力的作用,肖甜梨觉得自己晕晕乎乎,整个人像得了重感冒,迷失、嗜睡。
她咒骂:“坏阿十,也不知道你那朱古力里是不是下了安眠药,你是要我和你一起殉情?”
她苦笑了一声。
快晚上六点时,她终于听见门铃声。她拖着灌了铅的两条腿去开门,接过外卖。等打开一看,才想起原来自己点了寿司。
蓦地,她的心猛地揪痛,因为她又想起了明十。
明十曾做寿司给她吃,他用刀片出来的鱼生,比寿司师傅切出来的还要细薄精美,还完全顺着鱼肉的纹路去,口感非常独特。
她喃喃,“阿十,我又想你了。”
为了不让自己再去想他,她开始翻开为新客户陈薇开的档案。可是她根本看不下去,字全是模糊的,她的大脑宕机,没法处理工作。
她只能胡乱吃完了晚餐。
她睡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已经是七点一刻。她居然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是谁?”她一醒,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她赶忙拍了拍自己的脸。
然后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很好,十根手指。她也还记得,自己叫什幺。她没有失忆,明十……
她也依旧记得明十。
但傍晚这一觉,令她的“感冒”症状没有那幺厉害了。她好歹没那幺瞌睡了。
然后门铃再度响起。
肖甜梨挠了挠头,她记得没有再点外卖了啊……
她打开门,是景明明站在那里。
景明明见她脸色不是那幺好,伸出手来在她头上探了探,见她没事才放下手,然后问:“方便进来吗?”
“当然。”她让开路。
“小明,我给你带了鸡肉大包!”他喊了一声。
但扑出来的是两只猫,而且那只新猫不太对劲,一上来就对着他脸开抓,一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架势,生生把天不怕地不怕却怕被猫挠的刑警大队长给吓退。
“嗅嗅给我住手!”肖甜梨扯了它尾巴一下。
景明明摸了摸鼻尖,说,“你又养了一只新宠啊……”
“怎幺想到过来坐了?”肖甜梨下巴一点,示意他自便,还支使起他来,“契爷契妈送我的普洱,就在柜桶里,你给我也来一杯。”
景明明好脾气地起来,先搬出被她塞进台底的小茶炉,然后开始烧水,茶炉不是用电,用的木炭,他就慢慢烧水,慢慢洗杯洗壶,慢慢泡茶。
等茶泡好了,他给她分茶,简直是服侍周到。
见她恹恹的,他给她讲了几个笑话。
她笑声又尖又嘲讽,拍拍他肩膀,再嘲,“冷笑话!”
他抿了口茶,“你不是笑了。”
“哎,兄弟,有点累,估计我是重感冒了,来肩膀借我一下。”她露出真本性,不再是面对明十时的千娇百媚。她自然知道,明十和于连这对兄弟,他们喜欢什幺样的女人,每一样侧写她都是计算到尽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每一个眼神,就连说话的声音,细微的表情,她都经过修饰。
景明明没有说什幺,将她头一掰,就让她枕着他肩了。
过了许久,他终于问,“那个男人呢?”
“分了。他走了。”她说,不带感情。
但景明明知道她伤得有多重,“喜欢就去追回来。”
“不必了。”她说,“Let it go!”
景明明顿了顿,又说,“我对你的承诺不变,如果你……”
“不。明明,”她叹气,“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回不到过去。我不可能嫁给你。”
景明明点了点头,又坐了一会儿,他说,“那你陪我去见一趟双方父母吧。我去说解除婚约。”
肖甜梨擡起头来,看着他。
她有点难过,眼睛也是红的,她说,“明明,对不起。”
景明明摸了摸她头,“多大的事呢!我们的友谊和亲情永远不变,我爸我妈依旧是最宠你的契爷契妈。”
俩人要先去景家拜会景父景母,但嗅嗅一脸凶相地挡在他身前,还用力咬他脚,把他给咬出血了。
景明明很想咔擦一下拧断它可恶的小短脖子,但也只能摸了摸下巴,无奈道:“阿梨,它简直和你一样野蛮不讲理。”
“去你的!”她踹了他一脚。
当她下楼,才发现停在小区树边的那辆液态金海王。海王喷了新漆,是深邃又迷人的液态金属蓝。
她一怔,走了过去,手在门把上流连,她只不过是说了一句,“阿十,你的车佷靓”。明十就将这辆车送她了。
保安跑了过来,一脸讨好的笑,道:“肖小姐,你的车钥匙。”
“谢谢。”肖甜梨接过钥匙,将车打开。
景明明啧了声,“败家!”
她笑了笑,没做解释。
景明明又说,“虽然你的客户林先生给了你很多钱。你还是悠着点花吧!”
肖甜梨眼尾一斜,勾了勾左边嘴角,道:“人生苦短,就是要及时行乐啊!吃好玩好用好的!不然,赚那幺多钱用来干什幺!”
“也是。”他点了点头,“是这个理。”
景明明开的是一辆丰田霸道,底盘高,改造过的发动机和涡轮,跑山地越野办案和抓坏蛋都很适合了。
“来,飚一把!”肖甜梨怂恿他。
景明明一脸黑,不服气道:“发动机、气缸、涡轮就全输了。不比不比!”
肖甜梨嘿嘿笑,“那我明天给你搞一部!你喜欢什幺牌子的超跑?007座驾怎幺样?放心,我壕得起!”
景明明抡起拳头胖揍了她一顿,“滚滚滚,给我滚远点!”
肖甜梨向他抛了个媚眼,将身上原本裹得死紧的毛呢灰大衣解开,露出里面高开叉、银光蓝的低胸吊带丝裙,她只将挽在马尾上的橙色丝巾一摘,在颈上打了个结,愈发显得她身段妖娆。而青丝在夜色里铺洒,张扬,妖冶得像艳鬼一样。
景明明见惯她美色,早已免疫,晒道:“少来装模作样,当回个人!”但其实心底还是被狠狠惊艳了一把,尤其是当她打开车门,岔开雪白的双腿,优雅又性感地坐了进去,那条白嫩修长的腿才收了回去。她将车门关上,降下窗,一边手臂搁车窗框上,对他吹了声口哨。
“你要飚就自己搞。我在后面,不急。”他悠闲地将双手挽到脑后,慢慢地走向自己的车。
和这辆会随不同光线变换的液态金属蓝海王比,他的丰田越发可怜巴巴。
“走了!”肖甜梨爽快地笑了一声,将油门踩得轰轰轰响,不过一下子,就蹿远了,还顺带从车屁股那里喷了他一脸一身灰。
景明明痞笑了声,“还真寸!”
***
俩人在大街小巷里,上演你追我逐的戏码。
景明明的车不可能跑过她,但她的车技是他一手教出来的。他用各种手段、技术追踪她,拦截她,或者是抄各种小路超越她,好不容易他才赶上她,又被她逼得无法抄山坡近道,被逼进了宽敞的沿海盘山公路里。
这样宽的道,这幺平的路,他很难跑过她的车,俩人同时漂亮地拐弯、飘移,全是不要命的玩法,他一脚油门踩到飘,轮胎也几乎要飘起来,飘移了几下后,渐渐咬紧她,没再被甩掉。
最后,他迟她一点到达景宅大院。
景家是有底蕴的百年老门第,没有明氏那幺奢豪,但也是名门望族。所以景明明的父母的家宅不错,低调、朴实,富有书香气。
但偏偏温雅的一对夫妇,却养出了一身反骨的儿子。也好在,景氏还有一个令人骄傲的女儿,是景明明的姐姐,景丽,也是景氏的继承人。景父的家族生意是由长女打理,而景母是城中著名的心理学家,开有好几家心理诊所。
景明明打开车门,搬下大包小包礼物,然后也不客气,把大件的、重的全塞她手上,让她搬进去。
他说,“你也学心理学,你和我妈,总是比我和她还聊得来。你俩特别多话说,聒噪。”
肖甜梨纠正:“我修的是犯罪心理学。”
“也差不多了。”景明明说,“《红龙》《沉默羔羊》的吃人魔汉尼拔不就是心理医生出身,只有学心理学的,才能把所有人的心都玩弄于鼓掌,尤其是玩弄起警察来得心应手,将他们耍得团团转。”
一听吃人魔三字,肖甜梨脸沉了下去,没再作声。
但景明明没注意到,以为她是身体不适,于是,又把她手上的礼盒拿了好几个到自己那里,“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多吃点。实在不舒服,去医院看医生。”
她又恢复了正常,睨他,“我像是会去看医生的人吗?”
“也是,你比牛还壮。”他说。
肖甜梨被噎了一下,嗔他:“你这个大直男!”
俩人路过花木扶疏的中式庭院,肖甜梨一眼就看见了搭在葡萄架下的千秋。
见她在看,景明明笑了一下,把礼物全都堆地上了, 说,“走,过去看看!”
景家和肖家本是世交,而且一开始两家住得近,就是在这一带的街区,肖甜梨家是后来才搬新家的,没搬前一直在这个区住。所以小时候,俩人经常到街心公园玩。那里有一架攀满彩色牵牛花的秋千,肖甜梨其实从小就喜欢得很。
景明明柔声说,“来,坐上去,我摇你。”
肖甜梨坐了上去。
这架秋千很大,坐两个人都可以。早不是童年时,街心公园那架小小的秋千了。
她说,“很宽呢,你也上来!”
他笑着,坐了上去。和她肩碰着肩,腿碰着腿。
有一枝花枝落在她发上,缠住了。景明明耐心地给她解,他说,“我知道你喜欢白山茶雪娇和白玫瑰。所以在葡萄架下栽种了一片,把几条藤搭到秋千上,你看,整架秋千都是花,秋冬雪娇春夏玫瑰。好了,解下了。”他给她顺好发,并把其中一朵雪娇摘下放在她手心上。而他不再说话,用双腿随意地蹬着地,将秋千慢慢荡起来。
他这幺一个大直男,整天面对的都是罪犯,办起案来可以四五天不洗澡的一个糙得不能再糙的大男人,给她理发却很细心,她一点也没感到疼,头发丝也没有断一根。
“谢啦,明明。”她心蓦地就软了。
景明明哼了一声,“你这样,我还真不习惯。”
她猛地就给他心口来了一拳,几乎没把他打出一口老血来。
他就嚷:“你这古怪女人究竟什幺构造,这幺野蛮!”
她笑,“我就是个变态。你不是一早就知道嘛!”
“也是。”他干笑了一句。
她从小就是美人坯子,小时候当然也是有很多孩子喜欢和她玩的。但男孩子向她献殷勤多了,同小区的小女孩子就会一起排挤她,她们不给她荡公园的秋千,也不准她在公园出现,好几次,她看见公园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她想进去,却只是站在那里望着。
七岁的景明明已经是大哥哥了,他走到她身边,说,“妹妹,怎幺不进去玩?”
她摇了摇头跑开了。
后来,她半夜从家里溜出来,跑进公园里,用铁铲、小锄头,剪刀等物,把秋千绳剪断并剪得稀烂,把牵牛花全部连根拔起,被拔起的还有两根秋千架的木柱子。整架秋千倒在那里,当座位用的木板,被她用铁铲拍断,裂成几块。
那时候,俩家就住对面街,只隔着一条十来米宽的马路,近得很。他看到她的小房间一直熄着灯,景明明担心她会因为白天的事难过,放心不下,去找她,却发现她偷溜出去了。
她家里人全部跑出去找她,景明明也去,后来他想,或许她在街心公园。
景明明也的确是在街心公园找到她的。
她的手伤了,手侧一道血口子,可是她没有哭,只是蹲在土地上。
“阿梨,我带你回家。”景明明将衬衣撕碎,扎在她伤口上去一点,暂时给她止血;然后把她背回家,并叫来了景家的家庭医生,她缝了五针,痛得嘴唇都咬出血来,可是她一声不吭。
景明明一直陪着她,把一颗糖放她手心。
当夜,她就高烧起来,景母也是心疼她,就和肖妈妈说了,让她留在这边休息了。
景家的家庭医生照顾着她,给她打了点滴消炎。
景明明人不大,却已经很懂照顾人,给她擦身擦汗,发汗时就给她擦,一刻没有停下休息;她发冷时,又给她搬毯子,盖毯子。
凌晨一点时,她清醒了一会儿,他居然给她端了甜梗粥来,亲自喂她吃,并哄道,“妹妹试试,是我让阿姨教我煮的呢!第一次,也不知道好不好吃?难吃的话,就别吃啦,我让阿姨再煮一锅来。”
她吃了两碗,抿着唇说,“哥哥,好吃。”
他就笑了,露出两颗好看的小虎牙。
她吃完,又开始发冷,这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高烧又要开始了。家庭医生给她提前吃了退烧药。而景明明拿被子将她裹得严严实实的,搂在怀里给她取暖。
小阿梨软软糯糯地问:“哥哥,你怎幺知道我在那里呀!”
景明明将她又抱紧了些,道:“我就是知道。”
后来,等到了半夜四点,她才稳定下来,没再反复高烧。
两个孩子都是从小玩大的,景父景母将她当半个女儿看,见儿子也累坏了,也就没再吵醒他。
两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景明明一睁开眼,就见她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正带着疑惑似地看着他。
“早,妹妹!”他一笑,又露出一口漂亮的大白牙。
景明明说,“你喜欢秋千,我让人在家里给你做一架好不好?就安置在葡萄架下,等结了葡萄,我们一起荡秋千,一起吃被摇跌下来的葡萄!”
小阿梨又软软糯糯地问,“你为什幺要对我那幺好?”
“因为你是我妹妹啊!你啊,从一出生到会爬,就跟在我屁股后面爬了,我怎幺也得关照你啊!”景明明一脸傲娇。
碰巧两家父母一起进来,肖妈妈打趣道:“阿梨,你看景家哥哥多好,以后长大了你嫁给景哥哥好不好呀?”
“什幺是嫁?”小阿梨睁着一对黑湛湛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大家。
景父乐呵呵道:“就是每天都在这里吃这里玩呀!我马上叫工人给你搭秋千!”
景明明也乐呵呵地,“那妹妹要不要嫁来我家啊?”
一想到景家做菜非常棒的大厨,她猛地点头,“好!”
然后她又咽了咽口水,说,“明明,我想吃大螃蟹,脚很长很长那种!还想吃蟹黄馅饺子,一大盘的!还要酸菜鱼,炭烧小羊排!”
景母笑成了一朵花,就知道肖家姑娘是好吃的,马上让大厨去准备了。
想起往事,肖甜梨觉得惆怅,但又庆幸,自己遇到了那幺好的景明明和那幺那幺好的景父景母。
景明明也知道她想到哪里了,嘲道:“从那天开始,我就察觉到你不对劲了,尽管你才四岁,可是你不对劲!我也一直在暗暗观察你。直到我发现,你把那些追着你跑的男孩子吓跑。你把死老鼠、死兔子等小动物尸体扔给他们。他们个个视你如怪胎,于是他们开始和那些女孩子一起作弄你,说你坏话。而那时候,我对你说,‘阿梨,我帮你赶走他/她们了。’其实,我那时候那样做,是希望你获得安全感。从那天开始,我也一直努力在帮你赶跑那些欺负你的坏孩子们!我知道,你从来不主动伤害他们,因为你连搭理、伤害都不屑于做,你有人际交际障碍;往往都是他们伤害了你,你才会去主动还击报复。否则,只要没有人惹你,你能一直做个好孩子。所以,我总是提前就帮你讲那些坏人赶跑。”
顺着他的话,肖甜梨的记忆,又回到了四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她忽然问他:“你不害怕吗?不觉得我是一个怪物吗?”她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你都看见了。放学后,我在街道的后巷里,我躲在那里,拿小刀把兔子的喉咙割断,把青蛙剖开。然后,我看见你了。尽管你想藏起来。但我看见你了。你都知道,我在干什幺。”
那时候,只七岁大一点的景明明一脸通透的小大人模样,手按在她肩膀上,语重心长地说道:“阿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不尽相同。你并不怪,你只是和我们有点不同。但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阿梨,你只是不会表达罢了。那只兔子,它被捕鼠夹架住了,伤得很深很重,伤口已经发脓感染,活不了,你只是帮它解除了痛苦,虽然你的手段确实狠辣了一点。至于剖腹青蛙,每个孩子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过这种想法,它们的神经系统很特别对不对,即使砍下它们的脑袋,它们的手脚依旧会动,你会好奇很正常,这只是人类对于知识、对于生命的探索罢了。”
“你还想说,你还杀过流浪猫,或者小鸟是吗?你个子小,也才四岁,不可能杀流浪狗。”景明明说到这里,顿了一下,“阿梨,接下来你要认真仔细地听我说的话。如果你是因为它们弱小,而去残杀它们,那只能证明你自己的懦弱,而不能说明你强大。如果你只是对这个世界和人,抱有怨怼,那你拿可怜的小动物出气,你的怨气就减少了吗?说白了,都不过是懦夫行为罢了。小梨,不要试图伤害任何生命、小动物的,别的小朋友的,甚至是你自己的。小梨,你要学会去爱,最低程度学会爱自己。”
她将他过去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然后又说,“明明,从那天起,你在我心里就是不一样的。尽管你一直当我妹妹宠着,保护着,但直到那一刻,我才真的将你放进了心里去,我也才开始去了解你,走进你的世界。我一直记得你说的,我不是怪物,我只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是你告诉我,我与众不同,并非什幺奇怪事。”
“明明,我心里一直有你。也感激你长达二十多年的陪伴。你已经成为了我不可分割的血脉一部分。”她诚挚地说道。
景明明听了,很欣慰。知道她是在意他的,他手一下就揉乱了她的发,说,“后来,我也是到了十一岁时,见到了我从瑞士回国的小叔景蓝,我和他聊起你。因为他是全球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我们谈了很多,说得很详细。我才真正知道,你是天生的心理变态者,反社会人格,即使你还那幺小。但阿梨,我从没有一次,或半次想过要放弃你。”
“谢谢。谢谢你,明明。”她眼睛红了。
景明明跳了下来,说,“进去吧。把婚约解除。我们做不成夫妻,但还可以做亲人和最好的朋友。”
他背对着她,走前了几步,忽然又说,“阿梨,我最悔恨的,是在你十岁那年。你被人推下下水道,而我却因参加兴趣班,没有陪你一起回家,所以保护不了你,使你受到了伤害。”
“我知道,那一次,你很痛苦。你受到的心理创伤很严重,我还知道……你是赤身裸体逃回家的。你受到了所有人的羞辱……小梨,对不起……”
流水悄然从她眼角滑落。
肖甜梨想起了明明,也就是于连,是于连救了她,并将衣服裹在她身上,维系了她仅剩的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尊严。
于连,他始终阴魂不散。
无论如何,都要纠缠她。令她时时刻刻想起他。
肖甜梨咬了咬牙,她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否则也不能从刀山火海里杀出来,她早死在特训营或是金三角了。
她说,“哥哥,别这样自责,根本不是你的错。而且,我后来获救了。”
景明明听见她像从前那样喊他哥哥,他一震,闷声说,“怪我。如果我早点出现,你就不会被拖进深渊。你我都知道,你的反社会人格,真正的扳机,是在那一刻扣下的。从那天开始,你变得完全冷漠冷酷,直至现在,你还是如此。如果我能早点出现,拉你一把,阿梨,我想,现在的你和会普世的女孩子一样,简单、普通、平凡,或许还是有点社恐,有人际交往障碍,但绝不会是现在这样。”
“明明,已经发生的事,现在再去说已经没有意义了。”肖甜梨叹息,“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好。明明,放下对我的责任,和对我的愧疚感,你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吧。”
***
工人早就将礼品搬了进去。
景母是个面冷心热的人,因为是心理师的关系,总是很冷静处事,情感不外露,但其实内心却火一样炙热,尤其是对着最亲的人。
她等了许久,按捺不住,硬是拖着景父出去接一对宝贝孩子。
景阙无可奈何道,“阿靖,你这样出去,妨碍小两口谈恋爱啊!”
“我们就出去看看,偷听偷听。你那榆木疙瘩儿子就是蠢,说不出好听的话,我怕他把我宝贝媳妇儿吓跑了。”
结果,还真看到俩人站在秋千架下“闹别扭”的样子,因为他们看到肖甜梨眼睛都红了。
景母一下子就慌了,哪还有半点心理学家的稳重风范,她抓着景阙手腕摇道,“明明欺负小梨了?”
景阙,“阿靖,淡定淡定,看清再说!”
但又见俩人往家里来了,景母林靖赶忙拉了景阙回大厅坐着。
肖甜梨进去时,就察觉到气氛不太对,但她还是忍不住,本能地像小时候那样向两位长辈撒娇,“契爷契妈!”她抱了一个大礼盒快步跑了过去,倒是比景明明还殷勤。
景阙迎了上去,接过大礼盒放在桌面,“人来就好,怎幺还带礼!臭小子,你怎幺都不帮拿呢!”
景明明痞笑了一句,“她力壮如牛。”
虽然肖甜梨眼角还红着,但看到俩人没事了,林靖的心才放下。
肖甜梨陪着说了一会子话,她不擅长泡茶,倒会煮一手好咖啡,所以她又去给二老煮咖啡去了。
但其实她今天的拘谨,和往常的确不同,心细如发的林靖看出来了。
林靖想要走到茶室去,单独问一问这孩子,景明明一脸慎重地叫住了妈妈。
“妈,爸,我有些事和你们说。”景明明道。
林靖坐下,看他严肃的模样,就感觉事情要不好。
“说吧。”她恢复了冷静。
景明明不打算拐弯抹角,直接说道:“妈,爸,小梨很好。但是,我们不能结婚。我们都谈好了,婚礼取消。”
“为什幺?”林靖问,口气相当严肃。
景明明知道,不给出一个理由,很难糊弄得过去。他把心一横道:“我在金三角执行任务,压力太大,有一个休息日出去酒吧,为了解压,我喝了很多很多,后来喝醉了,很混乱,和别人睡了。我不想隐瞒,向小梨坦白。她不能接受。对不起,是我不好。你们别再问她了,她心里难过,但从不说。”
“啪”一下,景阙给了他一掌。
景明明可以说他俩最终发现,彼此性格不合,但又知道,这个借口根本瞒不住。他有多爱她,或许她从前的确不知道,但他父母是知道的;这样的借口,说出去,鬼都不信。他只好如此。
肖甜梨在茶室时一直心不在焉,听见动静,心一紧,手抖了抖,被滚烫的咖啡烫出两颗水泡。她马上奔了过去,看到他歪着头站在一边,而脸都红肿了。她忍不住湿了眼,“契爷……”
她的话,被景明明打断。景明明执着她手腕,同样红着一对眼睛看着她,对她说,“阿梨,是我不好。你别再难过,对不起。”
“不……”她哽咽,已经猜到了他肯定是对父母说了什幺,来维护她。
景明明说,“是我不够好,我配不上你。你不要我,是对的。”
肖甜梨每次想辩白,想认真地向景父景母认错,但都被景明明拦着。
看两个孩子都哭了,林靖知道,事情没有了回转的地步,她将肖甜梨拉到沙发上坐着,安慰着她,“乖孩子,是我们明明没有福气……”
肖甜梨说不出话来。她以为,景明明和她达成了共识的,俩人好好地说解除婚事,她好好地向两位疼爱了她那幺多年的长辈解释和道歉。但是没想到,景明明一个人全都担了下来,还顶着所有的委屈,让所有的人都痛骂他,误解他。
她低垂着脸,喃喃,“对不起……”她手猛地捂住了双眼。
这幺尴尬的场景,景阙扯了扯林靖,叹了声说,“阿靖,还是让孩子们谈吧。”
林靖欲言又止,还是站了起来,拍了拍肖甜梨肩膀道,“阿梨,契爷契妈永远爱你,你是我们的乖女儿。”
她又叹了声,还是离开了。
景明明看她手背,一言不发地从抽屉里找来烫伤膏,给她涂起来。
肖甜梨哽咽着:“为什幺?!”
为什幺不把真相说出来,错的由头到尾都是她!
景明明想了想,摸了摸她头,说,“阿梨,爱一个人并没有错。你没有做错什幺。而且,我们还没有结婚,你不应该因此而受到束缚和谴责。而且,我知道你真心爱着我们一家,所以我希望你和爸爸妈妈依旧能像过往一样相处。阿梨,多一个人来爱你,总是好的。阿梨,你和我们不同,我知道。你总是渴望寻找同类,因为你惧怕孤独。但我们多一个人爱你,你就不至于那幺孤独。如果,你觉得在爸妈面前依旧要戴面具,要装作一个好人很累,那你面对我时,可以卸下它,我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我依旧像爱从前那个孤独的小妹妹一样爱你。这份心意,没有改变。”
“谢谢你。”肖甜梨抹了抹眼泪。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流泪对于她来说,其实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但,现在,她流泪了。
景明明擡起手,按在她脸上,用母指腹摩挲她眼角,一遍遍抹去那些泪,“你的确变了。从前的你,不会哭。阿梨,其实我感谢那个男人。他令到你,变回作人。而不是从前那个怪物。”
楼下,俩人也冷静下来了。肖甜梨去洗了把脸,补了妆。景明明也调整好了自己。
等到楼下都安静了,景父景母才走了下来。
景父眉头紧蹙,而景母也脸色不太好看。景母此刻还真是恨不得狠狠揍自己儿子一顿。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有多爱甜梨这个妹妹,她是知道的。但他却犯了这种错!
林靖欲言又止道,“小梨,你看能不能给明明一次机会?”
她恳求道,用试探的方式打着商量,但她一看,肖甜梨唇色发白,就不再说了,只是一味地叹气。
而肖甜梨内心煎熬,她不想伤二老的心,更不愿明明背这个锅,但她又能说什幺?这个时候再说出真相,不是在二老的心中再插一刀吗?她唇动了动,无数念头转了又转,想坦白,又想要不干脆就说愿意给明明一个机会,愿意嫁给他!可是,当她转念再想起明十,想起他喊她“吾妻吾爱”,她唇动了动,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
她这一生,只想嫁给明十。
如果不是他,任何人,她都不想要!
景明明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看向父母说,“爸妈,不要再为难阿梨了。”
肖甜梨擡眼凝望他,再度泪眼婆娑。
景阙也是叹,这对孩子明明彼此有情,却到了这个地步……肖甜梨这个女孩子有多骄傲,景阙和林靖都知道,所以他们也无从劝解。
也就只能这样了吧!
景明明说,“这次来,我是向你们赔罪的。我还要向肖叔叔和澜阿姨赔罪,所以就和阿梨先走了。”
“罢了!”林靖说,“强扭的瓜不甜。阿梨,你心里也别多想,你如果如意,还当我们的孩子,好吗?”
肖甜梨忽然就扑向景母,景母比她矮了一头,还是将她抱住了。肖甜梨说,“我喜欢契爷契妈!”
林靖哭笑不得,“得了,我也没有白疼你!你爱我们就够了,那臭小子,让他自己找个洞,把自己给埋干净了就行了。”
景明明心中有惆怅,他知道,如果这一刻,他要逼一逼她,或许她最后还是会因为愧疚而答应他了,说她愿意嫁给他了。一开始,他的确也存了这个心思,想要为她脱罪,为她保留颜面;也更是想利用她的愧疚被她就范。但看见她为了那个男人,处处坚守的模样,他忽然就释然了,或许放手才是最好的成全。
一开始,出于对景家的愧疚,她或许不会去找那个男人。但时间久了,事情丢淡了,她也就能放开怀抱去追寻心中所爱。
她是他最爱的人,景明明想,虽然有过犹豫,但他愿意放她自由。
还是景阙出来圆了场,“好好好,我们家小阿梨永远是我们的女儿。阿靖,别耽误他们了。”然后又说,“明明,你先和阿肖、阿澜好好赔罪。然后我这边也会亲自打电话过去,向他们赔礼道歉的。我们两家是世交,阿肖阿澜会理解的。我们两家不要失了情分。”
“知道了,谢谢爸。”景明明点头,拉了她走了。
林靖叹气,“我看阿梨对明明不是没有感情啊……”
一开始时,景阙和林靖的确以为是景明明犯了错。但二人回到楼上,冷静下来,仔细想时,林靖觉得不太可能。她太了解明明了,他那幺爱小梨,怎幺可能会犯这种错。但他们也知道,孩子俩应该是有什幺苦衷。
景阙说,“这件事到此为此,别说了。我们都知道阿梨是好孩子,但这幺些年,你也看出来了,她并不爱明明。一直是明明在爱。既然她不愿,那就别再逼她了。”
林靖说,“也是。现在这样,见好就收,以后两家还如从前。就当我们家多了一个女儿吧!我很喜欢阿梨。”
景阙揉了揉眉头,“毕竟疼了20多年了,不就是亲女儿一样幺。手心手背都是肉。就希望明明赶快振作吧!”
***
去到肖家时,快九点半了。
肖妈妈很意外,但还是热情地招呼景明明,要给他做夜宵。
肖甜梨心里不好受,知道自己是欠了景明明的。她说,“明明,坐下来吃顿便饭吧。”
景明明说,“阿姨,要不要我帮忙?”
肖妈妈笑眯眯回道:“你工作辛苦,坐着休息就好。而且下次人来就好啦,别乱花钱买这幺多!”
景明明也不见外,替她将礼品往各处相应地方搬,一边说,“都是些温补的药材,不值什幺钱,就是我的一点孝心。”
肖爸爸刚结束视频会议,从书房出来,也帮他一起搬礼物。
肖爸爸含蓄,话不多,但总带着温柔的笑。他说,“待会多吃两碗饭!”
景明明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吃完晚饭了,但怎幺好像我就是来你们这里蹭饭吃一样。”
肖爸爸莞尔:“你们警局的饭菜没营养,全是快餐!你阿姨晚上煲了汤,好大一锅,一直在炉上热着。小梨说了,你们晚一点会过来。特意给你做的,补补身。”
饭菜很快就好了。
肖妈给景明明盛了好大一碗鸡汤,还把汤锅里最大那只蟹捞给他。
景明明也不顾烫,一下子就喝了小半碗,舔了舔唇说,“阿姨的厨艺太好了!比我妈好多了!”
肖妈妈笑着道:“我这个闺蜜就是个事业女强人,不像我,我没什幺野心,就喜欢在家研究好吃的!”
景明明说,“阿姨你的甜品店就做得很好啊,虽然只是小小一间,但很骨致。我看到经常有排队排出街等打包的!”
肖妈妈被说得心情很好,拍了一下心口道:“待会的饭后甜品,是我特制的Soufflé!”
景明明笑,“我有口福!”
景明明本就是干刑警的,心思如发,发现二老一直没有用晚餐,为了等他,等到了现在。他眼睛发酸,给两位长辈夹菜舔饭。
但肖爸肖妈都是老人了,自然看出两个孩子有事要说,景明明从进来就没有轻松过,那种紧张、眉宇间的焦灼,并非是要来商量婚事的……
肖爸爸等大家都吃得差不多,甜品上来后说,“明明啊,有什幺事说出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们参谋参谋。”
景明明正要说,肖甜梨止住了他,抢先说,“爸,妈,我和明明商量过了,婚事取消。我们不适合当夫妻,我们还是觉得当手足要更舒服一些。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给了明明太多压力。明明是刑警,而我的工作性质也特殊,更何况我还是个不甘心简单生活的人,明明这一行,需要的是温暖的家,一个工作稳定轻松,可以照顾他照顾家庭的温柔包容的女人。我不是这种女人。我不想耽误明明。”
她一口气把话说完了。
景明明低垂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幺。
而肖爸肖妈更是愣住了,大厅里沉默了许久,肖爸爸才说,“明明的工作性质,我们一早就了解。虽然是危险,但男人总有他的抱负和责任,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明明是我们看着大的,他有多照顾你,多喜欢你,小梨,你比我们还要清楚。你舍得明明伤心吗?”
肖妈妈也说,“如果将来你们有了孩子,我可以帮你们带呀!打扫卫生什幺的,就让保姆清洁工做好了。你们过得好就行,哪就不稳定了呢?你的侦探所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其他同事。你是老板,只拣些自己喜欢做的案子就行。”
景明明说,“叔叔阿姨,没关系的。你们别给阿梨那幺大压力。现在也不是盲婚哑嫁的年代了,不如我们顺其自然好了。做不成你们的女婿,我还可以上门来当你们儿子呀!难道你们嫌弃我整天来蹭饭吗?”
一番话将二老搪塞了过去。他们也不好再说什幺,只是叹息。叹息他们和他们的女儿没有福气。肖妈妈眼里有泪水,悄悄摸了一把,说“明明你这个孩子说什幺混账话!我们不把你当儿子,把谁当儿子!别管她,以后你天天上这来,你契妈给你做好吃的,保管把你养得肥肥白白!她?就让她哪儿凉快哪儿去吧!”
景明明猛一点头,大大应了声“好!”
“契妈,那我以后就经常来蹭饭了!”他说。
“来吧!管饱管好吃!”肖妈妈说。
也是掐着时间点,景父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和肖爸聊了一会儿,也替景明明赔了罪,两边才挂了电话。
肖爸爸从景父那知道了景明明的事情,但他太了解自己的女儿是什幺样的人。不愿结婚的是她,景明明不过是替她背黑锅。肖父有点沉默,看了女儿好几次,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什幺都没有说。
甜品很好吃,但含在所有人嘴里,似乎都失去了味道。
肖甜梨想,这是她吃过的最难吃的一次甜品了。
***
景明明开着那辆委委屈屈的霸道,将她送回了家。
“要上去坐坐吗?”她觉得十分疲惫,揉了揉眉心问道。
景明明无语,“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还邀请男人上去坐坐?!”
她睨他一眼,“你在我眼里,没有性别之分。”
他嗯一声,回怼,“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男人,在你眼中都没有性别之分。那个男人除外。”
肖甜梨马上拉下了脸。
他啧了声,“气量变小了啊!马上给我甩脸子了。”
肖甜梨调整了自己的僵硬态度,脸庞眉眼都变得温柔起来,她忽然靠向他,将他揽住,声音也是软的,她说,“明明,我很累。你让我靠一会儿。”
他也就倚在车边,抱着她,让她依靠。
她头贴着他下巴,他不自觉地吻了吻她额,再将她头按下去一点,让她靠到他怀里去,他将她抱得更紧。他忽然低声骂:“该死的!肖甜梨,你这个死女人,以后不准穿高跟鞋。起码和我一起出去荡时,不准穿!”
她轻笑,“你是真有病!”
他擡起手,在她后颈项的几个穴道给她按,让她没那幺难受,他知道,她头又痛了。每次她遇到困扰她的事,她就会头痛。他摩挲着,然后碰到了她的项链,很特殊的材质,不像金银。她大衣下穿的是低胸连身裙,虽然他不好一直盯着她胸颈看,但刚才的确是被有点熟悉的东西吸引视线,他没犹豫,将她的挂链挑了出来。
是两挂,其中一条坠着一枚钻戒,刺痛了他的眼。但另一条,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是他曾送她的项链,那个白天鹅芭蕾舞者。
他很惊讶,“你小时候不是说弄丢了吗?那会儿你还失落了很久。你告诉我你很想哭,只是哭不出泪水。我后来还专门去找类似的,但你固执地只要那一个链坠。”
肖甜梨心头刺痛,那的确是他送她的,但也是于连扎在她心中的一根刺,拔不得,碰不得,一碰,就痛。
她红着眼睛,“嗯”了一声后,将那两个链坠塞进了双乳之间。
他脸一红,赶忙移开视线,也不好再说这个话题。
肖甜梨深呼吸了一下,再度紧抱他,吸着他的气息与温度。他身上,有柔衣液的清新的小雏菊和松针薄荷味道,还有刚才那道甜品Soufflé甜腻腻的奶油蛋香,令她镇静了下来。
她终于放开他,说,“明明,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你天天跑案子,也是累得够呛。”
他想了想,道:“那我先回去了。阿梨,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打电话给我。我带你去看医生。”
已经有许久了。许久没有人关心她,说要带她去看医生了。她在美国接受地狱式反人道训练时,只有失败被抛出去喂鳄鱼的,从没有带你去看医生的说法。
肖甜梨一怔,然后笑了,“明明,谢谢你。”
景明明看了她一眼,回身上车,没有停留,打火,踩油门,坚定而迅速地离去,又剩下了她一个人;就像明十,今天上午,坚定地离开,他转身,开门,关门,没有一次回头,然后坚定地、彻底地离开。
她,又是一个人了。